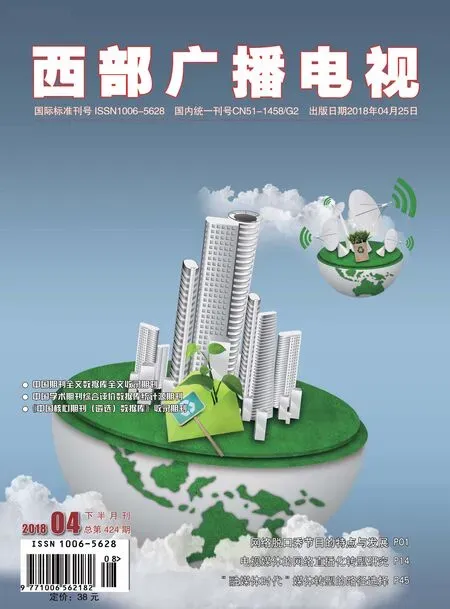后真相時代突發事件的價值判斷及傳播探究
張甜梅
“后真相”是指情緒較事實更能影響人,突出表現為大眾對精英或主流媒體的不信任。有西方學者在2016年提出,傳統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奉為圭臬的“真相”已經衰落,逐漸失去了主導社會共識的力量,西方社會已進入“后真相時代”。國內對后真相的關注集中在2017年,新聞傳播的社群化、社交媒體和社交平臺所依賴的算法推薦、娛樂至上、職業道德缺失等被認為是“后真相”泛濫的重要原因。
1 “江歌案”
“江歌案”發生于2016年11月3日,青島女留學生江歌在日本租住的公寓門前被室友劉鑫的前男友陳世峰殺害。案發時,劉鑫先江歌一步進門得以幸免。因事后當事人劉鑫與江母之間的一系列矛盾使此案頗受關注。
2017年11月10日,《新京報》旗下“我們視頻”局面欄目發布視頻《江歌遇害后第249天 江母和劉鑫終于見面》,將這一事件推入輿論焦點。微博話題#東京女留學生遇害案#閱讀量數十億,相關話題談論度也居高不下。
在局面發布視頻之前,澎湃新聞于9月9日發布了《留日女學生江歌遇害311天:一個母親的“愛、恨、執”》,被認為是相對均衡了雙方意見的報道,影響范圍較小。視頻發布第二日,微信公眾號“東七門”發布文章《劉鑫,江歌帶血的餛飩,好不好吃?》,重點轉向對劉鑫的譴責。11月12日,自媒體人,網絡大V針對此事發表自己的意見。其中,以咪蒙的《劉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兇手,但誰來制裁人性》為代表。
2 “江歌案”的傳播特點
“后真相”入選《牛津詞典》2016年度詞匯時,被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江歌案”的傳播,與“刺死辱母者案”“榆林產婦墜樓”事件等,引發輿論爆點的關鍵在于“訴諸情感”。
2.1 “訴諸情感”引發輿論爆點
“相依為命的母女”“在江歌的墳邊,江歌媽媽給自己留了一個空穴”“我女兒是為劉鑫死的”“你女兒命短”,面對這一句句具有激烈情感沖突的語言渲染,加上被曝光當事人劉鑫的種種舉動,一時間受眾對江母的同情和對劉鑫的憤慨充斥胸膛,人們急需一個情緒宣泄的出口。恰如評論指出的那樣,太多人害怕成為下一個江歌,至于真相到底如何已無過多人追究。正如被引用多次的《經濟學人》“Art of the lie”一文對“后真相”時代的闡釋,“真相沒有被篡改,也沒有被置疑,只是變得很次要了”。
一如“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讓中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生活也沒有那么安全,這些事件引起廣泛關注的點就在于營造了一個良好的情感代入氛圍,大眾被情緒左右。受眾仿佛只需扮演一名“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吃瓜群眾”,再代入自己豐富的情感,站在道德高點一通指責謾罵,不必邏輯思考,也不用付出任何現實成本。
2.2 一邊倒的輿論
“江歌案”傳播過程中,劉鑫的一言一行都成了網民重點分析的對象,不僅是譴責、辱罵甚至上升到了人身攻擊。“地獄空蕩蕩,惡魔在人間”“生而為人,劉鑫你不配”“生而為人,請務必善良”,被大量媒體和網民引用,留言“刀應該往劉鑫身上去”的網民也不在少數。來自咪蒙的“這是我第一次支持網絡暴力”和“法律可以制裁兇手,但誰來制裁人性”也獲得很多認同。
充滿“正義感”的自媒體人,在留言區與反對對劉鑫實施網絡暴力的留言“回懟”,充滿戾氣的回復反而獲得了較高點贊。少數對劉鑫同情的言論被認為是故意刷存在感。同樣,一旦有媒體試圖跳出譴責、還原事實,就會有受眾認為是標新立異,為劉鑫洗白。直至庭審首日,媒體和受眾關注的重點依然是劉鑫到底有沒有撒謊。受眾對劉鑫的憤怒已經遠超兇手,劉鑫成為十惡不赦的罪人。
2.3 真相缺位,輿論定罪
談論“后真相”,一個繞不過的詞是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從傳統新聞價值判斷出發,“江歌案”有幾個關鍵事實:江歌是否是替劉鑫擋刀?兇手為什么要殺了江歌?這些不應該被模糊的事實遲遲沒有媒體去挖掘,甚至“陳世峰”還是“陳世鋒”一度被搞混。對當事人劉鑫的重點關注和對兇手陳世峰的“忽視”,成為多家媒體默認的選擇。開庭首日,報道焦點仍在“劉鑫是否撒謊了”。新聞報道的“歪樓”,與一些社交媒體煽動情緒,忽視真相有很大關系。
網友們深信劉鑫該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價,庭審期間的報道也是幾經反轉。引用庭審期間網友的微信留言,“究竟是誰把江歌推向死亡,這兩天百度推送都不看了,總是峰回路轉,層出不窮!”
2.4 精英話語式微
主流媒體講求客觀、理性的報道和專業人士發言為代表的精英話語在“江歌案”的傳播中,影響有限。
對“江歌案”的理性報道和譴責自媒體人煽風點火的聲音不是沒有,《人民日報》評論微信公眾號發布了《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檢察日報》11月15日在《江歌案更多反思,不妨再等等》提出,與悲劇有關的討論都是有價值的,但媒體牽線二人得以會面,至于案件審判的效果,卻未必是積極的。鳳凰網11月13日發表評論《江歌悲劇中的所有人都需要走出來》,從留言可以看出,這一觀點并沒有獲得認同。對自媒體人的譴責則主要集中在咪蒙身上,如《新京報》發表《媒體評江歌案:殺氣騰騰的咪蒙制造了網絡暴力的新高潮》,公眾號“看理想”的《正義沒贏,人性沒贏,咪蒙贏了|江歌劉鑫案》,但從留言部分看,其贊同度和影響力遠不如譴責性文章。
3 “江歌案”與后真相時代的傳播
維基百科中對后真相時代傳播環境的描述為:雄辯勝于事實,立場決定是非,情感主導選擇。“江歌案”傳播過程中,受眾情緒影響報道重點的現象突出,同時,輿論走向也與自媒體人的引導有直接關聯。后真相時代是一個較復雜的命題,后現代社會發展、新舊媒體勢力迭代、草根階層發聲、媒體煽動情緒、傳播技術革新都可能影響后真相時代的傳播。
3.1 利用社交媒體進行“議程設置”
拋開媒體報道,“江歌案”產生如此大的輿論影響,與江母積極利用微博進行發聲有很大關系。案發后第二天,江母發微博稱懷疑兇手是劉鑫前男友,引起關注。今年5月21日,江母在微信和微博上發布文章《泣血的吶喊:劉鑫,江歌的冤魂喊你出來作證!》,微博閱讀量超過3千萬。江母在8月14日發起的征集簽名請求判處陳世峰死刑的請愿中,有29萬人參與簽名,經媒體曝光后,簽名數達到百萬。隨后,11月23日在微博上發長文《感謝!》,獲得數十萬的點贊和過千萬的閱讀量。
“人人擁有麥克風”時代,受眾與真相提供者的關系不再是固定的。擁有話語權的“草根”當事人積極發出自己的聲音。主流傳統媒體一貫堅持的理性、客觀的聲音,在輿論“狂歡”面前迅速湮滅。受眾信息獲取渠道的轉變讓情感交流、情緒表達與獲取新聞的過程融為一體。面對沖擊,部分媒體的社會屬性開始讓位于商業屬性。至于“武漢面館砍頭案”在后來被證實嫌犯殺人并不是因為“面貴了一元”,榆林產婦墜樓之前到底經歷了什么,真相已無人關心。
3.2 傳統新聞價值標準面臨挑戰
傳播環境的變化使影響傳播效果的因素發生改變。傳統新聞價值要素“為人所矚目”的人物、地點和事件的顯著性轉向是否是具有顯著的情感導向。伴隨傳播環境的改變和信息獲取方式的轉變,受眾關注的已不僅僅是國家大事、著名人物,而傾向于貼近生活的微觀議題。
關注焦點的轉變和社交媒體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推動新聞價值標準的轉變。除去實時、生動、方便瀏覽等因素,作為信息獲取渠道的朋友圈,匯聚了具有類似喜好的群體,點贊和轉發已化為社交禮儀。便于群體交流,滿足自我呈現需要的信息無疑能獲得較好的傳播。關系、喜好、情緒等都成為影響傳播效果的因素,一味用傳統新聞價值標準來衡量新聞傳播的重要性似乎已經不合時宜。
同時,信息傳播環境客觀因素的改變也要求新聞價值標準改變。信息冗余使真相的暴露更為復雜,小道消息繁榮又讓獲取真相的成本變大。新的信息傳播環境,要求新的新聞價值標準。
3.3 網絡輿論生態更趨復雜
后真相時代,輿論的指向越來越趨向于個人情感維系和體驗,而缺乏對事件進行理性思考。這同樣離不開社交媒體的影響。社交媒體追逐利益和群體傳播特性,情緒在傳播環節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致使傳播效果不確定性增大。“客觀事實”不再由公共輿論主導,而取決于分散化的小群和個體的好惡與取舍,公共輿論成為一種不確定的存在。
從“江歌案”始終一致的輿論走向來看,網絡作為公民發表意見的公共平臺,不僅沒有促進多種聲音出現,反而使一種聲音高度一致,呈現出“回聲室效應”。與此對應的是,隨著社交平臺發展日益成熟,每個人都可以借助網絡發表信息、意見、觀點,甚至情緒表達,各種信息充斥網絡,魚龍混雜,輿論主體多元化,主流媒體和個別意見領袖引領輿論的時代似乎成為過去。王志安在《關于“江歌案”:多余的話》中提到,“‘江歌案’報道之初追求的是客觀、理性,真實,”而出現輿論一邊倒譴責劉鑫的現象,看來是與“盡量不給新聞當事人施加額外的傷害”的希望相去甚遠了。
4 結語
“后真相”不是一個新命題,卻因為社交媒體給傳播環境帶來的巨大變化而引起關注。這種情況下,主流媒體的價值在今天顯得尤為重要。受眾并不是不需要真相,只是真相的獲得較以往更困難。因此,主流媒體要適應社交媒體傳播特點,給紛亂的輿論場帶來權威的聲音。
參考文獻:
[1]汪行福.“后真相”本質上是后共識 [J].探索與爭鳴,2017(4).
[2]史安斌.人民日報思潮之思:“后真相”沖擊西方新聞輿論生態[J].人民日報,2017-11-03(07).
[3]陳海峰.“后真相”時代的新聞與真相[J].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7(5):2-7.
[4]王秋菊.后真相時代的輿論特點、引導難點及建議[J].青年記者,2017(6).
[5]孫江.“后真相”中的“真相”[J].探索與爭鳴,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