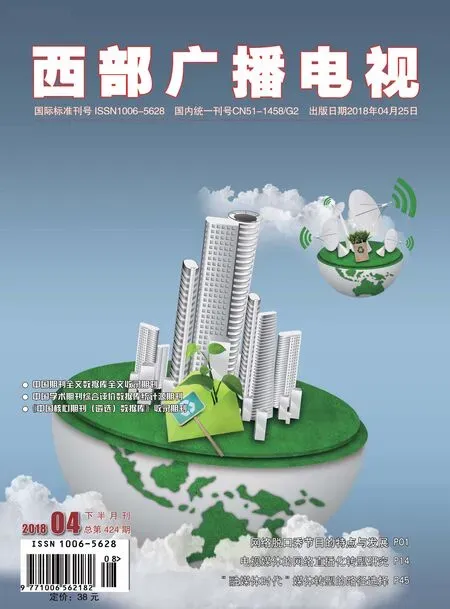電影《芳華》中的符號傳播
林阿強
《芳華》是馮小剛導演根據嚴歌苓同名小說所改編的青春文藝片,影片以女二號穗子的獨特視角,講述了劉峰及何小萍為主線的一群正值芳華的青年一代,在那個充滿理想與激情的年代中,感受著時代所賦予的美好未來,殘酷的戰爭給其帶來的心靈創傷,戰場上血染的風采綻放著獨有的芳華,并在時代改革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整個影片以懷舊的色調,象征性的手法敘述故事、抒發情感、闡述哲理。
1 影視劇中符號的“編碼”形式
麥克盧漢曾言“媒介是人體的延伸”,作為第七藝術的電影是當代重要的傳媒之一,它是人們對信息的交流與分享,同時也是人的視覺與聽覺的雙重延伸,在影視傳播過程中,符號傳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銀幕上直接展現聲音和圖像所組成的符號,以及由這些符號所表達的意義,深沉含蓄地傳達某種觀念思想情感,構成了一種特有的影視符號語言。
1.1 色調在影視作品中的運用
“凡是按一定編碼方式代表著自身之外的實物都是符號,文字、圖像……代言的名人等”。所以,影視在傳播過程中,看似平淡無奇的色彩正傳遞著簡單而純粹的東西,表面看一覽無遺,只有當受眾跳出思維的枷鎖,運用自身文化背景、價值取向等主觀性極強的自我功能才能真正理解影像,也就是說電影文本,是一種有意義的話語,電影從制作伊始便承載了制作方的意義符碼,觀看行為便是我們對這套編碼的解讀過程。
電影《芳華》中以紅綠黑白為其主色調,尤其以紅色為主。紅色在傳統文化中象征著喜氣,奔放之意。在本片所反映的特殊年代中,紅色被賦予了新的文化基因,它不僅代表了那個火紅年代所散發的激情歲月,更是一種對領袖的無比忠誠及革命情懷。影片開始階段,巨型毛主席油畫將觀者帶入自身所處的年代,讓其感受當時的璀璨年華,隨處可見的紅色標語,以及劇中人物所佩戴的紅色領章等影像貫穿影片始終。黑紗徐徐落下,遮住紅色畫像,對于偉人的逝世,黑與紅的強烈對比,象征的是兩個時代的變化和故事情節從美好到衰敗的轉折。隨著整個影片的深入,除運用紅黑色調外,白色基調在劇中也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白色本身象征著純潔,但在影片中白蝴蝶在行進的士兵中穿梭,忽落于士兵肩頭,它是否暗示著死亡,此刻的寧靜給人以沉寂感,似乎等待著戰爭噩耗的來臨,暴風雨前的寧靜隨之被陣陣槍炮聲驚醒,士兵則倒在血泊之中。
1.2 背景音樂在影視中的巧妙安排
聲音是一種感官體驗,是對影像的理解和詮釋。音樂的旋律、節奏結合電影情節的發展能夠影響觀眾的情感反應,本片恰如其分地將音樂與故事場景融于一體。
影片以《草原女民兵》樂曲開篇,此時的文工團內除何小萍外,所有人都沉浸在自身綻放的芳華之中。鄧麗君的一首《濃情萬意》,紅色背景下映襯著浪漫而青春的氣息,也是那段美好的回憶,紅色表現的是年輕人對自由的渴望。同時,也使彼時女青年們芳心未泯,更引得好人劉峰觸景生情,開始了其坎坷的一生。隨著影片的推移,當“觸摸事件”發生后,劇中的好人劉峰被下放到連隊,即將告別文工團時,李叔同的一曲《送別》此時想起,劉峰與小萍的道別,道盡了人世間的冷暖情懷。正是這樣“一個始終不被善待,最能識別善良,也最珍惜善良”的人,將人性的正能量發揮到了極致。當時間來到1976年,三位偉人相繼離世,歷史巨變,《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此時想起,是對偉人的緬懷,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文工團解散,眾人從理想回歸現實,在現實中逐漸妥協,歌曲《駝鈴》唱出了不舍的戰友情,詮釋了一個時代的呼聲。
1.3 拍攝手法的靈活運用
影視制作中,不同的景別與景深的運用可以傳遞各異的藝術效果已是不爭的事實。影片中對偉人逝世,巨型油畫漸漸被遮掩的畫面,運用大仰拍手法,體現了“編碼者”對偉人的無限崇敬。劇中,全景與長鏡頭的出現,綠軍裝,綠軍車,種種影像再現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風貌,突顯了歷史的厚重感,反映了那個年代的滄桑歲月。劉峰在戰場中受傷的近景鏡頭,絕望的表情,憂傷而無奈。影片中,拍攝手法運用最好的一幕便是小萍操場獨舞,坐在觀眾席已患精神障礙的她聽見舞臺上《沂蒙頌》伴奏樂響起,不自覺地抬起雙手跟隨節拍舞動,穿著病號服徑直走向空地,全神貫注地在午夜獨舞。此刻的她沉浸于自己的心靈深處,沒有聒噪的掌聲,沒有嘲笑她的隊友,舞罷,深深一躬,引得無限遐想。影片的結尾,劉峰與小萍再度重逢,坐于小站的長椅之上,相互依靠,默默無語,影片定格于此。屏幕畫面的滄桑掩不住已然逝去的芳華,劇中旁白更加深了世間的悲涼。
2 影視作品的“解碼”體現
任何影視文本本身都是攜帶有意識形態的文本,而這種意識形態是建構而來,也就是說由制作者本身編碼而來,編碼過程受制作者的知識框架、意識形態、技術設備等的影響,將其期望受眾接受的“意義”符碼注入電視作品中。同樣,受眾也在解碼中受到知識生產設備的影響。此理論同樣受用于影視媒介,社會不是同質性的,受眾群體不該被看作是無差別的整體,不同群體囿于自身的意識形態、文化背景、審美差異、年齡階層等限制,對所接收的信息解讀過程并非無差別。
受眾的知識結構、解碼語境與“編碼者”不同時會導致他們對傳播內容作出不同的選擇。基于“霍爾模式”提出的三種解碼立場來解析受眾的“解碼”過程,主導-霸權的立場可以說這是對“編碼”者意圖的最好解讀,“解碼”者完全遵循生產者的邏輯,協商性的立場是受眾接受主導符碼,但對其中某一點提出質疑,對抗性立場則是以一種完全相反的方式解讀主導符碼。對于《芳華》的受眾分析來說,采取完全順從態度的一類人,可以說是與“編碼者”處于同一個時代或能夠在影片中引起共鳴的一群人,而采取對抗式的則是基本對那個歷史年代處于盲區或采取完全對立態度的一群觀眾。可以說,無論采取何種方式解讀影片,只要在影片信息傳遞過程中,受眾并非“子彈植入式”的接受,對“編碼”者所傳遞的意義有自身本能的反應,達到一種動態的傳遞過程,便預示著文化傳遞的成功。
3 結語
電影是精神的載體,任何電影在生產過程中必對現實有所關注。《芳華》運用音樂、色彩、美學等手法,尤其以影視符號語言來闡釋所處年代的文化基因,并以隱喻的方式敘述當時的情景,是對青春記憶的集體反思與回憶,將一個時代的悲歡離合描述得淋漓盡致,詮釋了一代人的芳華歲月。在不違背主流意識形態的前提下,將商業價值作為主要訴求,對重大題材進行歷史化以致至娛樂化改造,以明星陣容來博取觀眾眼球,無可厚非。再者,電影本身就是一種“遺憾的藝術”,因而它自身對歷史的表達就不可能完整如初。
參考文獻:
[1]陸揚.文化研究導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2]嚴歌苓.芳華[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3]拉里·薩莫瓦.跨文化傳播[M].閔惠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