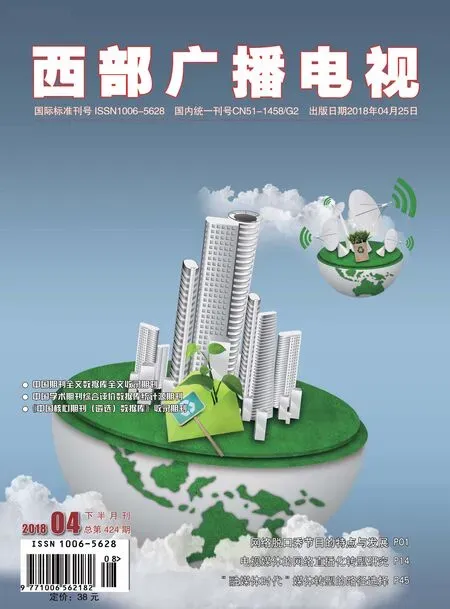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電視紀錄片發展路徑研究
——以《如果國寶會說話》為例
肖 菲
紀錄片作為媒介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傳播知識、承載文化的嚴肅作品,在國家的扶持下和新媒體時代帶來的契機下不斷發展,從傳統的電視紀錄片到由網絡新媒體自制的新媒體紀錄片,從專業團隊制作到UGC用戶上傳參與制作,其形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從《舌尖上的中國》打破中國紀錄片沉默以來,我國紀錄片數量呈現井噴式增長。2018年元旦,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適時地推出了《如果國寶會說話》,其創作和傳播體現著許多新媒體時代電視紀錄片的特性。
1 新媒體下電視紀錄片的新變化
1.1 形式碎片化
早在2016年,日本廣播協會(NHK)為吸引年輕觀眾而推出時長僅60秒的紀錄短片。《如果國寶會說話》開創了我國電視紀錄片的全新形式,以往電視紀錄片通常是30~50 分鐘為一集,而這部紀錄片,每集僅5 m分鐘,實現了“碎片化”的傳播。從2018年1月1日首播以來,《如果國寶會說話》共推出25集,每集介紹一件文物及背后蘊含的深厚歷史。這樣拋棄“大與完整”而取“小與精悍”的大膽嘗試,符合新媒體時代碎片化傳播特征,讓更多現代受眾在忙碌的罅隙中得以“充電”。
1.2 多平臺傳播
每集5分鐘的設置為《如果國寶會說話》掃除了多平臺傳播的主要障礙,在注意力有限的新媒體時代,觀眾的耐心多用于“短小精悍”而非“長篇巨制”的短視頻。《如果國寶會說話》先于2018年元旦在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播出,隨后登陸央視網和騰訊視頻等各大網站,實現了多平臺的成功傳播。截止到2018年2月1日,第一集《人頭壺:最初的凝望》在BiliBili網站已獲66萬播放量,新浪微博“#如果國寶會說話#”話題閱讀量達1.1億。
1.3 話語平民化
與文化歷史類紀錄片一貫的嚴肅風格不同,《如果國寶會說話》的解說詞“正經”而不失活潑。在對文物陶鷹鼎的介紹中,旁白“它有一種很現代的氣質,用當下的話說,就是萌萌噠、肌肉萌”中借用了時下網絡流行語“萌萌噠”,如此輕松的文案廣受網友好評。對中央電視臺這樣國家級官方傳統媒體來說,在制作精良的基礎上凸顯受眾意識,走親民路線,通過話語的平民化來增加受眾文化身份的認同感,無疑是穩中求新的一招。
2 新媒體下電視紀錄片的發展路徑探索
2.1 節目IP化
如果不對其深層價值進行挖掘、運營和跨界轉化,《如果國寶會說話》就和其他紀錄片一樣,始終只能停留在節目本身。在美國好萊塢等成熟的影視產業市場,70%的收益來自電影衍生產業,而在我國,這個數字不足20%。《如果國寶會說話》作為一個文化類IP,有著央視的強大后盾,自帶巨大粉絲量與影響力,如何在深厚且復雜的文化資源中塑造符合現代審美的文化符號,如何使其產生跨文化、跨行業的影響力并實現線下轉換,值得相關工作人員去深入探索。同樣作為文化IP的故宮博物院便是國內跨界轉換的典例,2016年入住淘寶天貓開設“故宮博物院文創旗艦店”,推出故宮博物院主題文創產品,至今已有近80萬粉絲。
2.2 創新形式
新媒體時代呼喚新媒介內容與形式,我國文物類紀錄片數量不少,《如果國寶會說話》能脫穎而出并走紅網絡,與其敢于創新有直接關系。《如果國寶會說話》在時長上進行大膽創新,在話語表達上對精英話語的突破和在宣傳上給予受眾的新鮮感,都是對電視紀錄片創新的有益探索,值得借鑒。
2.3 不忘初心,深耕內容
近年來文物類紀錄片大熱,《如果國寶會說話》正是抓住了這一熱點,但是,紀錄片同綜藝節目、電視劇和電影等娛樂節目相比仍屬小眾節目,其受眾以大學生等高學歷人群為主。在把握熱點、創新形式之外,紀錄片還應保持其應有的品質,以精良的制作和思想性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審美需要,這是紀錄片的立身之本,也是其傳播文化、普及知識、提供娛樂的社會功能的必然要求。
3 結語
新媒體環境極大擴展了各種影視藝術作品的發展和傳播空間,在紛繁復雜的藝術文化作品中,紀錄片始終是思想性和知識性的代表。在新媒體環境中,我們要融入互聯網思維,創新內容與形式,延長紀錄片發展的產業鏈,不斷探索應對新媒介環境的解決之法和我國電視紀錄片的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張昊.新媒體背景下我國紀錄片的網絡化傳播分析及展望[J].新聞傳播,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