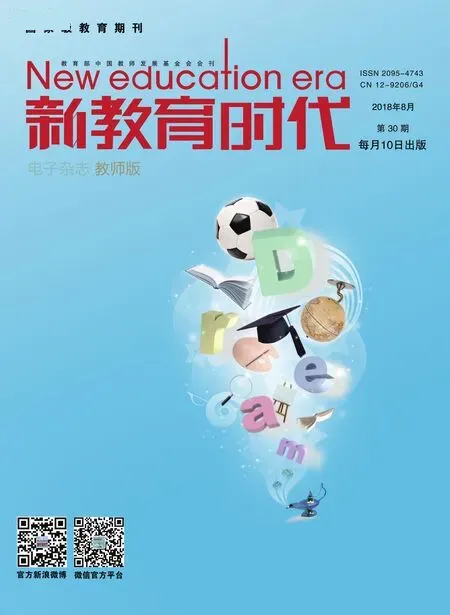陶冶性情 美化生活
——淺談書法欣賞
(臺山市少年宮 廣東臺山 529200)
書法欣賞與其它藝術欣賞一樣,具有整體的直觀性,欣賞者不僅以豐富的學識為后盾,更重要的是要有對于書法美的直接感受能力。憑這種直觀,不必經過程任何科學的分析,即能把握住書法作品的優劣,這是經過長期審美訓練達到的,其中包括先天的因素。
書法審美,是對作品的整體觀照,這是一個完整的、活的生命,我們不能肢解它。作品的技巧、社會性、歷史內容只是作為通向真正欣賞的橋梁,所以說,書法欣賞的中心是把握其核心所包含的意蘊及其深刻的啟示力量。人的靈智及整個身心,在欣賞中由現實的世界逐漸過到藝術世界的彼岸,象禪字一樣,“書法即禪”,在領悟中進入到“禪境”的最高境界。[1]
所以我認為,整體的書法欣賞方法有幾個要點,即遠觀、圓識、活參。[2]
一、遠觀
一幅優秀的書法作品,首先要從整體上感染欣賞者,失去了整體,局部的“美”也就不存在了,并予示著這幅作品的失敗。要把握整體,就要與作品保持一定距離,作品的整體布局、意味,都會在一定的空間距離外閃觀出來,有些作品每個字的筆畫、結體還不錯,甚至還有一定功力,而整體卻相當零亂,就象合唱隊里的各聲部演員,不管高、中、低音,都扯著喉嚨唱高八度,盡管每個人的聲音都高亢、優美,但整個旋律破壞完了。書法作品整體美表現在文字內容、外在形式、藝術內涵有機融會所顯示的總的藝術特征。所以說,遠觀即把書作中諸多要素在主觀上有意地統一起來,從而便于在整體上進行審美感受。[3]
二、圓識
書法本身即單純又復雜。它單純到僅以黑白旋律去征服欣賞者;但其本身又是一個多維結構。深入理解一件作品,有賴于多方面的知識經驗,它涉足的領域是如此之廣,盡管這一切在實際欣賞中不顯露出來,但作為內在的知識結構卻是不可少的。圓識,即用廣泛的社會知識、人生經驗從各種角度、各個層次去理解作品。[4]
三、活參
至今,我們還未能對藝術美徹底解釋清楚。人們除了物質需要,還必須傾訴、宣泄自己的感情、欲望及一切體驗、感受等,此為人們的生理及心理的需要。藝術,便是人們惜以傾訴的形式,其渠道,除創作之外,對于更多人的表現則是欣賞。書法,在諸多藝術形式中是最善于使人傾吐感情、宣泄心靈的一種藝術手段。人們的精神生活是復雜的,一些可以靠語言去訴說,但更多的潛意識則必須在心靈直接與藝術的觀照中才可得以抒發。假若作品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意味”能成為欣賞者心靈中的圖象,那么這幅作品就是成功的,所以,人們常常感到在書法作品中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神秘的意味,仿佛精妙之處全在其中。單靠知性、邏輯推理是難以把握住這精妙之處的,這就要靠遠觀、圓識之后的“活參”了。“活參”者,乃書法欣賞中不受外界干擾、精神整個沉醉于其中,在頓悟中產生心靈的象征表現活動之謂也。這已超出了作品的表面形式及理智所理解到的一切,產生了對人生、人性形而上的大徹大悟,從而進入到一個更高的、只可意會的精神境界之中。
“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書法的這一深層意蘊的獲得也不是靠抽象的說理可以悟到的。袁枚在《與尹相國論書》的尺牘中說:“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器為形象,必以道貫之,而精神始露,然道不能以氣力取也。誠于中,形于外,必有事焉,而易正,蘊釀久之,不期然而然。”他大致道出了悟“道”的方法。欣賞者應拋卻掉世俗的,實用的觀點,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整個身心融入到作品中,把個人的“舊我”消融在新的藝術境界之中,揚棄淺薄的、功利的東西,欣賞者本身也經過了“再創造”,于是精神經過陶冶,感情得到升華。藝術之門,只向敞開心扉、敢于暴露靈魂的人啟開!
站在新時代的折點上,作為中國人,應為中華民族國粹——書法感到驕傲和自豪,弘揚傳統文化,更應作為使命,我們自覺地、堅定地守護好這塊文化沃土,在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同時,更應高舉習近平新時代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讓中華文化更好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
書法——這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璀燦明珠,將會在世界文化之巔上光耀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