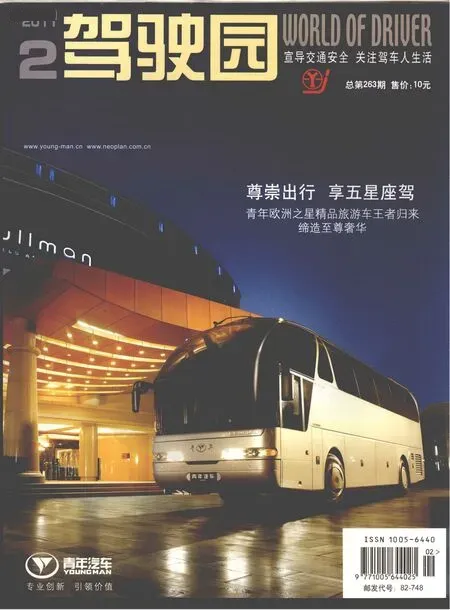北京知青修筑“世界最長磚砌公路”
姬長偉
清晨,“牛頭”車從“新疆第二大城市”庫爾勒出發,向著大漠中的那段現存僅5公里的“世界上最長磚砌公路”抵進。兩三個小時后,我和同事及磚砌公路當年的建設者高敦祿一起抵達它的近前。退休賦閑在家已年屆七旬的高敦祿老人,踩著眼前斑斑駁駁的磚砌公路緩緩地走,眼神讓人難以琢磨。
一
1966年夏天的北京,“文化大革命”風起云涌。當時,在京各大農場接受“正面教育”的知識青年,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觀看《生命的火花》《軍墾戰歌》《黃沙綠浪》《天山上的紅花》等影片,于是人們對美麗壯觀而又遙遠的新疆產生了向往。
看過電影,居然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干部給知識青年們作報告介紹新疆的情況,動員有志青年報名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支援邊疆建設。于是,后來就有了一幫北京知識青年,高唱著“滿懷熱情,滿懷理想,跨山越水到邊疆”的歌曲登上了開往新疆的列車。
高敦祿稱,在北京的天河農場接受“正面教育”前,他是山東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學生,因為在課堂上向老師問了些對浮夸風不能理解的問題,被打成是彭德懷等人的“應聲蟲”,而被迫接受勞動改造。
“受打擊歸受打擊,但那個年代知識青年們的愛國激情并沒有因為時代特殊而減退,所以很多北京知青積極報名來了新疆。”高敦祿說,1966年那趟由北京到新疆的列車上,有已“摘帽”的和猶未“摘帽”的“右派分子”;有對“極左”路線和“三面紅旗”略有微詞的“思想反動者”;有不安心農業生產盲目流入城市而被稱為“盲流”的農民子弟;也有稍具劣跡的城市失足青少年。那是一支兩千多人的隊伍,他們的出身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文化程度更是參差不齊,有研究生、留學生,也有小學生甚至文盲。
經過四天四夜顛簸,高敦祿這一行人終于到了大河沿(吐魯番)火車站。剛下車,他們就受到熱烈歡迎,一位全副戎裝的兵團領導當場宣布:你們這批北京青年已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前身)的新成員!這支兩千多人的隊伍當即被編入兵團建設工程第二師工程支隊(1969年二師解散,工程支隊編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二師),并接受指令向南疆尉犁縣開進。
“到了尉犁縣,我才知道是讓我們去修尉犁到若羌的公路。”高敦祿說,開始的時候,這支隊伍的隊部設在尉犁城南橋頭上。當時,尉犁至若羌公路的代號為“654工程”,意思是說,是國務院于1965年4月正式批準立項的。
二
“由尉犁至若羌原本是有路的,盛世才兩面三刀依附蔣介石政府后,蔣介石為了拉攏他,曾給新疆撥付1305萬元興建庫爾勒至甘肅安西的等級公路,這條路就經過尉犁和若羌。但由于民國時期這條路的修建標準低,沿線又多為沙漠戈壁,所以路況很差。1966年,我們北京知青來到這里時幾乎看不到公路的樣子了,過往汽車大多要靠拱沙包,扛杠子,鋪紅柳枝,才能勉強通過,由庫爾勒到若羌一般要走四天。”高敦祿說,民國時期的那條公路叫南疆公路,全長1344公里,其中庫爾勒至若羌為422公里。新中國要重修這條路,一是為沿線各族人民的生產生活提供便利;二是要為新疆尋求第二條連接內地的大動脈。因為當時中蘇關系惡化,北疆通往河西走廊的路一旦被卡住,新疆就會與內地失去呼應。
高敦祿說,他所在的建設工程第二師工程支隊的二大隊八連,當年的第一站住在尉犁縣卡拉附近的戈壁上。他們一個班十幾個人住一頂帳篷,時值8月下旬戈壁上驕陽似火,帳篷里和蒸籠沒什么兩樣。到了夜晚,涼風陣陣,大多數人身上也只有一件單衣,施工戰士們又被凍得瑟縮發抖。
高敦祿回憶說,那些年輕人本想到了兵團上級會發給書包、衣物,但沒想到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他們人人夢寐以求的軍裝、軍帽都遲遲沒發下來。在尉犁通往若羌的那片茫茫的戈壁和沙漠上,他們那批來自京城的青年,第一次領略了“早穿皮襖午穿紗”的內陸沙漠性氣候。
“氣候決定了我們吃不上新鮮蔬菜,最好的情況下我們也只能吃點四川臘肉。我們的主食也就一頓兩個窩窩頭。由于沒有機械,工程得全靠手工來干。”高敦祿說,當路修到尉犁至若羌間的英蘇地區的時候,施工隊伍已經沒有足夠的砂石料,經工二師黨委與新疆交通廳研究,決定由工程支隊就地取材,用風干胡楊作燃料燒磚砌路,先試點,取得經驗再全面推廣。由此,“654工程”中,全長102公里的磚砌國道公路,就此全面在若羌縣英蘇地區推開。
三
戈壁上沒有專門制作磚坯的機器,施工隊員只好土法上馬,他們先平整場地,再備上土燒制砌路的紅磚。高敦祿回憶說,那制坯的土很有講究:黏土和沙性土要搭配合適,黏性大了,磚坯容易干裂;沙性大了,磚坯回“酥”,強度不夠。制磚的土要用水泡透,不能有疙瘩,軟硬也要適當,泥硬了灌斗不實,磚坯缺棱短角,泥軟了磚坯凝不住會變形。
燒磚要建磚窯,沒有現成的圖紙,畢業于清華大學建筑系的知青林鋒和劉雪鵬有了發揮專長的用武之地。在沒有任何資料的情況下,兩人白手起家與大家一起邊試驗邊改進修起了兩座“馬蹄窯”,又經過多次摸索試驗,竟燒出了高標號的紅磚。高敦祿說,用風干木做燃料,窯火力猛、溫度高,燒出的磚像涂上瓷釉,色澤青黃,黃中透綠,頗似北京故宮用的琉璃瓦,輕輕敲擊則叮當作響,仿佛金屬發出聲音,其硬度和強度都大大超過了青磚,接近于陶瓷,施工隊員叫它“琉磚”。有時磚窯內溫度過高,琉磚熔化變形,互相黏結在一起,出窯時要用鐵錘敲打分離開才能取出磚窯……
實在沒想到,高敦祿這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高才生,居然能夠把燒磚的工藝回憶到如此火候。他說,磚坯模子也是施工隊員動手做的,按照紅磚的標準規格長24厘米、寬12厘米、厚6厘米,用木板釘成六塊連在一起的坯斗,一次可倒六塊磚坯……
如今,人們經過尉犁至若羌的那段218國道公路,仍會在路旁看到一些廢棄的磚窯,它們雖然已經火滅灰冷、四壁坍塌,但仍可映現燒磚人當年的智慧和艱辛。endprint
高敦祿說,磚燒成了,最后一道工序是砌磚路面。這項工作要把黏土路基墊平夯實,使之中間稍高,略成拱形,兩邊各留出一米寬的路肩,上鋪二十厘米厚的黏土灑水夯實,內側立一排橫磚作邊界。中間六米寬的路面下面先鋪一層平磚,上面再按“人”字形拼碼一層橫磚,這很像鑲木地板的樣子。磚與磚擠得很緊,雖然沒有水泥灌漿勾縫,只有用細綿沙填充磚縫,路面卻緊密無間,渾然一體。
四
218國道尉犁至若羌方向931至1033公里間,曾經坦坦蕩蕩地鋪展著102公里的紅磚路面,它于1966年8月開工建設至1971年5月竣工。于今,在它殘存的5公里的路基的一側,新疆交通廳公路管理局立起一塊“世界上最長的磚砌公路”紀念碑,其近旁還有一塊“世界上最長的磚砌公路”簡介碑。那紀念碑和簡介碑都用大理石砌成,是過往行人憑吊“世界上最長的磚砌公路”的主要物什。
高敦祿緩緩走到那紀念碑和簡介碑的跟前說,“世界上最長的磚砌公路”共計用了6200多萬塊磚,足可建上百幢樓房,但當年的筑路隊員當時住的卻是帳篷和地窩子,竟沒有人說要用磚來蓋住宅樓。20世紀70年代初,西北公路設計院的一位工程師聞訊前來考察。他經過實地調查、檢測后大發感慨:這樣的磚砌公路世界少見國內僅有。兵團戰士,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修起這樣高水平的公路,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創造,值得載入世界公路建設的史冊。
2002年7月28日,新疆交通廳與巴州黨委、巴州人民政府,在庫爾勒聯合舉行最長磚砌路國道公路吉尼斯世界紀錄頒證儀式暨新聞發布會。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總部理事、新疆總代理為新疆公路管理局頒發了最長的磚砌公路創“吉尼斯世界之最紀錄”證書。
時至今日,那段“世界上最長的磚砌公路”引來不少猜疑:在茫茫戈壁灘上,從哪里弄來這么多磚鋪路面呢?有人說,是從幾百公里外的庫爾勒、尉犁運來的;有人說,是重刑勞改犯就地燒制的;還有人說,當年修路的工人在這里砍伐了大片胡楊林燒磚鋪路,破壞了生態平衡……
林林總總的猜疑讓高敦祿這位歷史的見證者百口莫辯,他只是站在磚砌公路上自言自語:“不管怎樣褒貶不一,這條路為人們提供了交通方便應該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吧。”
在我的眼前,那段現在僅存5公里的磚砌公路,也并不能夠輕易地望到盡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