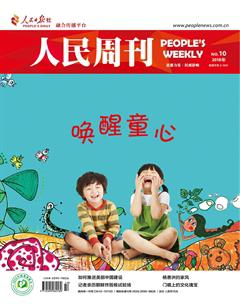那場古希臘喜劇
王佳可

提起古希臘,你會想到什么?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古希臘悲劇?還是雅典燦爛陽光下歷經風雨依然矗立的帕特農神廟?無論哪一樣,都凝聚著古希臘精神與文化的魂魄,都能讓觀者領悟到崇高與悲壯的意義。穿過時光的隧道,這個春夏之交,古希臘喜劇經典《鳥》在國家大劇院創排、上演,為我們展示出希臘古典戲劇的另一個面向:夸張、幽默、機智、諷刺,在令人會心一笑的同時,有所感悟,有些思考。
古希臘的喜劇藝術
若說古希臘悲劇是西方文學史上不墜的太陽,古希臘喜劇則仿如太陽之影,存在著,卻常被人忽略。其實,喜劇產生的歷史早于悲劇,它起源于古代祭祀酒神狄奧尼索斯的狂歡歌舞,普遍認為來自麥伽拉地區的蘇薩利翁于公元前570年左右就進行了喜劇創作。但直到公元前486年,喜劇才正式在雅典“大酒神節”戲劇比賽中演出,而早在約公元前536年,雅典詩人忒斯比斯的戲劇就在“大酒神節”上演。于是,公元前486年,被永久地鐫刻在戲劇史上。
《鳥》的作者是古希臘詩人阿里斯托芬,他約生于公元前446年,那是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也是雅典城邦日漸衰落的時代。他一生創作了44部劇本,在保留下來的11部劇本中,《鳥》是唯一一部以希臘神話為題材的諷刺喜劇,理想深寄,文辭優美。詩人去世后,哲學家柏拉圖為他寫下墓志銘:“秀麗之神想要尋找一所不朽的宮殿,畢竟在阿里斯托芬的靈府里找到了,”
與古希臘悲劇表現嚴肅命運的題材不同,古希臘喜劇展現的多是民間生活,形式幽默,語言詼諧。在阿里斯托芬生活的年代,雅典的社會階級發生急劇變化,奴隸的廣泛使用與貨幣經濟的興起,令貧民與富豪之間矛盾尖銳。與此同時,詭辯學說風行,傳統信仰和道德被否定,在教育和思想領域產生不良影響。面對這一切,詩人的創作態度是嚴肅的,他以荒誕的情節寫現實的主題,在嬉笑怒罵中蘊含了對社會現實的諷刺與批判。恩格斯曾評價阿里斯托芬是“有強烈傾向的詩人”,車爾尼雪夫斯基也說他的喜劇具有“重大的教育意義”。
《鳥》于公元前414年首演,雖僅得次獎,但詩人精湛的諷喻技巧與詩意的語言風格在劇中爐火純青。《鳥》講述了這樣的故事:兩個雅典人皮斯賽泰洛斯和埃福埃爾皮得斯厭惡城市的苛捐重稅和訴訟風氣,離開雅典,四處奔走,想尋找一個可以逍遙生活的地方。到了鳥林,他們請教戴勝鳥,隨后決定與鳥兒們一起在空中建立一個城邦,截斷天地間的交通,用饑荒迫使天神向鳥類臣服。城邦落成后,命名為“云中布谷城”,來自人間的詩人、預言家、不孝子等人紛至沓來,洋相百出;天神宙斯也派海神波塞冬和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來“云中布谷城”交涉,冀圖收回統治權。二人與其周旋,最終利用眾神的饑餓獲得勝利,與鳥兒們過上幸福的勞作生活。
復排經典要讓觀眾看懂
翻開楊憲益先生翻譯的《鳥》,抒情歌詞鋪陳而出,與古希臘神話淵源深厚的用典比比皆是,許多針砭時弊的內容距離今天太過遙遠,可以說,不讀注釋就想讀懂這部喜劇,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作為閱讀的文本和作為演出的劇本之間差異巨大,畢竟在舞臺上,演員無法停下來對觀眾解釋每一個用典和人物背后的意義。于是,如何讓今天的觀眾看懂,成為擺在導演羅錦鱗和羅彤面前的一道難題。
羅彤對我說:“在《鳥》中,阿里斯托芬通過語言而非戲劇沖突來達到喜劇效果,這對戲劇演出來講非常困難,因為希臘語中的很多典故都來自當時的社會生活,例如打了敗仗的將軍等,今天的觀眾很難理解這些,我們只能忍痛割愛。此外,楊憲益先生的劇本語言優美詩化,適合閱讀而非演出,我重新翻譯了劇本,力求既是詩歌,又是臺詞,朗朗上口。”即便如此,羅彤重譯的翻譯本依然綴滿200多個注釋,在導演使用的工作本中,她再度進行了刪減,刪除了歌隊合唱中抒情的與劇情無關的內容。
在羅錦鱗看來,導演是一門渲染與沖淡的藝術,對于經典戲劇的當代開拓,重點在于渲染什么,沖淡什么。談起《鳥》的創作,這位第一個將希臘戲劇搬上中國舞臺的老導演眼中閃著理想的光芒,略有些激動地對我說:“有人說,阿里斯托芬的《鳥》過于理想化,無法實現。可我說,人怎么能夠沒有理想?只是理想的實現,要像劇中的鳥兒們一樣,通過踏踏實實的苦干才能成真,這是我想對觀眾說的話。”
也許正因對戲劇始終懷有熱忱的理想主義,羅錦鱗才會接下這部從立項到上演不過兩個多月的喜劇創排任務。他說,國家大劇院重視經典作品的表現,這是他們的長項,整個劇院都非常支持《鳥》的創排工作。在舞臺效果上,羅錦鱗力圖將古希臘喜劇簡潔、夸張、諷刺與中國戲曲寫意、虛擬、象征的美學風格相結合,以中國傳統戲曲服飾中的翎子象征鳥兒的翅膀,用一幅簡約寫意的中國紅色剪紙,剪裁出阿里斯托芬的頭像剪影,倒影在如一張卷曲白紙般的舞臺之上,仿佛一幅中國古典水墨畫。
“我有一種使命感”
初見羅錦鱗和羅彤,我的心情緊張而激動,因為羅念生,他是羅錦鱗的父親,羅彤的祖父。每一個對希臘文學稍有了解的人,都無法不對羅念生心懷崇敬,如同普羅米修斯,他是把希臘文明的火種“盜來”中國的人。
他翻譯了古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完整傳世的7部悲劇,索福克勒斯全部傳世的7部悲劇,歐里庇德斯的5部悲劇,阿里斯托芬的5部喜劇,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修辭學》,以及眾多古希臘文學經典。他主持編寫了《古希臘語一漢語辭典》,制定了《古希臘專用名詞譯音表》等希臘文學翻譯的奠基之作。1987年12月,希臘雅典科學院授予羅念生“最高文學藝術獎”,以表彰他近60年來為研究和傳播古希臘文化作出的巨大貢獻,全世界僅有4人獲此殊榮。
深厚的家學淵源令羅錦鱗對希臘戲劇有著近乎天然的血脈聯系,然而直到1986年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登上中國舞臺,他的導演生涯才終于與希臘戲劇合二為一。提起父親羅念生,81歲的羅錦鱗對我說:“直到《俄狄浦斯王》上演,父親才對我這個大兒子刮目相看,才開始偏疼我,之前他更看重學習自然科學的弟弟,因為他更聰明。”就是這個在父親眼中看來不那么聰明的長子,在30多年的戲劇導演實踐中,始終致力于古希臘戲劇與中國戲曲的“中西融合”。他導演的河北梆子戲版《美狄亞》在第二屆國際古希臘戲劇節演出時,時任希臘文化部長竟激動地對他說:“我們應該派人到中國去學習中國人是怎么認識希臘戲劇的。”
翻譯《鳥》的時候,羅彤常常翻查《古希臘語一漢語辭典》,每一次的查找,都仿佛如她與祖父對話那樣美好。在她看來,父親是從事導演實踐的人,使祖父在半個世紀前進行的文學翻譯“活”到了舞臺上,而自己則很幸運,既做學術研究、文學翻譯,同時也參與舞臺實踐,導演戲劇作品。這樣的幸運,更是一份責任。羅彤對我說:“我覺得,我有一種使命感,不僅要繼續完成希臘文學的翻譯更新工作,還要向大眾普及希臘文化知識。當我們走出去與世界對話之時,需要了解世界,了解西方文明的源頭——古希臘文明,它的文學、藝術和哲學,這是展開對話的基礎,也是相互理解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