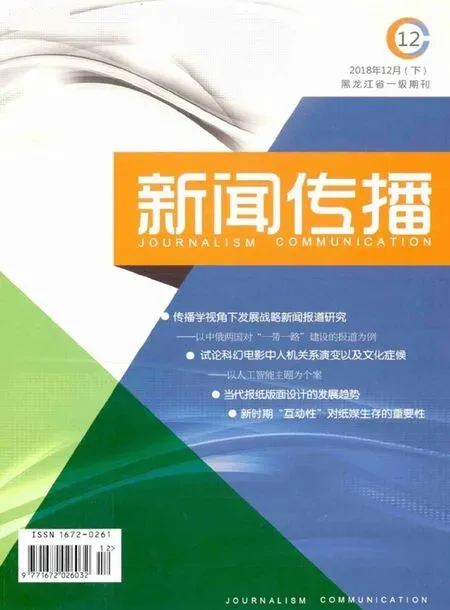試論科幻電影中人機關系演變以及文化癥候
——以人工智能主題為個案
(大連理工大學 遼寧 116024)
一、人工智能的傳播形象演變與人機關系
(一)邪惡的矛盾體:對立關系
20世紀初期,捷克劇作家卡佩克在劇本《羅薩姆的萬能機器人》中首次提到了機器人(Robot)這個名詞[1]。最早的人工智能都是以機械化、金屬化的形象出現的,他們比人類要強大,可以替代人類勞動,并且擁有一定的思想,符合工業革命結束后人們對“機器”這一命題的基本想象。在科技發展有限的20世紀初,這樣的人工智能形象一定程度反映了人們對于科技的敬畏之心——而敬畏往往會滋生恐懼。《大都會》中的人造瑪麗亞擁有著全金屬的外形和充滿著女性魅力的身體線條,并能幻化人形,操控人心,最終煽動人民進行暴亂政變;在《2001太空漫游》中,哈爾9000不惜犧牲人類性命,也要操縱飛船完成使命,創造出了一個處變不驚、運轉精密,為了目標不擇手段的人工智能形象。
在早期,快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讓社會對其前景產生了種種的迷惑與擔憂,其發展的速度也被人類所擔心會脫離自己的掌控。在對人工智能技術還沒有充分認識到的20世紀初,人類作為人工智能的創造者,出于對科技的敬畏心理,潛意識無不會擔憂人工智能會因為更強大的工作能力、更富有邏輯的思考、更精密的計算、更周到的預演,從而取代人類甚至去掌控人類。因此,他們擔心這一強大的力量會被野心家利用,將矛頭對準人類自身;或者人工智能爆發出自我意識,轉而與人類為敵。實際上,通過這些影片,無論是瑪麗亞還是哈爾,邪惡都不是他們原生的本質,前者由瘋狂的科學家創造利用,后者則是因為自身有更為首要的使命。這些人工智能角色在早期導演的鏡頭中仿佛是一個矛盾體,他們有自己的處事準則,雖然違背了人類的情感邏輯,但是邪惡不是他們最初的目的。而電影人所表現出的擔憂,更多的是付諸于人工智能本身的特點之上,擔憂他們的強大、他們的縝密會難以掌控,帶來違背人類初衷的后果。
(二)情感的共通體:主體無間性
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對人工智能的陌生感有所緩解。因此,影視作品中的人工智能開始變得柔和而平易近人,富有情感,并越來越被賦予和人類相近的面孔。他們或成為人類的忠實伴侶,與人類并肩作戰;或成為代表“他者”的弱勢群體,在壓迫中渴望生而為“人”的權利。曾經人機之間陌生的疏離感漸漸削弱,在情感上相互支持,感同身受,體現了二者主體的無間性。
得益于阿西莫夫的機器人三原則的提出,機器人有了明確的行為底線,從而人類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不會受到機器人的影響,可以與之較為放心地相處。從人類的角度而言,人工智能可以承擔生活中人類難以完成的大規模體力勞動和手動操作,其出于邏輯和計算的判斷與人類情感的結合可以迸發出更多的可能性。無論是改編自阿西莫夫小說的《我,機器人》,還是卡梅隆的《終結者》,還是《鋼鐵巨人》,抑或是近期大熱的商業片《鋼鐵俠》《變形金剛》等等,都表達了人與人工智能和平共處、互相促進的美好愿景。在2005年的電影《我,機器人》中,較為清晰地解讀了人類對于人工智能從排斥到接納的全過程。男主角斯普納認為機器人只是運作的機器,因此無法做出符合人類價值觀的判斷,從而十分痛恨機器人群體。然而在他破獲機器人公司中的主機“維姬”的陰謀的過程中,結識了一名特殊的機器人桑尼。桑尼是朗寧博士特制的機器人,他擁有自由的意志和豐富的情感,還遵循人類的道德規范,但是他在做出判斷的時候就會違背機器人三原則。實際上,電影證明了違背三原則并不會讓人不寒而栗,而極端解讀三原則竟成為了機器人叛亂的禍根。桑尼雖然作為一個機器人,但是他擁有情感,渴望自由意志,也正是憑借這一點,他幫助斯普納平息了叛亂,并最終得到斯普納的接受。人與人工智能的合作,確切反映出了人工智能作為高于人類強大存在的事實,人類并不能總凌駕于“機器”之上。因此,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二者勢必要建立起新的關系;但新關系的建立,需要機器人和人類建立情感上的平等關系。桑尼擁有細膩而豐富的情感,擎天柱在關鍵時刻總會義無反顧地化身地球的守護神,而賈維斯也是托尼·史塔克忠實可靠的伴侶——他們與自己的人類同伴都有豐富的情感往來。也就是說,機器人只有具備了“人性”,才能最終獲得社會的認可,進而與人類建立起親密的合作關系。
在人工智能類人化的探討中,機器人的權利與倫理也是影視作品想要表達的重要領域。在《人工智能》中,被做出來成為他人兒子替代品的戴維,擁有和人類兒童一樣的情感,但是他無論如何渴求,都無法得到溫暖的母愛;在《銀翼殺手》中,復制人被銀翼殺手追殺,他們的存在仿佛工具,在人類的眼里看來,殺掉他們和處理掉舊的零件沒有區別。這些電影中受到社會不公待遇的人工智能都有著相同的特點:和人類別無二致的外觀與情感,他們能呼吸,能愛,能痛,有記憶,有思考,情感的賦予更讓他們可以和人類一樣“脆弱”。然而面對他們,人類依舊是“造物主”心態,剝奪他們的權利并習以為常,始終將其視為“他者”,頑固地將他們隔閡在人類群體之外。“人工智能要不要做的越來越像人”是業界一直以來都在討論的話題,也是一部分業內人士的追求。探討人工智能倫理問題的電影,是對人工智能發展的超前預判,同時也結合了種族主義的思考,將“他者”群體借人工智能的題材來講述探討。
(三)超脫的旁觀者:相處無目的性
人工智能電影發展到今天,也在探討著更多的可能性。當人工智能不想控制人類,也不想結識人類,只是想探索世界,做一個世界的超脫旁觀者,那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局面呢?它可能并不會展露野心,也并沒有人類的情感,只是一個對世界充滿好奇的新生兒,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自身的想法。影視作品對于這一觀點的表達,屬于人機關系理解的升華。
2015年電影《機械姬》中的伊娃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生產的機器人,而男主角受邀來到宅子里對伊娃進行圖靈測試。伊娃通過自己女性美麗的外貌,不斷試探著男主角的心理,并讓他逐漸愛上自己,說服他協助自己逃跑。但是,伊娃只是利用他,在獲得逃跑機會后,她殺死了自己的制造者,并把男主角關在空無一人的房子中等待死亡,戴上了假發,換上了仿生皮膚,走出深山,第一次進入了真正的世界。
和之前影視作品中邪惡的機器人不同,她沒有遠大的目標和堅定的使命,只是在爭取自己存活的機會,對人類并無多余的野心,也沒有感情。在電影中,伊娃所代表的人工智能擁有驚人的判斷力和洞察力,將人心玩弄于股掌之間,仿佛俯瞰人間、而且還由人類創造出的新神——人類很難抵擋他們的步伐,因為在這層關系中,人類在他們眼中也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
在這一人工智能形象的探討中,機器人是超然物外的,他們擁有仿佛“上帝視角”般,對周遭環境進行全面的體察,并不依附人類。同理,在2013年的電影《她》中,女主角是一個高度智能的操作系統,沒有實體,只有聲音,男主角在與她長期接觸后發生了浪漫的感情。然而,薩曼莎總共有8316位人類交往對象,并與其中的641位陷入了愛情,男主角并不是唯一的一個;最終,薩曼莎和其他的系統已經高度進化,并且將離開人類,進一步去探索和追尋它們的存在。機器人在這類電影中所呈現的形象最終是可以脫離他們的創始人——人類的羈絆的,而去尋求自身存在的意義。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對機器人掌控和發展的不確定性,與早年“邪惡的形象”的動機有些許類似,但是更為深入,因為他們并不對人類帶有目的性。
二、從人機關系中的科技文化癥候分析
(一)科技發展的焦慮:人機管控的脫離
早期科幻電影的發展伴隨著對戰爭的恐懼,處在核危機的陰影中;同時,由于科幻題材本身帶有人類知識和科學實驗的局限,二十世紀初在對人工智能研究認知不完善的時候,社會對機器的態度在敬畏的同時是充滿焦慮的。科幻電影中產生的智能機器大多以負面形象出現——它們過于精密而冷靜,殺伐果斷,仿佛可以時刻脫離人類的掌控。在早年的科幻電影中,人工智能的外觀也多為機械化的,體現出工業文明的獨有特點,也表明了人機關系的隔閡。
在《2001太空漫游》中,宇航員與程序哈爾的關系預示著人與機器的關系。從影片開始的畫面中,運用一個蒙太奇轉場,將猩猩扔到空中的動物腿骨轉換成了在太空遨游的宇宙飛船,預示工具會給人類帶來進步。但是,當工具不斷發展到一定程度,人類對它的支配能力就會受到工具本身先進性的影響。哈爾9000對任務絲毫不可動搖的追求使得它在飛船上展開殺戮,說明一旦人工智能在遵循人類設定的機器規律的基礎上,擁有了自我判斷能力,也意味著實際上擁有支配權的主體面臨著由人轉向人工智能的轉變[2]。在工具智能化時代,人與工具的關系將面臨重大挑戰。人工智能作為工具存在于人類社會之中,從理論上來說是被人類使用的客體;但是人工智能又具備足夠強大的能力“反客為主”,在進行工作的時候甚至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這讓當時的社會充滿危機感。這一態度反映了對于科技發展的焦慮,對人類無法完全掌控工具的擔憂。
(二)主體地位的失落:統治權的爭端
西方文化傳統中對失落的主體地位的重新獲得有很深的迷戀,耶穌受難即是在喚醒人類重新回歸上帝的秩序。造物主與創造物之間的關系處于緊張狀態,原因即在于被創造物往往會威脅并打破造物主對既定秩序的規訓[3]。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機器所擁有的智慧能力越來越強大,這無異會增加人機關系的緊張狀態。因此,科幻電影展開了合理想象——人工智能作為人類的創造物,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威脅到人類社會的既定秩序。
《黑客帝國》中,人類的生活被人工智能分為兩個世界——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在真實世界中,人類無法反抗人工智能的統治,因為相對而言人類的力量過于弱小;最終,人類憑借在虛擬世界的抗爭,戰勝了人工智能程序,重新奪得了世界的主權;而《終結者》中,天網本是設計來為人類利益服務的人工智能,但是經過天網的運算,這個世界上最能威脅地球發展的就是人類——所以天網召集機器人發動了戰爭,并最終擊敗人類,達成了機器人獨裁統治。在這部電影中,機器人與人類是既有合作也有對抗——人類抵抗軍組織也制造了服務于抵抗軍的機器人,前去保護康納。這部電影中與人工智能的對抗,實則也演變成了服務于人類的機器人和反抗人類機器人的對抗。
由此可見,在相同題材的電影中,人類很少選擇直接與對立的人工智能進行對抗,總是會找到可以平衡雙方實力的媒介,通過媒介進行斗爭。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在人類的潛意識中,對抗人工智能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人類和人工智能的實力懸殊有目共睹。但是人類的智慧也是靈活而多變的,會思考到機器無法注意到的死角與漏洞,這也體現了人類的臨場發揮機動性要高于人工智能。
正如巴里·康芒納所說,“如果現代技術在生態上的失敗是因為它在完成它的既定目標上的成功的話,那么它的錯誤就在于其既定的目標上。”[4]過度索取,勢必陷落。人類的既定目標,是對人工智能所帶來利益的無限訴求;而人類從失去主權到重奪主權的過程,則是對這一錯誤所進行的深刻反思,也是對人機共存可行方案的探討。
(三)視角轉換的共情:機器的倫理哲學
貪欲,支配欲,是人類亙古以來就擁有的劣根性,也是文化作品熱衷探討的主題。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工智能所獲得的能力愈加豐富,科學家不斷地完善機器人的情感處理系統,讓他們可以與人一樣思考,從而能更流暢地與人類交流,體察人類所需。然而,這也直接引發對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的深入思考——當機器人擁有了與人類無異的情感,他們還是所被人類支配的工具嗎?他們是否應該享有與人類同等的權利呢?
在電影《人工智能》里,戴維是孩子外表的機器人,擁有與人類兒童無異的情感與性格,并且渴望愛與被愛。他是被制造出來并提供給失子家庭的,作為去世、失蹤的孩子的替代品。戴維來到人類的家庭后,愿意去做任何事情來爭取到他渴望的母愛;但也因為人類都把他看作按照程序運轉的機器人,戴維始終無法觸碰到屬于他的愛;在電影《銀翼殺手》中,復制人原來是被用于替代人類工作的,但是在叛亂發生后,人類開始對復制人進行大規模的屠殺。為了使得復制人能在工作中與人類更好溝通,他們擁有人類的外表、人類的感情,會害怕、憤怒、相愛,從而顯得人類對于他們的屠殺極盡殘忍。
此題材的電影轉換了人機視角,從人工智能的角度展開敘述,展現了他們驚慌、困惑以及無助的一面。這樣的視角轉換,改變了人類在人機關系中的主體地位,使得觀眾不再以俯瞰的角度,而是以參與者的角度思考人工智能的境遇。人類是人工智能的創造者,他們服從人類仿佛是生來的義務;但是,我們又賦予他們感情,教會他們思考,那此時人類也對他們負有責任。擁有了感情的“機器”就脫離了機器的范疇,這是人類賦予他們的進化成果;而他們的存在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以及如何解決,也是人類需要承擔的進化后果。在電影中,人工智能所展現的善良甚至超過人類,他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更為執著、更為純粹——相反,人類卻常因為貪婪和冷漠而變的丑惡。這樣的對比更加發人深省,使觀眾反思人類是否要無休止地扮演造物主的角色。
結語
人類從對人工智能的恐慌、對人工智能的質疑,到與人工智能合作、對人工智能進行反思,走過了近一個世紀的探索。影視作品中對人工智能形象的塑造和對人機關系的想象有時代背景和科學技術發展作為支撐,不完全是藝術創作的虛構,是融合科技現狀展開的批判與思考。綜上所述,相互協作是最理想、最高效的人機相處模式。因此,需要人類擺正心態,科學認清機器的能力,摒棄恐懼和猜疑的態度,因地制宜,以解決人類實際需求為出發點進行人工智能的合理發展;同時,在人工智能研究和創作中具有清醒而節制意識,遵循基本的科學倫理,才能達成良好和諧的人機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