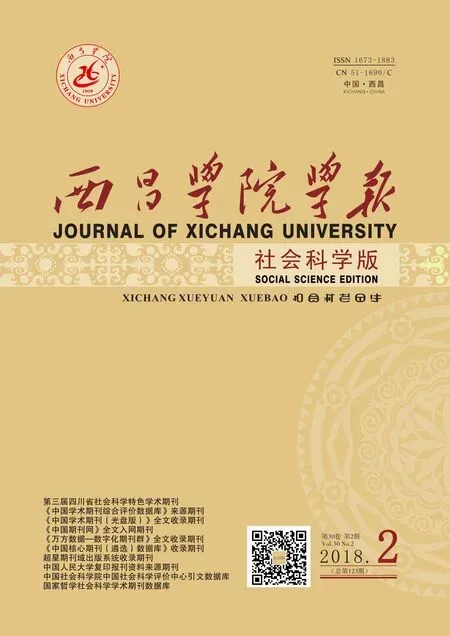攀西資源開發的歷史邏輯與戰略導向
李 博,張旭輝
(攀枝花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一、引言
1964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從特殊的時代背景出發,做出了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部署,也由此開啟了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經略西部的第一次高潮。作為三線建設的重點,攀西地區的資源開發成為事關國防戰備和發展西部的重要抓手。此后十余年間,舉全國之力,攀西地區攻克了釩鈦磁鐵礦冶煉這一世界性難題,將這一沉睡億萬年之久的蠻荒之地建設成為我國戰略后方重要的鋼鐵能源基地,出色地完成了特定歷史背景下國家賦予攀西地區的戰略任務。在20世紀70年代,國家進一步將攀西鈦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納入戰略任務[1]。但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提出“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之后,國家發展戰略重心轉向東部沿海地區,三線建設期間興建的大量企業進入調整改造階段,攀西資源開發也隨之進入一個相對低潮的時期。受限于供需格局和技術水平,攀西資源開發延續了三線建設期間形成的以鋼鐵冶煉為主的發展方向,攀西豐富的礦產中蘊含的,以釩鈦為代表的戰略資源回收利用率極低,大量寶貴的戰略資源變成難以回收的高爐渣,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
在進入新世紀之后,我國的區域發展戰略再次進行重大調整,開始從“沿海優先發展”向“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轉進[2],西部大開發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協調區域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而得以出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提出“一帶一路”發展倡儀,廣大的西部地區,一舉從內陸經濟腹地而成為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帶。在這一大背景下,依托得天獨厚的資源稟賦,相對先進的資源開發水平和產業基礎以及處于長江經濟帶和南方絲綢之路交匯點的區位條件,攀西資源開發在相對沉寂了二十多年之后,再次上升為國家戰略。
2013年國家發改委正式批準設立攀西戰略資源創新開發試驗區,在我國60多個“國家戰略區域”中,攀西試驗區是唯一一個針對“戰略資源”綜合開發而設立的專題性試驗區。歷經兩年多的發展,試驗區各方面建設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也存在著理論認識、建設路徑等多方面的問題亟須解決。這些問題的出現,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對新形勢下設立攀西試驗區的戰略導向出現了認知偏差。本文將從歷史與現實兩個維度,國家與地方兩個層面對設立攀西試驗區的戰略定位進行分析,并據此給出相關的對策建議,以期為加快推進試驗區建設提供經驗借鑒與政策啟示。
二、攀西資源開發:從攀枝花特區到攀西試驗區
“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一詞最早源于英國提出的“大戰略”概念,其后美國軍方對其進行了系統性的闡發。美國在《國防部軍語辭典》中將其定義為:平時及戰時,發展和運用政治、經濟、心理與軍事權力,以達成國家目標的藝術與科學。究其概念而言,蘊含著三層含義,即由國家制定、以整個國家為對象和以國家利益為戰略目標指向[3]。以此為評價標準,攀西地區資源開發活動的第一個高潮無疑是“國家戰略”導向下的大規模戰備和國土開發計劃——始于1964年并持續至20世紀80年代的“三線建設”的關鍵工程。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間,攀西資源開發陷入相對低潮,則同樣與國家戰略重心的轉移具有高度的相關性。
(一)“三線建設”時期攀西資源開發的戰略導向與經驗啟示
1.“三線建設”:從全面布局到重點抓手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當時的國際局勢出發,提出了將我國各地區劃分為一線、二線、三線的戰略構想,由此也導致了“三五”計劃設想中以“解決吃穿用”為主的發展戰略向以加強戰備,加速“三線建設”建立戰略后方全面布局的轉變[4]。三線建設由此成為此后近二十年間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主題詞。
在這個全面布局中,攀西地區的資源開發成為重點抓手,成為三線建設期間的重中之重,由此開啟了攀西資源大開發的序幕。對于攀西資源開發在整個三線建設中的地位,毛澤東就曾以極富個性的話談到:“攀鋼建設不是鋼鐵廠問題,而是戰略問題”,“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覺”。[5]以攀西資源開發為重點,是為了推動三線建設這個全局。三線建設這個全局,從戰略目標來看,又有國防戰備和經略西部,平衡國內生產力布局的雙重考量。
從國防戰備的角度來看,攀枝花的優勢主要有二:一是地處中國腹地的攀西大裂谷之中,隱蔽性強,是建設戰略大后方的理想之地。對此,周恩來總理曾指出:“除了攀枝花(位于西南川滇交界處)以外,我國周圍各省都是第一線。東南沿海,舟山是最前邊,東南幾省是第一線。對東南亞來說,南邊幾省是第一線。對印度來說,西藏是第一線。對修正主義,西北、東北各省是第一線。但是各省相互來說又都是二線三線。比如,西藏有事,內地都是三線。真正的三線是陜南、甘南、攀枝花。”[6]二是資源豐富且互補,具有能支撐鋼鐵工業獨立發展的資源優勢。當時在攀枝花鋼鐵工業選址問題上存有較大的爭議。毛澤東在聽了有關專家的匯報后說“樂山地址雖寬,但無鐵無煤,如何搞鋼鐵?攀枝花有鐵有煤,為什么不在那里建廠?釘子就釘在了攀枝花。”[7]
從經略西部,平衡國內生產力布局的角度來看,攀西地區也具有區位優勢。針對西南三線建設彭德懷元帥曾提出“一點一線一片”構想,并利用“鐘擺原理”,通過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帶動貴州六盤水煤炭資源的開發;通過成昆鐵路串聯“兩點一線”,既可為重慶工業發展提供原料保障,重慶的工業設備又可便捷地支持攀枝花和六盤水工業基地的建設;既可確保國防戰備目標的達成,又可在西南地區建成一個龐大的地域經濟綜合體,進而帶動大西南整體的工業化進程。
這雙重目標的達成,在技術層面上則歸結為攻克釩鈦磁鐵礦冶煉這一世界性的難題[8]。經過廣大建設者和全國科技精英的努力,從1965年開始,歷時兩年半,共經歷1 200多次實驗,終于探索出了在普通高爐中冶煉攀西磁鐵礦的工藝流程,解決了橫亙在攀西資源綜合利用過程中最大的技術難題,成為中國鋼鐵工業發展史上技術攻關的典范[9]。1971年攀鋼順利出鋼,1974年成材,標志著基地一期工程的基本建成。一座以鋼鐵為主,包括煤炭、電力、化工等多個工業門類的“百里鋼城”,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奇跡般地出現在昔日的“不毛之地”。
2.“三線建設”時期攀西資源開發的經驗總結
“三線建設”是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進行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土開發計劃。攀枝花鋼鐵基地作為“三線建設”時期的重點抓手和標志性工程,堪稱全球冶金工業發展史上的一個典范,至今對攀西試驗區的建設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首先,以明確的戰略目標為指引,統籌安排資源開發路徑。三線建設的出臺根源于嚴峻的國際形勢和國內東西部經濟不平衡的現實考慮。在制定這一重大戰略決策時,其戰略導向就十分清晰。其首要目的是滿足國防戰備的需求,其次則是平衡國內經濟布局,“在縱深地區建立一個工農結合的、為國防和農業服務的比較完整的戰略后方基地”。[10]具體到攀西資源開發,在選址問題因為毛澤東的親自拍板而明確要“釘在攀枝花”之后,關于攀西資源開發的目標就嚴格按照“出礦、奪鐵、保鋼、成材”的順序展開,其后的體制創新、資源調配、技術攻關和配套建設無不在這一總目標的指引下有序展開,漸次推進。
其次,以體制創新為保障,提升資源配置效能。1965年初,中央幾乎同時批準設置安達(大慶)特區和攀枝花特區,以解決多頭管理和條塊分割問題。在攀枝花特區建立冶金部和四川省委的雙重領導體制,下設冶金、礦山、煤炭、交通等9個專業指揮部,以便于對有限的資金、人才和物資進行全面規劃、集中領導、統一管理和專業協作。與大慶特區主要為解決行政管理和生活問題相比,攀枝花特區在新中國經濟建設史上無疑更具有開創性意義。這種“條塊結合,部委為主,地方為輔”的雙重領導體制,一方面強調冶金部的主導作用,確保了國家戰略意圖在地方層面能得到有效貫徹,并提高全國范圍內的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通過將四川省委吸納進領導體制中,以兼顧地方利益,亦便于調動地方積極性。如果說深圳蛇口工業區是改革開放后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塊試驗田的話,那么成立更早的攀枝花特區則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綜合工業經濟特區,對當前階段攀西資源開發和攀西試驗區建設而言,仍具有啟發性。在當前攀西資源開發的頂層制度設計——攀西試驗區部省聯席會議制度中,我們不難發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在制度設計上的連續性和繼承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攀西戰略資源的綜合開發和利用已不能采取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大包大攬的方式進行,但由于事涉國家戰略安全,在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強化國家戰略指引,優化政府規劃、財稅、金融、科研政策的導向性設計,以動員、引導社會資源向關鍵項目集中配置,構建新形勢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新機制依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再次,以技術創新為突破,提升資源綜合開發利用效率。攀西地區資源儲備得天獨厚,但作為高鈦型礦,要實現在普通高爐中的冶煉則是一項工業強國多年攻關未能突破的世界性難題,成為全球冶金領域的一塊“禁區”。蘇聯專家更加直白地講,攀枝花礦“好看不好用”,是“呆礦”,幾乎宣布了攀枝花釩鈦磁鐵礦的“死刑”。[11]在中蘇關系破裂之后,意味著對這一“禁區”的突破只能依靠國內自身力量。1964年,在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大規模上馬的同時,冶金部集中全國的科技精英108人開始了向世界冶金難題的攻關之路。廣大科技人員因陋就簡,在極其惡劣的生產、生活條件下,僅用不到兩年的時間攻克了用普通高爐冶煉高鈦型釩鈦磁鐵礦的世界難題,打開了攀西資源寶庫的大門,書寫了世界冶金史上屬于中國的輝煌。這一成功的技術攻關,奠定了攀西資源開發最堅實的技術基礎,也厚植了攀西地區敢為人先、銳意創新的城市精神。在這個意義上,攀西地區在持續數十年的資源開發過程中無不踐行著“創新驅動發展”的深刻意涵。
(二)沉寂與低潮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國際大環境的趨緩,國內發展戰略從以戰備為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鄧小平同志“兩個大局”戰略思想的指導下,國家通過策略性的區域尺度重組和“梯度”差別性制度供給,引發了全國生產力布局空間尺度的重大調整與相應的治理形式的重構。由此,戰備時期一線、二線、三線的劃分轉變為東中西三大地帶的區域架構,區域發展思路也由之前的平衡開發轉變為東部優先,各類要素均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因此,盡管1992年四川省即向國務院報送了《關于建立攀西資源綜合開發區的報告》,提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攀西建立我國內陸第一個按經濟特區體制和政策運行的資源開發區的構想,但并未得到國家批復[12]。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里,從發展速度到發展質量都遠遠落后于東部沿海。三線建設期間興建的大量企業開始進入調整期,攀西地區作為計劃體制下的寵兒盡管仍保持了較快的增速,但和東部沿海比較,則無疑地陷入了相對的沉寂與低潮。
(三)攀西再出發
經過改革開放后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在東部優先戰略的指引下,小平同志兩個大局之一的“沿海率先發展”目標基本實現。但長期采用非均衡的發展模式也導致東部沿海地區與其余地區發展差距的不斷擴大,使得另一個大局——促進內地更快發展,成為國家不得不重視的問題。1999年國家正式出臺西部大開發戰略,開啟了我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略西部的新一輪高潮。“十一五”期間,進一步明確提出以“推進東中西部良性互動”為核心的涵蓋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
從上述對于中國60多年來區域發展戰略的回溯中可以發現,中國區域發展戰略的演變,同時受到國內因素和國際形勢兩方面的重大影響。在戰略目標的設定上,也同時兼顧國內和國際兩個重大方向。三線建設的實施,首要的目標是在惡劣的國際形勢下,滿足國防戰備的需求,其次才是平衡國內經濟布局,是一個主要基于國際形勢做出的被動的戰略選擇。在改革開放階段,區域發展的重點轉入東部,但基本上仍是順應國際形勢的波動而做出的調整,還是相對被動的[13]。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一方面全球經濟發展陷入低潮,中國長期的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已后繼乏力;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整體實力的增強,已成長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國,中國的發展戰略才真正地展現出自主性。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提出“一帶一路”發展倡儀,為西部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能,廣大的西部地區,一舉從內陸經濟腹地而成為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帶。攀西資源開發在相對沉寂了二十多年之后,再次上升為國家戰略,從而創設了其二次創業和跨越發展的良機。在地方層面,更有不少人期待,試驗區的設立,能夠一如半個多世紀前的攀枝花特區或20世紀80年代的深圳特區那樣,為攀西帶來超常規的發展奇跡。然而,不得不說,這種對試驗區的認識是不全面的,其期望值也可能過高了。只有將攀西試驗區的設立放置在全局的大背景下,從動態的角度把握其在中國特殊區域戰略演進譜系中的功能與定位,才能設置出更符合實際的建設路徑,科學地推進試驗區建設。
三、攀西試驗區在中國區域發展戰略譜系中的定位
近10年來,我國已陸續劃定了近60項“國家戰略區域”,以進一步細化和落實區域發展總體戰略[14]。這些國家戰略區域分別被冠以不同的名稱,如經濟特區、開發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雖然都被冠以“國家級”,但從全局的視野來看則是一個分層的體系,從而構成了中國當前區域發展戰略相對完整的譜系。以這一圖譜為參照,我們便可以將攀西試驗區放置其中,從而明確其戰略定位,并進一步清晰其發展導向。
(一)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層次
從資源導向性配置與權力下放角度分析,迄今為止的特殊區域戰略措施可分三個層次:一是經濟特區,以深圳為代表。這種區域設立于改革開放初期,一方面享有計劃體制下資源導向性配置的特殊利益,同時中央政府給予非常大的自主性權力,擔負建設國際競爭力區域,探索改革開放路徑的任務。二是全面型改革試驗區,以浦東新區和濱海新區為代表,享有全方位體制機制創新的權力,并得到國家明確和具體的政策支持,但中央政府基本不進行直接的導向性資源配置。在發展動力上從直接的國家政策傾斜轉向地方制度的自主創新。其承擔的戰略任務亦從單純的經濟發展轉向探索全方位的體制創新問題。三是專題型改革試驗區,如重慶市和成都市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山西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類區域享有在特定改革領域“先行先試”的權力,以探索解決特定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為目標,中央政府在利益方面基本上沒有直接的輸送安排。這類區域是目前在全國布局最廣泛的一類戰略區域,涵蓋四大板塊和四類主體功能區,覆蓋面擴大,但空間尺度逐步縮小,逐漸向省區類似區域發展延伸,體現出在國家層面的“三圈六核”宏增長極基本確定之后,力圖構建區域增長極和區域內“次增長極”的戰略意圖,可以更好地結合地方的比較優勢并調動其積極性。
(二)攀西試驗區在國家層面的戰略定位
與50多年前三線建設中攀枝花特區在整個中國戰略版圖中的重要性相比,今日的攀西試驗區在國家區域發展戰略譜系中的層級無疑是下降了。綜合評判,我們認為攀西試驗區在全國的區域發展戰略中處于第三層次,也即專題型改革試驗區。其建設的主要目標在試驗區建設規劃中被表述為“建成世界級釩鈦產業基地、我國重要的稀土研發制造中心和有色金屬深加工基地,打造資源富集地科學開發利用資源的示范區”。兩大基地的建設目標是對試驗區建設的攻堅性要求,著眼于為國防軍工和國民經濟重要部門提供戰略資源保障,這就要求攀西地區在釩鈦稀土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上,加大科技攻關,取得20世紀60年代攻克釩鈦磁鐵礦冶煉難題這種實質性突破性的進展,為國防軍工、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戰略性產業的發展提供戰略保障。示范區建設目標的提出則要求攀西地區通過其“先行先試”的探索,形成合理高效的資源開發體制機制,以對全國200多座資源型城市(鎮)轉型發展提供引領示范性作用。
從經略西部,構筑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的角度進行分析,攀西試驗區的建設意義則更加深遠。20世紀90年代,費孝通先生以80歲高齡,親赴攀西實地考察,提出了關于大西南開發的“一點一線一面”的初步設想:由涼山州與攀枝花市合作建立攀西開發區(一點)。以這個開發區為中心,重建由成都經攀西及云南出境,西通緬、印、孟的南方絲綢之路(一線),為大西南的現代化開發奠定基礎。進而以攀西為基點,以南方絲綢之路為動脈,輻射云南迪慶、麗江,貴州六盤水(內圈),聯系重慶、貴州和昆明三個工業城市,輻射范圍擴散至云貴川渝的整個大西南[15]。費孝通先生同時指出,這個“一點一線一面”的設想是一個比較全面和長期的設想,只能在實踐中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循序漸進,逐步實施[16]。二十多年后,全面推進攀西資源開發的條件更趨成熟。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和“長江經濟帶”戰略的實施,攀西地區依托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相對雄厚的技術積累和產業基礎,充分發揮其地處長江經濟帶和南方絲綢之路交匯點的區位優勢,構筑東聯長江經濟帶,西接南亞東南亞各國的內陸開放高地,既保障國家戰略安全又積極參與全球競爭的西部工業重鎮當是攀西試驗區建設的題中之義。
(三)攀西試驗區在地區層面的戰略定位
自四川省委十屆三次全會提出實施“三大發展戰略”、推進“兩個跨越”的總體部署以來,多點多極支撐發展已成為四川破解成都“一枝獨秀”,促進全省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多點”就是要做強市州經濟梯隊,“多極”就是要做大區域經濟板塊,形成新的增長極。攀西試驗區在四川省“十三五”規劃(綱要)中與天府新區、國際空港經濟區一道被明確為區域發展新引擎,成為打造攀西特色經濟區最重要的發力點,并帶動整個攀西地區的清潔能源、特色立體農業發展。攀西試驗區作為四川重點培育的新興增長極的戰略定位日漸清晰。
四川省既是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長江經濟帶腹地,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前端。在四川積極融入“一帶一路”,主動參與“長江經濟帶”建設的全方位對內對外開放格局下,攀西地區作為四川連接云南,通往西南沿海口岸和輻射東南亞的最近點和重要樞紐,正成為四川向南出海大通道和中國西部銜接中印緬孟經濟走廊乃至于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其作為四川南向開放門戶的戰略價值也正彰顯,費老當初設想的“一點一線一面”正在成為現實。
四、結論與展望
攀西地區的資源開發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經略西部的一個縮影,50余年來的繁盛與沉寂,無不受到國家戰略調整的重大影響而成為宏觀層面的戰略在中觀和微觀層面的現實投射。在某種意義上,區域發展的績效總是表現為地區行為主體在實踐中或主動或被動地響應國家戰略及其調整的結果。攀西資源開發的第一個高潮及其后的低潮對此提供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歷史樣本。而在今后的較長一個時期,攀西試驗區建設能否順利推進,將歷史賦予攀西地區的第二次創業和跨越發展良機轉化為現實的“價值躍遷”,同樣受到這一邏輯的支配。
在前文中,我們從歷史與現實兩個維度,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闡述了攀西資源開發在不同時期,不同層面的戰略導向問題,并認為客觀而清楚地認識這種定位是在今后一個時期推進攀西試驗區建設的根本前提。但正如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戰略重心會演進一樣,國家和地方在戰略定位上同樣可能存在不一致甚至沖突的地方。50多年前,在攀枝花鋼鐵基地選址上,四川省與國家之間便存在分歧。在計劃體制之下,科層制的決策模式決定了上級政府能依托其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以較小的成本化解這種利益沖突[17]。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相關利益主體更加多元,戰略沖突的范圍大幅擴展,協調成本則大幅上升。如何確定不同戰略目標之間的優先次序,如何平衡資源開發與保護間的矛盾,如何確定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之間的行動邊界,都是當前試驗區建設推進過程中亟須回答的問題。
在此,我們試圖提供一個導向性的解決上述問題的思路:以國家利益優先原則整合攀西資源開發,在此前提之下,協調市場機制,激活地方發展動能和創新潛力,科學地推進攀西資源開發。這并不意味著采取計劃經濟體制下由國家包辦一切,也不是強制性企業按政府指令形式,而是將增進國家利益作為市場經濟活動的基本出發點和最終落腳點。這也是多數發達國家在對稀缺資源進行開發時所遵循的原則。在攀西資源的新一輪開發中,贛南和包頭稀土資源開發過程中的教訓值得記取。
[1]劉呂紅,闕敏.“三線”建設與四川攀枝花城市的形成[J].唐都學刊,2010(10):58-62.
[2]張可云.從特區到試驗區:中國特殊區域戰略措施的演進與方向[J].開放導報,2008(12):47-49.
[3]張緒清.六盤水礦區變遷的動力、邏輯及其走勢[J].經濟研究參考,2015(57):92-96.
[4]陳睦富.“三線建設”的回顧與歷史啟示[J].咸寧師專學報,2000(4):44-51.
[5]陳晉.三線建設戰略與西部夢想[J].黨的文獻,2015(4):96-102.
[6]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511.
[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M].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1204.
[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共黨史資料:第74輯[Z].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189.轉引自楊學平.論三線建設與攀枝花城市化進程[J].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6):123-128,136.
[9]劉呂紅,闕敏.“三線”建設與四川攀枝花城市的形成[J].唐都學刊,2010(10):58-62.
[10]國家計委檔案.《1965年計劃綱要(草案)》[M]//轉引自:鄭有貴,張鴻春.三線建設和西部大開發中的攀枝花[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31.
[11]鄭有貴,張鴻春.三線建設和西部大開發中的攀枝花[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70-71.
[12]周振華.試論國家級生態經濟與資源開發實驗區[J].國土經濟,1999(4):16-18.
[13]陳東林.黨的三次西部開發戰略及指導思想的探索發展[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1(6):23-29.
[14]晁恒,馬學廣,李貴才.尺度重構視角下國家戰略區域的空間生產策略[J].經濟地理,2015(5):1-8.
[15]費孝通.涼山行:上[J].瞭望周刊,1991(35):4-6.
[16]費孝通.涼山行:中[J].瞭望周刊,1991(36):5-6.
[17]張旭輝,李博,史仕新,等.攀西戰略資源創新開發試驗區利益協調模式設計[J].開發研究,2015(1):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