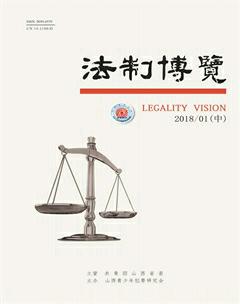刑事行為能力之初探
摘要:透過思考刑法上關于行為能力的意義,以及其在犯罪理論中的地位等問題,分別從作為犯以及不作為犯的角度去說明行為能力的內涵,藉以厘清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的差異,以及其在犯罪評價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試著去界定行為能力在犯罪體系中應該存在的價值以及作用。
關鍵詞:行為能力;責任能力
中圖分類號:D9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8)02-0017-04
作者簡介:許金龍(1964-),男,漢族,臺灣新北人,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學。
何謂行為能力?民法為保護智慮不周之人及維護交易安全,以行為人的意思能力為基礎,依其是否達一定年齡或精神狀態為判斷標準,將行為人區分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以及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三種(參民法通則第16、17條)。然觀之現行刑法典中,僅于第18條至第19條就有關責任能力之事項定有明文,并未有任何關于行為能力之規范,此是否意謂在刑法上無討論行為能力之必要,或者行為能力其實就是責任能力,亦或行為能力另有其他意義,容有加以厘清之需要。
目前司法實務上對于犯罪成立與否的認定,就行為人方面均以「責任能力」為中心,并未涉及行為能力的判斷;至于學術界,就行為能力這個課題專文探討者①,亦在少數,多數學者僅提出零星的簡要論述,并未就行為能力在犯罪體系中的地位加以深入討論。因此,本文擬以三階犯罪理論為基礎,對「刑事行為能力」這個課題,試著探究其在犯罪體系中的意義與地位,首先介紹學說上的見解,其次分別從作為犯以及不作為犯的角度去說明行為能力的內涵,并藉以厘清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的差異,以及其在犯罪評價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提出結論以界定行為能力在犯罪理論體系中的地位。
一、行為能力之意義與內涵
(一)學說介紹
刑法對于行為事實的評價,不論德、日之三階段評價模式,或現行通說所采的四要件評價理論,普遍均未對行為人是否具備行為能力(精確的說法應該是「犯罪行為能力」)乙節,進行評價判斷,司法實務上更是付之闕如。為此本文乃就學界關于行為能力的概念曾為文論述者,分別摘述其要,介紹如下:
1.刑法上的行為能力的概念,乃著眼于行為人在事實上可否支配其外在行止。在概念上,應嚴格區別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因為行為能力系責任能力的前提,故無責任能力未必欠缺行為能力,惟無行為能力則必定欠缺責任能力②。
2.一般所謂行為能力,乃指行為人有能力支配其身體動作而言。凡實際上可自由發動其身體之動靜,其人即具有行為能力,不問其人之年齡、生理或精神狀態如何③。
3.刑法上行為能力系指一個自然人,不論其年齡、精神狀態,基于人類自然的意志力(natuerliche Willenskraeften)一般所附的行為資格而言;其與個人具體的責任能力,自有不同④。
4.舉凡任何自然人,只要具備固定意思之形成能力者,均具「行為能力」。縱令精神病患,仍具備刑法意義上的「行為能力」,其所欠缺者,僅系「責任能力」(Schuldf·higkeit)而已⑤。
5.行為能力,僅指行為人能基于自己之意思而為舉止之能力,并不問行為人是否有違法辨識能力或駕馭能力等責任能力⑥。
6.行為能力是故意犯和過失犯的共同主觀不法要素。當我們依客觀行為是否可以制造風險而判斷行為人的故意時,所檢驗的行為人有無認識,已包含檢驗了行為人的認識能力,行為人必定被假設成有認識能力,才可能認為它應該對可能實現構成要件的風險有認識,而在檢驗行為人的意欲時,意欲包括意思決定和行為決定,如果欠缺行為能力,行為決定是有瑕疵的,故意也可能因此被推翻,這種檢驗故意犯而推翻故意認定的程序往往隱藏在行為能力欠缺而否定過失的檢驗程序當中,因為連過失都沒有,當然也就沒有故意⑦。
7.一般所謂行為能力,乃指行為人有能力支配其身體動作而言,凡實際上可自由發動其身體之動靜,其人即有行為能力,而不問人之年齡、生理或心理狀態如何⑧。
(二)本文見解
刑法上之行為概念,因時代的變遷及學者間的見解之互異,而有不同的理論產生。然在各種行為理論之間,除身體動靜說外,不論實行因果行為論,或社會行為論,或目的行為論,甚或個人行為論者,皆認刑法上之行為系以得由人類之意思支配或可能支配、控制的活動,為其立論之基礎。由于身體動靜說者,認為人表現于外表的身體動靜,就是行為,因此縱非出于有意的或目的的意思所實施的身體動靜,例如,反射動作、睡眠中的動作、無意識的動作或是絕對強制下的動作等,都可以認為是行為⑨。學者有認為此說之主張忽略了人之行為(身體動靜)之得以成為刑法評價之對象,乃因為該行為受到人之意思之支配或有支配之可能,若將與人之意思毫無關聯性之反射動作等亦視為刑法評價之行為,實無意義,亦與一般人所理解的做為刑法處罰對象之行為有落差⑩。本文以為,刑法行為理論所要闡明的問題,并不是法律判斷或評價的關系,也不是刑法如何認定犯罪的議題,而是要決定什么樣的人類舉止,可以做為刑法判斷的對象,什么樣的人類行止,刑法才會感到興趣。也就是說,行為理論主要的任務,是要界定人類的行為舉止,必須具備何種條件,方才具有刑法上行為的適格,進而成為刑法評價的對象,以做為是否成立犯罪的判斷基礎。因此,必然系人類有意識支配或控制下的行止,刑法才會感興趣,也才是具有刑法上意義的行為;而那些欠缺人類自主意識的行為,并非刑法評價的對象,自非屬刑法上行為的范疇,當以排除。故而身體動靜說主張保留至構成要件主觀要素該當的評斷時,才處理刑法上行為適格與否的問題之見解○11,顯然仍有討論的空間。
從而,刑法上之行為應系一種人類認知意思下的活動,故有學者將刑法上行為之要素,區分為「心素」與「體素」兩種○12,原則上應可贊同,惟本文以為,刑法上行為應是由「人」與「外在動作」結合而成的產物,而此之「人」應包含兩種意義(或要素):一為主觀意義,另一為客觀意義。所謂主觀意義,即指「心素」而言,乃行為人對其客觀外在身體的動作有所認識,亦即行為人清楚認識其在做什么事情,因系從行為人心理的認識出發,故為一種主觀要素,例如夢游者因欠缺心素,其行為自非屬刑法上之行為。另所謂客觀意義,則系指『行為能力』而言,蓋一個人類有意識支配或控制下的行止,除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心素外,尚以客觀上具備足以完成或成就外在身體動作的能力為必要,故而,刑法上行為能力的概念,顯然系指「人」對于完成或成就其「外在動作」的一種地位或資格(一般在法律上所稱的能力,系指「地位」或「資格」而言○13),而此種地位或資格系客觀存在的條件,幾乎無法由人類加以控制,自與主觀的心素有所不同,而成為客觀構成要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endprint
據上所述,本文認為刑法上所謂「行為能力」,系指行為人客觀上足以完成或成就外在身體動作的資格。行為能力之有無,應以行為人客觀上所具備的條件做為判斷基礎,與行為人主觀上的認知無關。因此,在從事犯罪判斷的過程中,關于構成要件行為的檢驗,實際上即隱含著對『刑法上行為(即一般所指的心素、體素二要素)』與『行為能力』二者的判斷。因為倘若沒有行為的發生,就不可能涉及行為能力的問題,且因為行為人具備有行為的能力,才會有造成行為發生的可能,所以,行為能力是行為發生的前提,若沒有行為能力,自然不會有行為的產生;反面言之,若有行為的發生,行為人必然具備有行為能力,絕不可能認定存在有刑法上之行為,卻得出行為人欠缺行為能力之結果。從而,在檢驗某個人的舉止是否為刑法上行為時,是無法忽略行為能力判斷之問題的,假如將行為與行為能力強予分割處理,必然會對是否屬于構成要件行為的判斷,產生一定不當的影響,甚至可能造成評斷上的錯誤。
二、作為犯之行為能力
作為犯,是指構成要件設定成立犯罪的行為形式,必須是以積極的作為方式,方能夠成罪的構成要件類型。通常刑法的構成要件,都是以作為的方式,作為對行為實現犯罪的要求○14。而作為犯依構成要件內容的實現與否,又可區分為既遂犯與未遂犯。因行為能力的內涵,既然系指行為人一種客觀存在的能力,則于作為犯罪之情形,行為人亦存在是否具備行為能力之問題,本文以下擬從既遂犯與未遂犯之情形,分別予以討論。
(一)既遂犯之行為能力
既遂犯,系行為人的行為已經完全實現構成要件內容的一種犯罪型態。在作為既遂犯之情形,顧名思義,行為人必已完成構成要件之行為,始足當之,則既有構成要件行為的遂行,表示行為人本身在客觀上已然具備有完成或成就刑法上行為的能力,否則一個欠缺行為能力的人,如何仍能遂行所謂構成要件行為。因此,對于作為既遂犯而言,構成要件行為該當的判斷結果,實際上已包含對行為人客觀行為能力的肯定;換言之,構成要件行為既然已獲得實現,行為人客觀上是否存在有行為之能力,顯然已不具任何特別的意義。所以,行為能力在作為的既遂犯之情形,似乎已不見其實益與價值。
(二)未遂犯之行為能力
未遂犯,是指已著手于犯罪行為的實行,而尚未完全實現構成要件內容的犯罪型態。凡是屬于客觀不法構成要件之任一要素沒有實現,就是犯罪未既遂,不限于構成要件該當結果的未發生,尚包括行為人已著手實行構成要件行為,但仍未完成實行行為的情形在內。因此,在討論未遂犯的行為能力時,亦須針對實行行為是否已完成之情形,分別論之:
1.當行為人已完成構成要件行為的情形,必然行為人客觀上已具備有完足的完成或成就外在身體動靜的能力,想當然爾,此時與作為既遂犯相同,對于構成要件行為該當的判斷結果,實際上亦已隱含對行為人客觀具備行為能力的肯定,因此,行為能力在此亦無討論的實益與價值。
2.至于行為人已著手實行構成要件之行為,惟因故未完成實行行為的情形。于此,行為人之所以未完成實行行為,可能出于悔悟自動放棄或外來因素之障礙,亦可能因本身實行能力的不足(例如甲欲炸死仇人乙,乃偷取某軍藥庫炸藥一批,并暗布于乙住處,惟于擬引爆時,始發現不知如何引爆炸藥)而不遂。后者即為行為能力欠缺之態樣,由于行為人客觀行為能力的不足,致無法完成實行行為,而使結果不能發生,且因該著手行為在客觀上并無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亦即無任何侵害法益的危險性。因此,在行為人已著手于實行構成要件之行為,卻因本身欠缺完成實行行為的能力,而未完成實行行為之情形,即屬不能未遂,而且是所謂的『主體不能○15』的未遂。故而,行為能力在作為未遂犯中,其實就是在討論不能犯中關于主體不能的問題。
三、不作為犯之行為能力
不作為犯,是指以不作為的方式所遂行的犯罪。所謂不作為,并非單純指身體的靜止狀態,而是指不為規范所要求或期待的一定作為。自規范的立場而言,刑法規范有要求國民為一定的行為者,亦有禁止國民為一定的行為者。前者,稱為命令規范;后者稱為禁止規范。對于命令規范,如有不服從該命令時,刑法即以不作為犯的方式加以處罰。又不作為犯,就其犯罪結構的不同,學理上將其區分為真正不作為犯(又稱純正不作為犯)與不真正不作為犯(又稱不純正不作為犯)二種。真正不作為犯,是指構成要件規定只能以不作為方式實施的犯罪。例如,遺棄罪(刑法第261條)、拒不提供間諜犯罪證據罪(刑法第311條)等。此等犯罪,因違反「扶養」、「提供」之命令,所以是違反命令規范而成立的犯罪。而不真正不作為犯,則是指刑法分則原本以作為形式規定的犯罪,行為人以不作為的方式實施的情形○16。例如,故意殺人罪(刑法第232條),在構成要件上所規定的行為,是「殺」的作為行為,行為人卻以不作為的方式,例如故意不給小孩食物,而將其餓死的情形,違反「不能殺人」的禁止規范。所以,不真正不作為犯,是違反禁止規范而成立的犯罪。然而無論依何種行為理論,都承認必須有身體的動靜存在,始能成為行為。而身體的動態,已引起外界事物或現象的變動,固得認其為行為;然身體的靜止狀態,并未引起外界事物或現象的任何變動,可否視其為行為,則頗受議論。惟自規范的立場觀察,規范命令行為人應為一定的動作,行為人竟然違反命令而不為一定的動作,違背規范的要求,自有其可罰性。所以,所謂不作為,并非屬于單純「不為」的身體靜止狀態,而是「有所不為」,也就是不為規范所期待的一定作為。
又依前所述,行為能力乃指行為人客觀上足以完成或成就外在身體動作的資格。而這個外在身體動作,從犯罪的評價的角度以觀,自然系指構成要件行為而言。因此,作為犯的行為能力,顯然系指行為人客觀上足以完成或成就構成要件行為的能力。然而在不作為犯的情形,由于法規范對于不作為犯的期待既然系一個「應為行為」的期待,該被期待的行為自是一個法規范所容許的行為,則行為人有無遂行該期待行為的能力,顯然與作為犯客觀上是否足以完成或成就構成要件行為的「行為能力」有別,并非同一之概念。至于所謂的「作為能力」,主要系在探討不作為犯的「作為可能性」之問題,亦與行為能力的意涵不同,二者亦不可等同視之。基此,本文乃認為,不作為犯實際上并不存在有無行為能力的問題,行為能力在不作為犯的領域,并無任何意義。所以,在從事不作為犯之犯罪判斷時,根本就不包含行為能力的檢驗在內。endprint
四、結論
綜合以上論述,足見行為能力并非民法上獨有的法律用語,在刑法領域中,仍然存在有行為能力的問題,而也因為刑法上的行為能力系一種客觀的不法要素,自與屬于罪責要素的責任能力有別,二者不容混為一談。另外,由于在不作為犯中「不作為」的本質使然,不作為犯僅有作為能力存在與否的問題,根本就與行為能力無關。至于在作為犯的情形,既遂作為犯在客觀上已實行了構成要件行為,行為既已完成,行為人必然具有行為能力,此時再去討論有無行為能力,自然是毫無價值與意義的;相較于此,行為能力在未遂作為犯似乎比較具有探討的空間,然而仍逃不脫被不能犯所取代的命運。或許因為行為能力天生宿命如此,所以立法者不愛,學說實務界對其亦形同陌路。本文在此,對刑事上行為能力這個命題提出個人初步研習的看法,主要目的在一解個人學習刑法過程中的疑惑,想法與結論也許不盡成熟而仍有討論的空間,但經由這樣的腦力激蕩,個人的收獲還是匪淺,當然期盼藉由本文的提出,拋磚引玉,希望會有其他不同面向或見解的導入,可以彌補足本文論述的不足或盲點,以獲取更大的學習成果,這正是本文論述目的之所在。
[注釋]
①許玉秀.主觀與客觀之間[Z].臺北:春風煦日論壇-刑事法叢書系列1997,9:179-218.
②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Z].臺北: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圖書部,2008,1:205,382.
③蔡墩銘.刑法上犯罪判斷與實例[M].臺北:漢林出版社,1987,6:85.
④蘇俊雄.刑法總論Ⅱ[Z].臺北: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圖書部,1997,7:42.
⑤黃常仁.刑法總論-邏輯分析與體系論證[M].臺北:漢興出版有限公司,2001,8:13-14.
⑥陳子平.刑法總論[M].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5,9:317.
⑦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M].北京:中國民主法治出版社,2005,11:35.
⑧靳宗立.刑法之傳承與變革[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10:201.
⑨甘添貴,謝庭晃.快捷方式刑法總論[M].臺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6:56.
⑩陳子平.刑法總論[M].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5,9:111,112.
○11甘添貴,謝庭晃.快捷方式刑法總論[M].臺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6:57.
○12蔡墩銘.刑法總論[M].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3:95.
○13甘添貴.刑法總論講義[M].臺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9:164.
○14柯耀程.刑法摡論[M].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4:135.
○15一般學說上稱主體不能,系指行為人具有實施身分犯的意思,但其并不具備特殊身分,因而不可能成立身分犯而言(參閱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1:352).如采此見解,在理論上欠缺行為主體身分者,在犯罪行為確認的前提上,已經不適格,根本無由成立犯罪,何來論以不能未遂之理?(參閱柯耀程.刑法摡論.臺北市,自版,2007,4:336)因此本文認為所謂主體不能,系指行為人不具備行為主體所應有的行為條件或能力而言,且此條件不包括身分欠缺在內.基于這樣的定義,則因行為能力的欠缺所成立之未遂犯,實際上就是指主體不能的不能犯.換言之,欠缺行為能力所成立的未遂作為犯,基本上就是在討論主體不能的問題.
○16周光權.刑法總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3:107.
[參考文獻]
[1]甘添貴.刑法總論講義[M].臺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9.
[2]甘添貴,謝庭晃.快捷方式刑法總論[M].臺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6.
[3]許玉秀.主觀與客觀之間[Z].臺北:春風煦日論壇-刑事法叢書系列-0,1997.9.
[4]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M].北京:中國民主法治出版社,2005.11.
[5]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Z].臺北: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圖書部,2008.1.
[6]蘇俊雄.刑法總論Ⅱ[Z].臺北: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圖書部,1997.7.
[7]柯耀程.刑法摡論[M].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4.
[8]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1.
[9]周光權.刑法總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3.
[10]陳子平.刑法總論[M].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5.9.
[11]黃常仁.刑法總論-邏輯分析與體系論證[M].北京:漢興出版有限公司,2001.8.
[12]靳宗立.刑法之傳承與變革[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10.
[13]蔡墩銘.刑法上犯罪判斷與實例[M].臺北:漢林出版社,1987.6.
[14]蔡墩銘.刑法總論[M].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