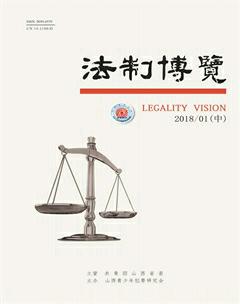兩份公證遺囑引發的糾紛
摘要: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與生活的發展,各種遺囑糾紛不斷出現。公證遺囑作為一種相當重要的遺囑形式,其對于穩定遺囑市場方面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國的公證遺囑本身存在有諸多缺陷,這就導致了公證遺囑糾紛也難以避免。在文中就對兩份公證遺囑引發的糾紛進行分析,以期為解決類似糾紛提供借鑒。
關鍵詞:公證遺囑;糾紛;賠償
中圖分類號:D92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8)02-0152-01
作者簡介:郭守敏(1979-),女,漢族,江蘇南京人,研究生在讀,江蘇德本律師事務所,律師,民商法專業。
一、案情簡介
原告系被告的妹妹,王某系原、被告的母親,于2002年5月死亡;張某系原、被告的父親,于2013年10月死亡。
1998年4月,張某買下位于某區芳華園23號101的房產(即案涉房屋),登記在張某名下。2001年5月21日,張某及王某申請遺囑公證,將案涉房屋交由原告、被告及案外人張丙(原、被告的哥哥)共同繼承。
2003年3月,張某再次申請遺囑公證,將案涉房屋交由被告和張丙共同繼承。2003年5月23日,張某與被告簽訂《買賣契約》,將案涉房屋出售給被告,成交價為15萬元,同期房屋變更至被告名下,張丙對本次房屋轉讓知情且認可。2011年3月4日,被告與案外人李某簽訂《存量房買賣合同》,約定以133萬元價格轉讓案涉房屋。隨后,房屋轉移登記至李某名下。
2017年3月,原告訴稱:因現已無法根據公證的遺囑繼承案涉房屋的相關權利,故訴至法院,請求判決被告賠償相關損失25萬元(含房屋價款和利息)。
二、爭點
沒有進行遺產分割的情況下,能否直接要求賠償損失?起訴是否已超過訴訟時效?被告主體是否適格?賠償的計算依據應該是什么?
三、裁判
被告辯稱,自2001年5月雙方父母進行遺囑公證至今,案涉房屋已經兩次買賣,產權人自2003年5月開始就已變更。不動產物權以登記為準,該登記具有公示、公信力,侵犯繼承權的訴訟時效應自2003年5月起算,起訴已超時效。但法院認為,被告亦認可原告是2016年得知父親生前將案涉房屋轉移登記至被告名下,后被告又將該房再次出售,故本案的訴訟時效期間應從原告知道房屋被轉移登記時,即2016年起算。
另被告辯稱,案涉房屋的處置是父親張某所為,即使存在侵權,也應由張某賠償。法院則認為,2011年3月的受讓人李某,通過中介購買房屋,支付了市場價,進行了產權變更登記,屬于善意取得。原、被告無法通過訴訟程序追回房屋,因此原告也就無法通過繼承取得相關權利,而該結果系被告所致,其理應承擔相應責任。
被告還主張父親張某以15萬元將房屋出售給自己,即使賠償損失,也應以15萬為依據。因為侵權只可能存在于第一次產權變更時,再次變更是被告對自己產權的有權處分。法院則認定,原告無法通過繼承取得相關權利,根本原因是被告再次出售房屋。此時,被告最終侵犯了原告的財產繼承權,故原告要求以再次轉讓時的價格進行賠償是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
綜上,原告根據其母親王某的公證遺囑依法享有案涉房屋的繼承權,同時其未明確表示放棄繼承。被告在父親將房屋轉移登記后,再次將房屋另行出售,被告的行為侵害了原告的財產繼承權,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故判決:被告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原告25萬元。
四、評議
因為作為遺產的房屋已被轉讓給善意的案外人,遺產分割事實上不能進行,所以直接訴請賠償損失是沒有法律障礙的。
產權登記起著物權變動的公示作用,該登記具有社會公信力。但能否因此推定所有民事活動相關人知道或應知道權利人是誰?無論從法律規定或法理推演角
度,還是民事活動的實踐,如此推定都是沒有根據的。具體到本案,作為繼承人之一的原告,法院認定其提起訴訟的時效起點就是實際知道侵權事實,而不是根據產權登記簿。
最后,對原告為什么能判如所請,根本原因還是:后來的公證遺囑可以撤銷之前的公證遺囑,但遺囑只能處分自己的財產。因為母親王某至死沒有變更遺囑,則2001年5月21日的公證遺囑就是王某遺產繼承的最終依據。而父親張某的遺產則應根據其2003年3月的公證遺囑進行分割,對該部分財產,因為張某改變遺囑,原告喪失繼承權。
遺囑自由是私法自治在繼承法上的表現,其含義包括遺囑行為自由、遺囑內容自由、遺囑形式自由。遺囑行為自由又包括遺囑設立自由、遺囑撤回自由。《繼承法》第20條第1款規定:“遺囑人可以撤銷、變更自己所立的遺囑”,此處的撤銷指撤回,遺囑人可以在生前任何時間進行。各種形式的遺囑中,公證遺囑的效力最高,但也是可以變更、撤銷的。撤銷公證遺囑的方式有:
一、作出新的公證遺囑;
二、作出撤銷遺囑聲明書,并對發表撤銷遺囑聲明書的行為進行公證。
最后,為避免將來糾紛,立遺囑者最好選擇公證遺囑,因為法律規定數份內容矛盾的遺囑,以最后所立公證遺囑效力為最高。
[參考文獻]
[1]張鳴.公證多元化參與遺囑法律服務的思考[J].中國公證,2016(09):58-62.
[2]任博峰.公證遺囑形式之法律問題研究[J].法制與社會,2013(17):277-27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