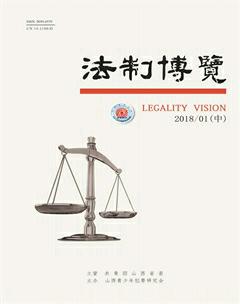淺談我國《民法總則》“成年監護”制度中的問題與完善措施
摘要: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民法總則》創新性的規定了成年監護制度,滿足了社會發展的需求,為完善成年監護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然而,《民法總則》在確定監護人和監督機制問題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針對確定監護人的問題,《民法總則》可不強制性規定監護人的順序和范圍,而應由成年人基于自由意志選定監護人。針對監督機制,可規定專門的監護監督管理機關,例如由民政部或基層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負責,更為適宜。
關鍵詞:成年監護;被監護人;監督管理機關
中圖分類號:D9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8)02-0159-02
作者簡介:任輝(1989-),女,漢族,河南南陽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2017級民商法專業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知識產權。
2017年10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民法總則》借鑒了《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成年意定監護制度,在第二章第二節規定了監護制度,不僅包括未成年監護,還包括成年監護。該規定相較于《民法通則》,有較大進步,基本實現了從立法層面對監護制度進行改革的目標,構建了相對完善的成年監護制度體系。然而,此部分規定仍有值得推敲和完善之處。筆者擬通過本文對這一制度取得的進步與不足之處進行具體闡述,并提出進一步完善的建議。
一、我國成年監護制度發展的現狀
伴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口老齡化已然成為21世紀不容忽視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我國于1999年正式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是第一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發展中國家,老年人監護制度需求日益凸顯。例如由于目前養老制度不健全以及養老機構的稀缺、費用過高等問題,致使老年人養老問題無法得到合理的解決,進一步凸顯出設置成年監護制度的必要性。
我國傳統民法中的監護制度,其根本出發點在于確定被監護人的財產代管人,結束被監護人的財產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從而維護交易安全。基于此,1986年《民法通則》規定了監護制度,其對象僅限于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卻并未提及成年監護。在民事特別法的規定上,2015年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26條規定了老年人意定監護制度,該規定彌補了我國老年人監護制度的漏洞,同時也為《民法總則》設定成年監護制度,提供了可借鑒的藍本。然而,其他法律卻均未涉及成年監護問題。
綜上,從我國社會整體需求和立法欠缺兩方面來講,完善成年監護制度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此次制定的《民法總則》雖然規定了成年監護制度,然而該規定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
二、《民法總則》“成年監護”規定中的不足之處
(一)《民法總則》對監護人確立的規定存在矛盾之處
傳統監護制度忽視被監護人的意志,原則上是監護人的意思優先。世界性的成年監護制度改革,目的在于追求“尊重本人自我決定權”“維持本人生活正常化”和“保護障礙者本人”的基本理念,以“自治式”的意定監護為主,理念先進、制度優化。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對于老年監護制度的改革,體現了這樣的理念,積累了立法經驗,成為《民法總則》改革成年監護制度的借鑒藍本。此次《民法總則》第33條對監護人的選擇的規定,原則上體現了尊重被監護人真實意愿的立法導向。然而第28條又規定了選擇監護人的順序。法條如此規定,限制了成年人確立監護人時的選擇權,或許也非完全基于成年人的真實意愿。
首先,成年監護制度追求“尊重本人自我決定權”的立法理念,亦即充分尊重被監護人個人意愿來選擇監護人。然而《民法總則》在規定尊重意愿的基礎上,又規定了監護人的選擇順序和范圍,這無疑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了被監護人的選擇權,更與“尊重本人自主決定權”的立法理念相悖,顯然存在不妥之處。
其次,法律規定成年監護監護人的選擇順序和范圍,實踐中將會給老年人監護人的確定造成一定的困境。隨著年齡的增長,在老年人逐漸喪失意思能力而成為限制或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而需要設定監護人時,若依《民法總則》之規定,其有監護能力的配偶便是其第一順位監護人,其父母、子女系第二順位監護人,然而此時,其配偶、父母等一般也已屆高齡,適用這樣的規則在現實中所選擇確定的監護人,可能無法充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那么也就無法實現成年監護制度的立法目的。
由此可見,設立一套合理可行的成年監護制度尤為重要。老年人在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時,其自愿選擇由《民法總則》規定的監護人范圍以外的且更有利于保障其合法權益的其他人或組織來擔任監護人的,筆者認為也并無不妥。
(二)成年監護缺乏監督機制
《民法總則》第33條的規定,從最大限度保障被監護人合法權益以及尊重被監護人意愿角度出發,這顯然是一個較大的進步。然而,《民法總則》卻未對監護協議生效后,在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過程中由誰進行監督,以及產生糾紛后如何解決作出具體規定,即缺乏監督機制,不可不說這是一大疏漏。成年監護不同于未成年監護,由于被監護人喪失意志能力,其很多權利均由監護人代為行使。而任何權利的行使都需進行制約,更何況由于被監護人行為能力的喪失使其很難依靠個人意志有效捍衛自己的權利。因此,在監護協議生效之后,當監護人違約或侵害被監護人權益時,依照現行法律規定,被監護人并無合理的救濟途徑。
因此,從司法實踐層面來講,立法需制定配套的監督制度。否則,若任由監護人肆意行使權力而無限制,成年監護制度可能會失去其最初設立時的意義,更不利于該制度的實施。
三、針對《民法總則》“成年監護”制度進行完善的建議
(一)成年監護監護人確定的順序和范圍不應受親屬關系的限制
《民法總則》目前對成年監護監護人的規定仍系以親屬關系為基礎,從實踐層面來說,難謂妥當。筆者建議,立法可不強制性規定監護人的順序和范圍,只要被監護人選擇的監護人系基于其真實意愿且系最大限度維護其合法權益,不違背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即可,法律并沒有必要過多干涉私人范疇內的事情。只是,作為保障公民權益最后一道屏障的法律,需要規定糾紛解決機制以保障公民權益受到侵害后可得到有效救濟。
(二)明確成年監護監督管理機關
關于成年監護監督管理機關,日本《任意監護合同法》第3條規定:“為了保證本人締結合同時的意思能力,任意監護合同必須要通過公證證書的方式進行”。對于具體的形式要件要求,則有公證、監護管理機關登記、法院登記等多種立法例。針對我國目前的情況,可以選擇采用以下方式確定監護監督管理機關:1、由民政部來專門承擔監督管理職責;2、由基層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來承擔監督管理職責。由于成年監護屬于私法范疇且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因此,筆者認為,成年監護監督管理職責由民眾較為熟悉的機關或組織,例如民政部或基層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來承擔,更為適宜。
綜上,由法律規定專門的監護監督管理機關,不僅能夠使《民法總則》監護制度體系更加趨于完善,而且在監護人違反約定或者實施侵害被監護人權益行為時,可解決被監護人自身救濟不能的問題,也符合成年監護制度的立法宗旨。
四、結語
從整體上來看,此次《民法總則》規定的成年監護制度,符合社會發展趨勢,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人權保護的理念。然而,《民法總則》規定的成年監護制度僅是理論層面的一個框架,卻未規定其在司法實踐中的操作規范,比如被監護人基于自由意志選擇的監護人若遵照法定的順序和范圍,是否符合“尊重本人自我決定權”的立法理念?再如監護協議生效后的監督機制,以及因履行監護協議產生糾紛后當事人救濟的問題。因此,在監護人的選擇上,建議可遵照當事人意志自由選擇監護人,針對監督機制,建議立法可規定一個專門的監督管理機關來完善監護制度,從而實現該制度的立法目的。
[參考文獻]
[1]楊立新.我國<民法總則>成年監護制度改革之得失[J].貴州省黨校學報,2017(3).
[2]滿洪杰.<民法總則(草案)>成年監護制度的問題與不足[J].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報),2016(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