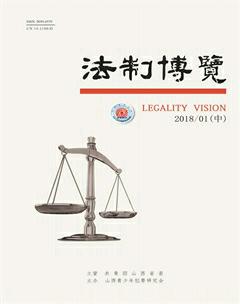比較法視野下我國應訴管轄制度的構建
摘要:民事訴訟中管轄問題本是一個細節性問題,但在司法實踐中,管轄問題卻往往成為影響案件進程和結果的關鍵性問題。應訴管轄作為新增設的制度,在國內司法實踐中尚無豐富的經驗可尋,必然需要在借鑒不同法域應訴管轄制度的立法例與實踐現狀的基礎上,同時求助學術界研究意見,從而不斷完善達到符合我國國情的制度要求。
關鍵詞:應訴管轄;比較法;適用條件;告知程序
中圖分類號:D92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8)02-0164-02
作者簡介:劉璐(1993-),女,漢族,山東淄博人,貴州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訴訟法學。
一、應訴管轄的適用條件
由于域外地區與我國在民事訴訟體系上具有較大差異,具體表現在應訴管轄制度即適用條件的不同。總體來看主要有以下差別:
第一,被告“默示同意管轄”的行為方式。以日本為例,日本立法規定被告允許以辯論或者陳述的方式來確認管轄權,口頭或者書面形式都可以成立應訴管轄。同時規定被告須在初次出庭日提交書面答辯狀且出庭參加辯論,即不僅要求被告沒有提出管轄權異議同時還要求在初次出庭日,參與應訴答辯,兩個條件缺一不可。但德國立法則僅認可被告的言詞辯論的方式。
第二,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時間段。日本與我國臺灣地區均對此做了明確規定,在兩種情況下可認定為應訴管轄:一種是在第一審法院被告沒有提出管轄權異議并且進行言詞辯論;一種是被告在準備程序中未提出管轄權異議且對實體性問題所做的言詞辯論也可以認定為應訴管轄。但在德國立法中沒有相對明確的規定。
第三,成立應訴管轄的階段。德國、日本均對被告沒提出管轄權異議也沒出庭應訴的情形與被告提出管轄權異議又出庭應訴的情形做出了規定。以日本為例,對于前一種情形,雖然法院無管轄權被告有參加訴訟的權利,但是這時由于被告缺席原告可以向法院主張“擬制自認”,就是將被告的缺席擬制為對原告主張的自認,從而使受訴法院取得管轄權。但在德國,被告缺席不能適用應訴管轄。對于后一種情形,如果被告在提出管轄權異議后又出庭應訴答辯的,只要應訴答辯的內容是關于實體性問題的,即視為被告放棄提出的管轄權異議。
在上述對比中,我國對于以上國家“默示同意”應訴管轄的行為方式不可貿然借鑒,主要理由如下:其一,上述各國的應訴管轄制度是在答辯失權制度基礎上規定的,即便是我國也建立答辯失權制度,不同國家便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國情,我國也不能亦不能想當然的借鑒。以德國、日本民事訴訟來講,若是只提交書面答辯狀,但沒有在初次出庭期日參加言詞辯論,這時即發生答辯失權。其二,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期間界限相對明顯,但德日規定的口頭辯論期日制度把起訴到做出裁判的整個過程都叫做“言詞辯論階段”,這就使得就算我國響應一些學者的建議增設答辯失權制度,也不能借鑒以上國家的規定。
二、應訴管轄的適用范圍
應訴管轄的適用范圍與其他國家有較多的一致性。首先,在適用法院的方面,上述國家與地區都規定法院不得違反專屬管轄,但各國對專屬管轄案件的種類不盡相同。由此可得,專屬管轄具有較強的程序剛性。同時,多數國家應訴管轄制度適用的訴訟類型僅能是關于財產類的案件,不包括關于人身性質的案件通過合意來確定管轄權。現理論界對于應訴管轄的適用范圍總體概括為兩個觀點:一是財產爭議類案件①;二是在適用第一種的基礎上,適當的擴大部分財產權益的人身關系案件。筆者認為,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行為主宰,既享有行為自由同時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應訴管轄制度正體現了這一點,由于當事人的特定行為從而產生具有訴訟效果的法律行為,充分體現了當事人對自己權利的處分權。但涉及人身權的案件,通常與當事人權益具有相對密切的關系,關乎社會秩序與公序良俗,需要法律來嚴格制約對人身權處分的行為。財產類案件則不會有這樣的情況,通過當事人權衡利弊并做出真實的意思表示來接受管轄權,使矛盾以雙方均便利的方式得以解決。若要擴大部分財產權益的人身關系案件,還需結合中國國情加以審慎思考與探討。其次,日本法中并無明文規定不得違背級別管轄,在《日本民事訴訟法》第16條第二款中規定,地方法院和簡易法院可以互相適用應訴管轄。
目前應訴管轄適用范圍大體概括為兩個立法路徑:一種是把適用案件的范圍限定在合同及其財產類;另一種是采用篩選的方式,將非財產類過濾在適應范圍之外。我國民訴法采用的是第二種,在不違反專屬管轄與級別管轄的情況下可以適用應訴管轄制度,但沒有從正面規定哪些類型的案件可以適用應訴管轄制度。就我國而言,從體系結構看,應訴管轄的規定置于第34條(管轄協議)之后似乎更為適當。②立法者的本意也是趨于將應訴管轄的設定條件同明示管轄協議相
類似,但依照第127條來看,顯然應訴管轄的適用范圍遠寬泛于明示管轄協議。
通過對比域外法律,我們可以看出法律的制定依據在一定程度上要依據國際性的原則,閉門造法所制定的未與國際接軌的法條,必定舉步維艱。自負啃書不如謙遜討教,在結合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取諸法之長,增加國內法與國際法的互相,在它們之間尋求一個合理的平衡點。
三、適用應訴管轄的告知程序
在現有國家的法律中,法院的告知程序僅有德國對此有明確規定。我國增設應訴管轄后,最高法在兩本解說書中都有涉及應訴管轄有必要學習德國的“法院告知義務”的問題。如:“考慮到我國民事訴訟的當事人訴訟能力相對不足的事實,我們應該借鑒德國法的規定,向受訴法院規定釋明義務,現在立法層面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將來有必要在司法解釋層面明確。”③司法活動中,我國不是強制聘請律師的國家,當事人并不充分了解立法現狀以及法律知識,時常有不知情或者不知法律行為所產生的后果而出庭做出答辯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若是推定當事人認可法院具有管轄權,則可能違背了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德國的“由于不責問而生的管轄”在第504條明確規定法院的告知義務,保障了當事人的權利,并且避免了程序反復所帶來的司法資源的浪費。但德國在該制度上也有特殊性,州法院則沒有這種規定。但如若被告沒有代理律師且自己對專業知識不了解,此時規定法院履行告知義務才顯得更具意義,符合建立法院告知義務程序的立法初衷。
該程序的確立還有效的保障了當事人的訴訟知情權,避免不知情而導致接受管轄的情形。在實踐中發揮法院引導的作用,為應訴管轄的實施提供了明確先前的程序。
[注釋]
①周翠.協議管轄問題研究——對<民事訴訟法>第34條和第127條第2款的解釋[J].中外法學,2014(6).
②王福華.協議管轄制度的進步與局限[J].法律科學,2012(6).
③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法修改研究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73.
[參考文獻]
[1]張衛平,齊樹潔.日本民事訴訟法典[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7.
[2]周翠.協議管轄問題研究——對<民事訴訟法>第34條和第127條第2款的解釋[J].中外法學,2014(6).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法修改研究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4]齊樹潔.臺港澳民事訴訟法制度[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