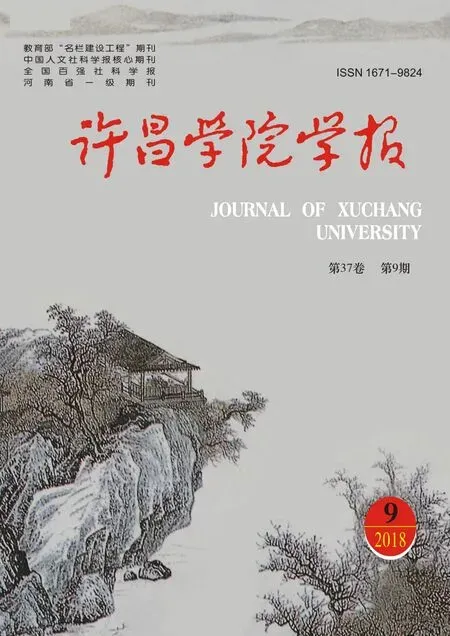“所樂樂吾樂,樂而安有淫”
——以“樂”為核心的邵雍詩學觀念
龐 明 啟
(重慶郵電大學 傳媒藝術學院 ,重慶 400065)
邵雍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理學家,位列“北宋五子”,但與其他四子不同的是,他同時以詩人自居,并非常自得于自己的詩人身份。他看重“詩言志”的本體認知,贊美《詩經》所開創的儒家詩教傳統,不僅沒有將作為經典的“詩三百”與后世詩歌進行功能的對立而厚此薄彼,而且毫不輕視詩歌的娛樂作用,并將其與詩教的道德色彩結合起來,借此提高娛樂的重要性。他把詩歌看成是個人與他人、萬物連接、溝通的紐帶,也看成是體道與娛樂相輔相成的唯一途徑,詩、道、樂三者在邵雍那里是密不可分的。
一、《詩畫吟》《詩史吟》《史畫吟》:有德之樂詩歌觀念的集中體現
邵雍《詩畫吟》《詩史吟》《史畫吟》三詩,集中從儒家詩教的高度談論詩的功用。其《詩畫吟》曰:
畫筆善狀物,長于運丹青。丹青入巧思,萬物無遁形。詩畫善狀物,長于運丹誠。丹誠入秀句,萬物無遁情。詩者人之志,言者心之聲。志因言以發,聲因律而成。多識于鳥獸,豈止毛與翎?多識于草木,豈止枝與莖?不有風雅頌,何由知功名?不有賦比興,何由知廢興?觀朝廷盛事,壯社稷威靈。有湯武締構,無幽厲欹傾。知得之艱難,肯失之驕矜?去巨蠧奸邪,進不世賢能。擇陰陽粹美,索天地精英。借江山清潤,揭日月光榮。收之為民極,著之為國經。播之于金石,奏之于大庭。感之以人心,告之以神明。人神之胥悅,此所謂和羹。既有虞舜歌,豈無皋陶賡?既有仲尼刪,豈無季札聽。必欲樂天下,舍詩安足憑?得吾之緒余,自可致升平。[1]482-483
這首詩談的是《詩經》的功用,里面含有傳統儒家詩教的許多說法,比如《尚書·堯典》中的“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論語·陽貨》中的“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以及《詩·大序》中的“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等等。在此基礎上,邵雍進一步引入了他的觀物思想,包括觀自然、觀歷史、觀宇宙,從中得到歷史和宇宙發展運行的規律法則。之后,他又把以詩觀物與詩樂舞一體以及《詩經》原始的祭祀功用結合起來,以“人神之胥悅”“必欲樂天下”的和樂作為至高無上的最終目的。詩的觀物性能及詩人的觀物所得,通過詩樂舞的結合及其在祭祀中的應用——娛人娛神,達到感人心、告神明的目的。由此,邵雍不僅借《詩經》提高了自己所獨創的觀物思想的地位,而且提高了他所信奉的“和樂”的生命境界,以詩娛樂便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而是變成贊天地造化的大功德。
《詩史吟》曰:
史筆善記事,長于炫其文。文勝則實喪,徒憎口云云。詩史善記事,長于造其真。真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天下非一事,天下非一人,天下非一物,天下非一身。皇王帝伯時,其人長如存。百千萬億年,其事長如新。可以辨庶政,可以齊黎民。可以述祖考,可以訓子孫。可以尊萬乘,可以嚴三軍。可以進諷諫,可以揚功勛。可以移風俗,可以厚人倫。可以美教化,可以和疏親。可以正夫婦,可以明君臣。可以贊天地,可以感鬼神。規人何切切,誨人何諄諄。送人何戀戀,贈人何勤勤。無歲無嘉節,無月無嘉辰,無時無嘉景,無日無嘉賓。樽中有美祿,坐上無妖氛。胸中有美物,心上無埃塵。忍不用大筆,書字如車輪?三千有余首,布為天下春。[1]483-484
此詩認為,詩歌是內心節奏和生命節律自然而然的感發,因此詩史就比刻意懲惡揚善的史筆更具真實性。無論是詩畫還是詩史,邵雍都在強調詩歌如實客觀而又直指本真的觀物功能。只不過詩畫是對歷史、宇宙的全方位觀照,而詩史的觀照對象僅在于歷史,但和詩畫一樣,詩史功能的最終旨歸也在于調和夫婦君臣之義的人倫秩序和天地鬼神的物理秩序,具有一種含納萬有的泛道德性。不過在此詩最后,邵雍卻把詩史的落腳點集中在作為萬物之靈的人與人之間的和樂上。需要注意的是,邵雍所謂的“詩史”和我們一般而言的杜詩那樣記錄史實的詩史不同,它還含有詩歌本身的發展歷史這一層面的意思,所以無論是寫歷史還是寫個人,無論是記時事還是記心事,其全部類型的詩歌都可以納入詩史范疇當中。于是古往今來的酬唱詩、送別詩、宴飲詩這些產生于日常人際交往,用來娛人娛己,具有直接和樂功能的詩歌便被邵雍著重提出來,作為和樂的詩歌核心屬性最為直觀的見證。邵雍由兼綜史事之詩、心史之詩的大詩史縮小到人際之詩、宴飲之詩的小詩類,再進一步縮小到自己的詩,最后逆向地把自己所作詩歌以及詩歌本身的和樂真誠功能收攝到詩史當中去。且看《詩史吟》結尾四句:“忍不用大筆,書字如車輪?三千有余首,布為天下春。”大字寫詩是邵雍平日快意作詩的習慣性行為,如其《大字吟》曰“詩成半醉正陶陶,更用如椽大筆抄”[1]349,《安樂吟》曰“小車賞心,大筆快志”[1]413。“三千首”是邵雍對自己所作詩歌的經常性稱謂。其《擊壤吟》曰:“擊壤三千首,行窩十二家。”[1]461《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七曰:“三千來首收清月,二十余年捻白髭。”[1]561而“三千首”又是孔子刪詩以前原始《詩經》的數量。“春”也是他經常用來形容和樂狀態的詞語,他常常將飲酒、作詩等自適行為所營造的內心和樂之“春”引申到萬物和樂的“天下春”上。如此一來,層層縮小以至最后落腳到自己那些以和樂為基本精神的詩歌之后,他又旋即將其放大到詩史的宏大視野中,娛樂的小道也頓時進入人間與宇宙的大德序列中。
其《史畫吟》曰:
史筆善記事,畫筆善狀物。狀物與記事,二者各得一。詩史善記意,詩畫善狀情。狀情與記意,二者皆能精。狀情不狀物,記意不記事。形容出造化,想象成天地。體用自此分,鬼神無敢異。詩者豈于此,史畫而已矣?[1]485
此詩題為《史畫吟》,實際上是合起來論詩史與詩畫的,卻又并非《詩史吟》《詩畫吟》二詩的簡單疊加,而是論詩歌的敘事與描寫功能,敘事、描寫分別對應著詩史、詩畫。邵雍認為詩的敘事、描寫主要是記事之意、狀物之情,也就是關注事物的所以然而略其所當然,即抓住背后的各種因果聯系。顯然,這是理學家格物致知的詩學觀,反映了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的不同,邵雍是以前者自命的。綜觀邵雍的全部詩歌,其中固然有大量的說理議論詩,但也有不少情趣盎然的寫景抒情詩,而絕少敘事詩。邵雍寫詩講究快意、率性,從來不曾苦吟,對事物的敘述、描摹都采取遺形取神的態度,該詩中所謂的“形容出造化,想象成天地”就是這種作詩方式的反映。又有所謂“體用自此分”,即重體輕用,重本質而輕外在,也是一樣的道理。邵雍采用這樣的方式作詩,使得他的詩歌完全擺脫了思慮之苦,即便通篇說理也能達到快意適性的目的,而那些生活情趣詩則更加灑脫爽利。無論如何,詩只要能“言志”,便不失快樂,即如其《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八十所言:“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歡喜時。歡喜焉能便休得?語言須且略形之。胸中所有事既說,天下固無人數殊。更不防閑尋罅漏,堯夫非是愛吟詩。”[1]530
以上三詩主要談論詩之德而又兼重詩之樂,將樂提高到了道德的層次,有德之“樂”是邵雍核心的詩歌觀念。這個“德”范圍很廣,既是人倫秩序之德,又是宇宙秩序之德,與“道”別無二致。現代研究者也注意到邵雍詩學中“樂”的重要性,如張海鷗先生根據《伊川擊壤集自序》中邵雍自陳“《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惟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認為他的快樂詩學包括“自樂”和“樂時與萬物之自得”兩方面,并總結出三有、四不原則[2]26-31。劉天利先生認為“樂”是邵雍詩一大主題,是北宋社會繁榮和邵雍本人心性修養共同作用的結果[3]54-58。詩歌是大德大道的載體,而寫詩本身又是如此快樂,能自樂、樂人、樂時,乃至與萬物同樂,修德載道便與娛樂達成了高度的一致性。
二、友朋、風月、天機:邵詩之樂的三個層次
筆者將邵詩之“樂”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友朋酬唱的知己之樂,二是收管風月的自然清歡,三是覺悟天機的通達理趣。《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四十一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得時。風露清時收翠潤,山川秀處摘新奇。揄揚物性多存體,拂掠人情薄用辭。遺味正宜涵泳處,堯夫非是愛吟詩。”[1]522說的大致就是這三個層次。
(一)友朋酬唱的知己之樂
邵雍《觀詩吟》曰:“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1]416《讀古詩》曰:“閑讀古人詩,因看古人意。古今時雖殊,其意固無異。喜怒與哀樂,貧賤與富貴。惜哉情何物,使人能如是。”[1]406這與他的觀物思想、詩史思想是一致的。詩歌能夠“曲盡人情”,即使古今時殊事異,依然能夠通過讀古人詩而知古人意,進而通過設身處地、換位思考而尚友于古人。而對于同時代人來說,詩歌當然更是結緣、交游的絕佳媒介。愛好作詩,又喜歡不斷在詩中展示自我形象的邵雍,在交友方面自然從詩歌中獲益良多。邵雍在《答客》中說:“人間相識幾無數,相識雖多未必知。望我實多全為道,知予淺處卻因詩。”[1]229可見詩歌已經成為這位道學家必不可少的交際手段。雖然邵雍說其詩只能反映他思想的“淺處”,富弼卻認為從其詩集《伊川擊壤集》中能夠看出他的“全道”,《弼觀罷走筆書后卷》詩曰:“黎民于變是堯時,便字堯夫德可知。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略無遺。”[4]卷二六五3369富弼還在和邵雍《安樂窩中好打乖吟》中講述了邵雍自衛徙洛、樂道安閑、不應舉薦、甘守貧寂、治史吟詩、與己交好的經過,曰:“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常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4]卷二六五3367富弼將“吟詩”作為他“樂道安閑”的隱居生活的主要內容,與“探古”的學術研究相提并論,也從側面說明了詩歌在二人交情之中所占有的分量。富弼詩歌現存較少,《全宋詩》中收詩23首,而《伊川擊壤集》中附載他與邵雍的唱和詩即有12首,占二分之一強,成為除司馬光而外附載詩歌數量最多的詩人,而現存邵雍與富弼的唱和詩更是多達16首。詩歌像一面照鑒表里精粗的明鏡,不僅可以作為二人精神風貌的真實寫照,使得地位懸殊的兩人毫無滯礙地相互了解,引為知己,更直接見證了二人誠篤的友誼。
邵雍《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三十七自述對交友的熱衷及其在老年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認為詩歌能為他處理好這些交際事務,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好話說時常愈疾,善人逢處每忘機。此心是物難為動,其志唯天然后知。詩是堯夫分付處,堯夫非是愛吟詩。”[1]522“分付”就是委托、交付的意思,他把說好話、逢善人這些事情都委托給詩歌去辦理了。《閑居述事》六首其五敘平居與友朋歡會的情形,曰:“清歡少有虛三日,劇飲未嘗過五分。相見心中無別事,不評興廢即論文。”[1]238其中“論文”大抵亦指唱和及品評詩歌而言。作為長者和師者的邵雍,其苦心孤詣的道學成就吸引著大量的慕名而來者,《宋史》本傳曰:“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5]卷四二七9949而他之所以能表現得“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一接以誠”的重要原因就是能夠以“觀物”“言志”的坦誠態度與四方的拜訪者詩酒酬唱,從而賓主相得,讓人產生彼此無殊、異常親切的感覺,即如《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三十所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對酒時。處世雖無一分善,行身誤有四方知。大凡觀物須生意,既若成章必見辭。詩者志之所之也,堯夫非是愛吟詩。”[1]520邵雍的交游面極廣,鄭定國先生統計說,“總計雍之交游者約可得近二百人”,“其交游至好二十六人”[6]上冊24-25。在洛陽本地交游圈中,閑退耆宿、世家大族、各級官吏與之皆有交往。此外,他還有不少寄詩、與慕名而來者的唱酬詩等等,反映了他有著遠遠大于洛陽本地的交游圈。其唱酬活動也較為多樣,包括宴會、出游、贈答、送別、代簡等。
(二)收管風月的自然清歡
邵雍在《自作真贊》中自我評價道:“松桂操行,鶯花文才。江山氣度,風月情懷。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余暇,閑往閑來。”自注曰:“丸謂太極。”[1]375“松桂操行”指始終如一的品格,“鶯花文才”指歌詠自然美景的詩才,“江山氣度”指遠見卓識和透脫襟懷,“風月情懷”指對自然美景的熱愛。弄丸,指玩味易理。從該詩中能夠明顯看出,邵雍把自己的詩人身份和理學家身份看得一樣重要,而且研究易學和吟詠詩歌、欣賞美景都是本著愉悅身心的態度,即所謂“弄”,這在北宋理學家中堪稱異數。二程評價道:“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為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余暇,時往時來’(按,邵雍將《自作真贊》收入自傳文《無名公傳》中)之類 。”[7]45明確表示對邵雍這種治學態度的不滿,其實這正證明了邵雍是一位很接地氣、很有人情味的理學家。二程又評價道:“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后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7]45“雪月風花未品題”出自邵雍《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一。這也正反映了上文所指出的邵雍通過詩歌將娛樂提高到了道德的層次。與《自作真贊》相似的自我評價還有《堯夫吟》,曰:“堯夫吟,天下拙。來無時,去無節。如山川,行不徹。如江河,流不竭。如芝蘭,香不歇。如蕭韶,聲不絕。也有花,也有雪。也有風,也有月。又溫柔,又峻烈。又風流,又激切。”[1]473在此更是專門以吟風弄月的詩歌才能為自己的身份定性。
邵雍不厭其煩地在詩歌中表達對風花雪月等自然美景的喜愛、依賴、領悟,認為其乃人生一大樂事。他還以風月主人自命,反反復復聲稱自己有著“收管風月”的權力,而詩歌正是他的“權杖”,如《自況三首》其二曰“滿天風月為官守,遍地云山是事權”[1]246,《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七曰“三千來首收清月,二十余年捻白髭”[1]516,《花月長吟》曰“花逢皓月精神好,月見奇花光彩舒。人與花月合為一,但覺此身游蕊珠。又恐月為云阻隔,又恐花為風破除。若無詩酒重收管,過此又卻成輕辜。可收幸有長詩篇,可管幸有清酒壺。詩篇酒壺時一講,長如花月相招呼”[1]265。為什么詩歌能夠賦予詩人“收管風月”的權力呢?因為詩歌能夠將自然的美惟妙惟肖地描摹出來,并賦予它們更加靈動鮮活的氣息和不隨時間衰敗的永久魅力。面對美景,詩人除了擁有收管的權力,還有報答的義務,詩歌也正是這種權力義務的統一體。邵雍屢有“幽人自恨無佳句,景物從來不負人”[1]201(《和商守西樓雪霽》)之類的嘆息,又說“無涯負清景,長是愧非才”[1]213(《過永濟橋二首》其一)“煙輕柳葉眉閑皺,露重花枝淚靜垂。應恨堯夫無一語,堯夫非是愛吟詩”[1]523(《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四十二),覺得愧對自然無償無私的恩賜,詩人若是不能用和美景相匹配的美好詩歌投桃報李,就只能落得忘恩負義的惡名。不過,邵雍多半時候還是非常相信自己有著靈性和詩才,完全當得起風月主人的稱號。他自認為天生具有這樣的“風月性情”,會不由自主地顯露出天機自得之處,于是所有的愧怍都會在不經意的瞬間煙消云散,所有的負擔也會一下子渙然冰釋,轉變為無可名狀的欣喜和飄然灑然的輕盈,故曰:“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1]231(《閑吟》)
邵雍當然也意識到,作為一個理學家如此喜愛詩歌、狎昵風月并不是符合常規的舉動,所以他有時會將自己在這方面的濃厚興致稱為“風流罪過”,如曰:“月恨只憑詩告訴,花愁全仰酒支梧。月恨花愁無一點,始知詩酒有功夫。些兒林下閑疏散,做得風流罪過無。”[1]265(《花月長吟》)“既稱好事愁花老,須與多情秉燭游。酒里功勞閑汗馬,詩中罪過靜風流。”[1]325(《年老逢春十三首》其十)然而這只是戲稱而已,并沒有二程所指責的“侮玩”那樣嚴厲認真。“風花雪月”的意思在青樓妓館盛行的宋代早就變味了,雖然邵雍從來沒有染指其中,但他所謂的“風流罪過”也隱然含有這方面的戲謔,這也成為二程指責其為“侮玩”的口實。不過邵雍毫無忌諱地在詩歌中比花月為美女確有越雷池之嫌,如其《恨月吟》曰:“我儂非是惜黃金,自是常娥愛負心。初未上時猶露滴,恰才圓處便天陰。欄桿倚了還重倚,芳酒斟回又再斟。安得深閨與收管?奈何前后誤人深。”[1]267將月亮的陰晴不定比作嫦娥的愛負心,讓愛慕嫦娥的人也就是賞月的詩人徒費等待之苦,于是引起詩人的怨恨來,覺得真應當把這樣負心的女子收入深閨,以便長相廝守,而不是讓人如此枉費癡心。又,《愁花吟》曰:“三千宮女衣宮袍,望幸心同各自嬌。初似綻時猶淡薄,半來開處特妖嬈。檀心未吐香先發,露粉既垂魂已銷。對此芳樽多少意,看看風雨騁粗豪。”[1]267此詩意淫的成分與前詩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前詩中只有一個負心的嫦娥,此詩中卻有望幸心切、各逞嬌媚的三千宮女。望誰之幸呢?當然是皇帝。然而此處攜樽相對的卻是邵雍本人,為之魂銷、百般憐惜的也是邵雍本人,其中該有多少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深意,讀者只有慢慢體會了。
盡管如此,邵雍認為這些都是他獨特的心性之樂的書寫,并沒有不合理或者過分的地方,“所樂樂吾樂,樂而安有淫?”[1]459(《無苦吟》)因為對自然景物的愛賞是一種高雅的“清歡”,“小車芳草軟,處處是清歡”[1]310(《寄三城舊友衛比部二絕》其二)。既然如此,便多多益善,根本不存在貪婪的質疑和其他任何損害,“稍鄰美譽無多取,才近清歡與剩求。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雖剩且無憂”[1]211(《名利吟》)。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邵雍便毫不諱言對包括花月在內的一切美好自然景觀的癡戀,不僅可以放心大膽地去追求、去享受,并且不斷宣稱“無涯逸興不可收”[1]242(《秋日飲后晚歸》),“游心一向難拘撿”[1]250(《十七日錦屏山下謝城中張孫二君惠茶》),“游興亦難拘日阻,夢魂都不到人間。煙嵐欲極無涯樂,軒冕何嘗有暫閑”[1]245(《和祖龍圖見寄》),等等,堅信“貪清非傷廉,瀆幽不為辱”[1]210(《游山二首》其一)。所以根本不存在二程所說的什么“侮玩”的忌諱,一切都是對精妙詩思的陶冶、對奧妙心性的發揚。
(三)覺悟天機的通達理趣
邵雍詩歌敘事、描寫的成分較少,議論的成分較多。有的議論能夠結合具體的形象、豐富的想象和新鮮的比喻,顯得生動活潑。有的議論則是屏除任何具體形象直接說理,類似于押韻語錄。與“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8]1418(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的揚雄相反,邵雍是以淺易之語寫精深之理。但無論什么類型的詩歌,邵雍都是一揮而就,一氣呵成,除了節奏感、韻律感強,讀起來朗朗上口,語言淺顯易懂之外,還洋溢著智慧、靈動、爽朗的氣息,使得讀者親切地感知到一位洞明世事、通達性理而又趣味橫生的智者、長者形象。邵雍《放言》詩曰:“既得希夷樂,曾無寵辱驚。泥空終日著,齊物到頭爭。忽忽閑拈筆,時時自寫名。誰能苦真性,情外更生情。”[1]225他拈筆作詩純粹出于一種難以名狀、發自肺腑的希夷之樂,是為了抒發和愉悅自己的性情,力求擺脫佛家泥空、道家齊物的條條框框,即事即理,即景即情,一派真誠。這正應了他在《伊川擊壤集序》中說的:“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鑒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余,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性哉?”[1]180
綜觀《伊川擊壤集》,所照之物、所起之志的范圍是沒有局限的,包括說理、寫景、抒情、敘事、說易、詠史、詠物、養生、博物等各種題材,從我到物,從風花雪月到天地宇宙,從當前眼下到古往今來都包攬無余。雖然他曾經游歷四方,居洛時也偶有遠游之舉,但晚年他深居簡出,活動范圍一般不出洛陽城,大部分時間是在安樂窩中讀書、治易、閑行,而他之所以仍能有如此開闊的眼界和詩思,是基于由近而遠、由我而物、見微知著的理學家的思考。他的《二十五日依韻和左藏吳傳正寺丞見贈》詩從悟道的角度談“心騖八極,神游萬仞”的體驗,曰:“上陽光景好看書,非象之中有坦途。良月引歸芳草渡,快風飛過洞庭湖。不因赤水時時往,焉有黃芽日日娛?莫道天津便無事,也須閑處著功夫。”[1]253首聯“上陽光景好看書,非象之中有坦途”,指冬至是悟道、觀物的好時節。上陽,即一陽初起的冬至時節,此時萬物欲生未生,猶如天地初始時的鴻蒙希夷狀態,這是邵雍認為的最佳悟道時刻,即如其著名的《冬至》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1]489非象,是指似象非象、一片混沌的道的狀態,同時也是就冬至而言。頷聯“良月引歸芳草渡,快風飛過洞庭湖”,是寫神游天地的想象之詞。頸聯“不因赤水時時往,焉有黃芽日日娛”,談的是體道、悟道之樂。赤水,古代傳說中的水名,出于昆侖,此處當指天地的盡頭。黃芽,本指煉丹鼎內的黃色芽狀物,煉丹家認為是鉛的“精華”,用作丹藥的基礎。因為黃芽呈現出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所以內丹書籍也常借用為靜中有動的象征。同時它又與先天的混沌狀態有關,《性命圭旨》曰:“以其為一身造化之始,故名先天;以其陰陽未分,故名一氣,又名黃芽。”[9]利集148尾聯“莫道天津便無事,也須閑處著功夫”,神游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所居住的洛陽天津橋畔的安樂窩。“閑處功夫”,是指寫詩、體道、治易等一系列修身立德行為,邵雍又稱為“隱幾功夫”。
邵雍在詩中寫神游四方的詩句還有不少,其意在闡明他的先天易學的特點,他認為先天易學最能夠體現出道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仿佛創世之初的混沌、太和,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邵雍喝酒追求微醺的狀態,寫詩追求靈感偶然迸發的瞬間,這些行為特點都與他的先天易學的治學體驗一脈相承。二程評價道:“邵堯夫于物理上盡說得,亦大段漏泄他天機。”[7]42邵雍也說自己的詩歌泄露了天機:“每用風騷觀物體,卻因言語漏天機。”[1]517(《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十二)他寫詩歌詠花月美景也是要將天機泄露出來,幫助人解決面對自然時的困惑,彌補好景不長久的缺憾,“把酒囑花枝,花枝亦要知:花無十日盛,人有百年期。據此銷魂處,寧思中酒時?若非詩斷割,難解一生迷”[1]330(《囑花吟》)。因此,他甚至認為用詩歌揭示自然萬象的奧秘就是在代天言說,“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已著意時仍著意,未加辭處與加辭。物皆有理我何者?天且不言人代之。代了天工無限說,堯夫非是愛吟詩”[1]529(《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七十八)。所以,邵雍的詩中層出不窮、源源不斷的歡樂很大程度上來自一種覺悟天機的通達理趣,“因通物性興衰理,遂悟天心用舍權”[1]208(《賀人致政》),乃至冥會天心的融怡和樂,“才沃便從真宰辟,半醺仍約伏羲游”[1]328(《太和湯吟》)。
三、快樂與吟詩:圣賢事業的體現
邵雍總是自得于常人所擁有的一些最基本的生理屬性、生活條件,而且樂不可支,如《喜樂吟》曰:“生身有五樂,居洛有五喜。人多輕習常,殊不以為事。吾才無所長,吾識無所紀。其心之泰然,奈何人了此?”其后自注曰:“一樂生中國,二樂為男子,三樂為士人,四樂見太平,五樂聞道義,一喜多善人,二喜多好事,三喜多美物,四喜多佳景,五喜多大體。”[1]335這背后的思想資源很容易追尋,來自春秋時期一個叫榮啟期的隱士,劉向《說苑·雜言》曰:“孔子見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為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10]卷一七429這樣說來,邵雍似乎僅僅是一個非常容易滿足的樂天派,不足為奇,然而實際上在他看來正是由于這些條件太過基本,一般人很難從中發現快樂并發自內心地享受它,而這就需要圣賢的修養功夫了。他的詩歌不斷地描寫所享受的這些快樂,使得自己因而成為天下一等一的人物。如《自在吟》曰:“心不過一寸,兩手何拘拘。身不過數尺,兩足何區區。何人不飲酒?何人不讀書?奈何天地間,自在獨堯夫。”[1]356《多多吟》曰:“天下居常,害多于利,亂多于治,憂多于喜。奈何人生,不能免此。奈何予生,皆為外事。”[1]376所樂之事遍地都是,而能夠隨手取來以資快樂的,邵雍自信天下之大,只有他一人能夠做到。又如《偶得吟》曰:“人間事有難區處,人間事有難安堵。有一丈夫不知名,靜中只見閑揮麈。”[1]364區處,即分別處置、處理;安堵,即安居而不受騷擾。這就解釋了快樂的事情這么多,而人們普遍不快樂的原因在于世界上始終存在著一些難以處理和叫人不安的事情,但邵雍卻總能自處于閑靜無事的境地,其自身形象便一下子高大起來。邵雍以生而為人、為男子、為丈夫而快樂,但他卻又自命為十分人、真男子、大丈夫,這便與圣賢無異了。其《責己吟》曰:“不為十分人,不責十分事。既為十分人,須責十分事。”[1]427又有《十分吟》對“十分人”做了解釋,即具有“直須先了身”的“十分真”,以及“事父盡其心,事兄盡其意,事君盡其忠,事師盡其義”的“十分事”[1]475。“十分人”的標準非常高,連司馬光這樣的當世偉人在他眼里也不過是“九分人”[11]卷一八201而已。“真男子”與“大丈夫”意思相當,出于《感事吟》中“能言未是真男子,善處方名大丈夫”[1]454二句,而這位“善處”的“大丈夫”指的就是他自己。而他認為“可謂一生男子事”的是“寫字吟詩為潤色,通經達道是镃基。經綸亦可為余事,性命方能盡所為”[1]525(《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其五十四)。潤色,就是潤色鴻業、歌詠太平,“寫字吟詩為潤色”與邵雍在詩中一再塑造的太平閑人的自我形象是一致的。要寫出真正潤色鴻業的詩篇并不容易,這需要詩人本身從內到外散發出太平盛世中樂道安閑的氣象,而“通經達道”不過是基礎,“經綸”世務更不過是“余事”。這種論調并非故作驚人之語,而是出自邵雍獨特的圣賢觀念。
詩在邵雍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可以悟道,可以言志,可以娛情,是成圣成賢的必要途徑之一。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功能和類型上,邵雍并沒有把自己日常所作的各種題材的詩歌與作為儒家詩教經典的《詩經》區分開來,甚至將自作之詩與詩三百、詩三千等同看待,這一方面可以看作他的圣賢心理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那種“不立固必”、古今無殊的對于“詩言志”本質的價值體認。哪怕有時候他會自謙地說“林下閑言語,何須更問為?自知無紀律,安得謂之詩”[1]364(《答人吟》)“林下閑言語,何須要許多?幾乎三百首,足以備吟哦”[1]451(《答寧秀才求詩吟》),但也免不了將自作之詩和《詩經》比附一番。他有時會擔心自己寫詩的興趣過于濃厚,構思過于輕易,所寫詩歌數量過多,質量良莠不齊,但馬上又戲謔地自我安慰道:“久欲罷吟詩,還驚意忽奇。坐中知物體,言外到天機。得句不勝易,成篇豈忍遺?安知千萬載,后世無宣尼?”[1]463(《罷吟吟》)邵雍將自己的詩歌比作詩三百的始祖詩三千,和他稱自己的易學越過文王、孔子的后天學而直承伏羲的先天學的態度是一樣的,將吟詩與治易都看成前無古人的立德事業。在“三不朽”當中,立德是先于立功的,不過在官本位的封建社會,尤其是在宋代這樣看重科舉為官的時代里,士人多以建功立業、得高官顯爵為貴,即便是追求立德的理學家也罕有輕視功名富貴的,而邵雍卻認為治國平天下的經綸事業與“寫字吟詩”“通經達道”的修身立德事業相比不過是“余事”。難怪二程對此批評道:“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后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7]45
余論
在程朱眼里邵雍是理學家中的異端,這不僅在于他重象數而輕義理的易學研究傾向,還在于他對吟詩的熱情、對快樂的信奉以及通過詩歌對快樂的大量歌詠。除前面已經引用過的二程評價他“直是無端”以外,他們還用“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為之侮玩”[7]45來評價邵雍那種似乎與理學家身份極不相稱的快樂。朱熹也評價道:“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12]卷一〇〇2553“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顛蹶。”[12]卷三一798將他的詩與樂和孔顏之樂明確區分開來。盡管從道的角度來說,程朱“未嘗以圣學正門庭許他”[13]卷三29,但他們對他詩中的快樂及由此所展現出的坦蕩胸襟和開闊境界卻表示一定的贊賞,并稱之為“人豪”。程顥評價邵雍詩句“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曰:“真風流人豪!”[7]413朱熹評價其詩句“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曰:“可謂人豪!”不僅如此,針對學生“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的話,朱熹嚴厲地斥責道:“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里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個甚后敢如此!”[12]卷一〇〇2542說明朱熹肯定了邵雍不拘一格的快樂是以深厚的學養為基礎的,在“道”上給他留有一席之地,不像二程那樣簡單地以“無端”二字將其一筆抹殺。此外,朱熹師生間的對話也透露出邵雍的快樂精神在朱熹的時代并不缺乏追隨者。而后世的追隨者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從理趣相生的角度來評價邵詩之樂*早在南宋,陳知柔就認為杜甫、白居易詩中豪放通達之處“未若邵康節‘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尤有味也”。(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一五第479頁,中華書局2007年版。)明末袁宏道說:“余嘗讀堯夫詩,語近趣遙,力敵斜川。”(《西京稿序》,見《袁宏道集箋校》下冊第148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清代陳文述說:“余于宋人詩,最愛邵堯夫,蓋其胸次曠達,矢口皆和雅之音,自然之極,純乎天籟。……眼前景物,信手拈來,皆鳶飛魚躍氣象。”(《書邵康節詩后》,陳文述《頤道堂集文鈔》卷一〇,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506冊,第49頁。)所謂“味”“趣”“鳶飛魚躍氣象”皆與樂相關,亦與理尤其是儒學之理相關。,這就大大提升了邵雍詩中快樂的道德品格以及這種快樂對開拓詩歌意境的作用,并賦予其詩一定的詩史地位。伴隨這些評價的是南宋魏了翁,元代吳澄,明代陳獻章、莊昶、唐順之等理學家一浪高過一浪的邵詩崇拜熱潮,以致四庫館臣認為自宋至明存在著一個“擊壤派”,這就有過猶不及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