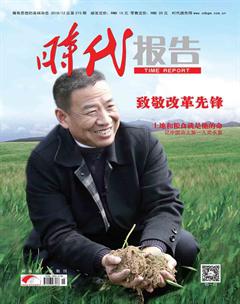樊錦詩:錦瑟華年去,莫高永留詩
任聞

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最長、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畫廊;它還是世界現存佛教藝術最偉大的寶庫。有人說看了它,就等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它吸引了無數的藝術家、考古學家、佛學家、科學家接踵而至,也讓全球的游客都心馳神往。還有的人說,它的絕世風情,只有中國人才懂。而最懂它的中國人之一,也許就是“敦煌女兒”樊錦詩了。
剛來敦煌的時候,樊錦詩因為一張笑起來爽朗的娃娃臉,走到哪里總是被問:“你十幾呀?”
她60多歲坐火車出差,被人問:“您這年紀還出差,有70了吧?”她才覺得老了。
樊錦詩往莫高窟的洞里面一鉆,就是漫長的半個世紀。
1962年,還在讀大學的樊錦詩前往敦煌實習,作為一名學生,沒有社會經驗,想當然地認為敦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敦煌的石窟這么美,研究人員也應該風度翩翩、房子也應該窗明幾凈。
到實地之后,樊錦詩和同學都被瑰麗的洞窟藝術深深地震撼了,從一個洞窟到另一個洞窟,里面的壁畫、彩塑等藝術品琳瑯滿目。之前雖然去過相關的博物館,但像這樣的石窟藝術卻是第一次見,其魅力之大使他們完全忘記了外部世界,仿佛置身于童話之中。
洞窟里面極美,但研究環境卻極差。離開洞窟時,沒有棧道、沒有樓梯,樊錦詩和同學們只能膽顫心驚地走在一根長木頭的左右兩側分別插入短木條的“蜈蚣梯”。住的房子是泥塊搭建的,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而且,敦煌交通不便,信息傳播的速度也極慢,收到的報紙日期都是一個禮拜甚至十天之前。當樊錦詩得知像常書鴻先生、段文杰先生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已經堅守了十幾年的時候,都有些難以置信。
兩個多月以后,樊錦詩身體出現了水土不服狀況,生了病,只好帶著對洞窟深深的印象回了北京。不久,得到老師的消息,敦煌方面希望去實習的四個同學能去那兒工作。 “我們誰也沒說去還是不去。那時候我們接受的教育,是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個人的志愿。周總理說,大學畢業生是青年中的極少數,是青年中最幸運的部分,國家培養了我們,號召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去,到工廠礦山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畢業時學校有兩個去敦煌的名額,分配我和另外一個北京的同學去敦煌。當時我接受了分配,決定去敦煌工作。”
“在敦煌越久,越深入地接觸它之后,就越發地感嘆敦煌藝術真的博大無邊、深不及底,仿佛有一種很強的磁力,牢牢地把人吸引住。
“文革”過后,百廢待興。彼時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保護氛圍、保護機構、保護標志皆已具備,唯獨沒有科學檔案。
通過翻閱伯希和拍攝的照片,對比實際石窟情況,樊錦詩發現,70年后的壁畫、彩塑似乎模糊、少東西了。如第217號窟,70年前的照片中,人和蛇線條生動、清晰,而70年后其鮮艷飽滿的顏色早已不見蹤跡,徒留大片斑駁墻土。
日出三危,日落鳴沙,莫高窟何以經得起時光雕琢,樊錦詩睜眼閉眼都在思考。“敦煌”二字,早已融入她的生命。
雖遠居大漠,她的思想卻是十分包容開放、勇于進取的。一次與電腦的偶然接觸,令她腦洞大開。迎接她的,是莫高窟數字化十年的上下探索。
原以為電腦能解決科學檔案永久保真的問題,結果拍攝洞頂的照片會變形,照片清晰度也遠遠不夠,建立科學檔案之路絕不是一帆風順。
樊錦詩的開闊胸襟、國際視野,讓遭遇瓶頸的項目重見曙光。通過與美國西北大學、蓋蒂保護研究所合作,莫高窟數字化保護終于有了突破性進展。
2011年,經過與國外合作單位反復試驗,十億級像素照相機橫空出世,此設備實現了石窟檔案的完整儲備,的確是個創舉。
時光流轉,技術人員在不斷攻堅克難。從剛開始技術受援方到后來技術輸出方,敦煌研究院技術、人才“質”的飛躍讓整個世界刮目相看。如今,院里擁有的博士數量在全國文保界名列前茅,且掌握了不少原創技術,每年都會為國際培養大批文保人員。
莫高窟終將慢慢消逝,這是讓人不愿直視卻注定無法挽回的結局。不過樊錦詩帶領的敦煌研究人員,用現代科學技術改變了洞窟命運,將壁畫、彩塑通過數字手段搬到室外,實現永久保存。除科學檔案外,如今巍峨屹立于沙漠中的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也離不開樊錦詩的不懈努力。
2003年,樊錦詩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提案,建議利用現代數字技術,展示莫高窟歷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藝術。

這項提案最終促成了巨額投資的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敦煌研究院也當之無愧地成為世界級敦煌學研究中心。
2014年9月,在樊錦詩推動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廳、數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內的數字展示中心投用。
2016年4月,“數字敦煌”上線,30個經典洞窟、4.5萬平方米壁畫的高清數字化內容向全球發布。
除了數字化,她和合作團隊確定的一個數字“6000”,對保護莫高窟也有著莫大的意義。
自2002年起,敦煌研究院與蓋蒂保護研究所合作開展“莫高窟游客承載量研究”的科研項目。項目采用發達國家關于遺產地游客承載量研究的科學方法,結合莫高窟洞窟環境狹小、文物材質脆弱和病害頻發的特殊狀況,首先對莫高窟全部492個洞窟的面積、可利用參觀空間容量、壁畫保存狀況、壁畫價值和游客風險防護措施進行了全面的調查評估;并根據現有開放洞窟數量、位置布局、單個洞窟游客參觀時間、不同游線等因素,經過科學調查、模擬實驗、開放洞窟微環境變化分析和不同游線的游客參觀體驗等一系列的綜合研究,最終確定了莫高窟單日游客接待的最大容量為3000人次。
通過對游客的科學規劃,合理分流,可以將莫高窟單日游客承載量由3000人次增加到6000人次,樊錦詩說。
2003年,莫高窟在中國首創旅游預約制,入洞人數得到了有效控制。隨后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的成立,電影和實地參觀的巧妙結合,減少了游客參觀時間,提高了洞窟承載量。
遇到挫折,沒有放棄,堅持尋找,勇于開拓,最終迎接勝利。這是樊錦詩參與的莫高窟保衛戰,直到如今,這場戰役仍在繼續。
沒有樊錦詩這樣的人,莫高窟壁畫、彩塑無法實現永久保存,我們的子孫后代可能也無法領略其美輪美奐。
“敦煌女兒”樊錦詩,甘愿用生命守護敦煌。按她的話講“我本來沒想留那么久的,我給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為了敦煌莫高窟,她是與時間賽跑的人,是改革中的巾幗力量,值得我們每個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