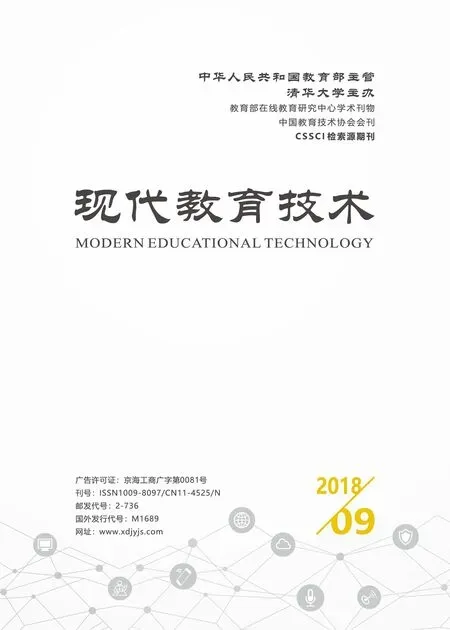大學虛擬化對學校教育的影響*
張 虹 陳恩倫
?
大學虛擬化對學校教育的影響*
張 虹1,2陳恩倫1
(1.西南大學 教育學部,重慶 400715;2.重慶師范大學 初等教育學院,重慶 400700)
隨著虛擬大學的出現,大學虛擬化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為此,文章首先對虛擬大學與大學虛擬化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并分析了大學虛擬化的特點。隨后,文章分別從學校管理、學生學習和受教育權三個方面,重點探討了大學虛擬化對學校教育產生的重要影響。文章指出,大學虛擬化引發了傳統學校管理的變革,使學生學習的基本要素發生了解構與重組;而大學虛擬化對學校管理和學生學習的影響,推動著受教育權的內涵與受教育權的義務主體均發生相應地變化。大學的虛擬化預示著傳統大學在數字化時代的變革方向,這一趨勢必然對傳統教育制度的觀念和實踐帶來新的沖擊,同時對受教育權利運行的制度環境產生挑戰。
大學虛擬化;虛擬大學;學校教育;學生學習;受教育權
互聯網的到來,催生了新型的互聯網教育形態——虛擬大學的出現。大學的虛實融合代表了傳統大學在數字化時代的變革方向,這一發展趨勢對大學生學習、接受教育的相關理念和實踐經驗帶來了新的沖擊,亟待傳統大學革故鼎新,積極應對挑戰。
一 大學虛擬化及其特點
1 虛擬大學與大學虛擬化
在界定“大學虛擬化”之前,有必要澄清一個與之相近的概念——虛擬大學。虛擬大學是運用虛擬技術,創辦在互聯網絡上,不消耗或少消耗現實教育資源和能量,并具有現實大學特征和功能的一種辦學實體[1]。虛擬大學不是一種新的大學,而是大學的一種新存在方式,它是網絡技術催生下繼理念大學和制度大學之后出現的且與之并存的第三種大學概念[2]。長期以來,傳統大學的高耗能建設與物質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不斷呼喚一種新的可替代性形態來為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新活力。這一需求促使人們從以往大規模、高耗能的傳統學校建設中解放出來,轉而思考如何向生態型學校的發展道路上轉型,由此催生了“虛擬大學”的出現。
世界上第一所虛擬大學是建于1984年的美國國家技術大學[3],而通過互聯網授課獲得認可的第一所虛擬大學是成立于1993年的美國瓊斯國際大學[4]。虛擬大學的辦學模式有兩類[5]:一是內生于傳統高校的虛擬大學,如美國鳳凰城大學網上校園;二是完全新生型的虛擬大學,如美國西部虛擬大學[6]、非洲虛擬大學[7]、英聯邦小國虛擬大學[8]。我國最早的虛擬大學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的“深圳虛擬大學園”[9],目前國內虛擬大學相關事務的運行主要由各實體大學中發揮類似教育功能的網絡學院承擔。
何謂大學虛擬化?受制于傳統教育體制與教育投入的影響,虛擬大學一直發展緩慢,反而是各實體大學紛紛通過開發MOOC、SPOC等在線課程而表現出一種強烈的虛擬化關懷,“如何在線”成為每一所實體大學當下必須關注的重要發展問題。本研究將傳統大學的這一戰略轉型稱為大學虛擬化,即受數字化技術影響,傳統大學在教學設施、教學活動和教學管理等方面所表現出的形態虛擬化、交往網絡化、時空無界化、學習自主化之虛實結合的發展態勢。
2 大學虛擬化的特點
大學虛擬化既是聯結傳統大學與虛擬大學的紐帶,也是兩者走向融合的必經階段,其特點表現為:
①形態的虛擬化。大學形態的虛擬化是指大學的實際活動場所不再是依附于傳統實體物理空間,而是由數字信息構成的虛擬電子空間;虛擬大學的教學形態已不具有人們在物理空間中開展實踐活動時那樣的實體性,不僅教學活動的空間被虛擬了(即主體在教學活動中必須依賴各種數字化信息符號作為自身標志和行為象征),而且學生的學習方式和學習思維也呈現出非現實性存在的虛擬化特征。大學的虛擬化改變了傳統大學的典型形象——圍墻、校園、班級和教室,動搖了傳統大學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形成了大學虛擬化特有的教育優勢,可以使學習主體獲得更多的自由體驗和更多樣的選擇——“網絡的這種寬容性既為社會和主體的存在與發展展示了各種可能性,也為主體的生存和發展增加了多種選擇性,使主體能夠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生存和發展的道路。”[10]
②交往的網絡化。互聯網基于分散式共享的網絡傳播模式,打破了傳統媒體一對一或一對多的單向線型傳播過程,削弱了傳統社會嚴格的等級觀念和中心化特征,形成了主體之間扁平化的無中心網狀交往形態和多對多的交互傳播模式——這一模式被引入教育領域后,對于傳統大學組織權力的分化與重組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知識的數字化存儲改變了以往知識自上而下的單向傳遞方式,師生交往在網絡環境下出現了多極主體的多維交叉和非中心化的轉變。這種網絡組織形態的開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造成了學校權力結構的分散,極大地擴充了學習主體接受教育的自由機會和選擇教育的自由,賦予了學生這一群體參與學校管理與決策的平等權,從而強化了學生在大學治理體系中承擔的重要角色,為真正實現現代大學多元權力的有效共存與和諧運行、推進高校從傳統管理走向現代治理的民主化與法治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③時空的無邊界化。受制于物理時空和交往主體身份的多重限制,傳統大學的教學活動備受阻滯,使得大學的教育功能因其時空組織的靜態化而難以適應彈性化的學習需求。數字技術的引入,將人們從物質“原子”時代帶到了數字“比特”時代。數字化建構的虛擬空間拓展了“無邊界”的教育時空,將學校的終極型教育延伸至人的終身學習形態、將條塊分割的學習空間擴展至全球教育范圍、將現實學習空間擴展至虛擬的“賽博空間”。由此,學習成為貫穿人一生的活動,學生的中心地位和主體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彰顯。而高等教育將終身學生作為目標群體,學校教育收縮傳統的三大功能(即知識生產、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而集中到學生終身學習關鍵能力的培養上,這正契合了學習型社會的理念,因為“全民學習權的保障、社會各種學習資源的有效整合、學習環境的形成,是邁向學習社會的關鍵”[11]。
④學習的自主化。互聯網的發展帶來了信息量的激增,網絡成為最大的“百科全書”,這不僅為教育者提供了廣闊的資源平臺,而且為激發學生的創新能力、促進學生的多樣化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保障。大學的虛擬化滿足了現代教育彈性學制的轉型需求,在虛擬技術的支持下,學生可以按照自身的興趣和能力自由地學習、靈活地支配時間,并能滿足學習主體的多元化、多樣化、多層次化需求,故更好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虛擬教育平臺的創建,提升了彈性學制的實施效能,尤其是各種學習終端、在線學習、移動學習和微型學習的發展,以及無標準、異步調多元課程的開發運用,促使網絡環境下學習計劃的靈活性、學習內容的選擇性、學習進程的自主性得以順利實現。大學的虛擬化使學生真正享有了對學習的控制權,推動學生在這一進程中逐漸獲得自由發展、主動發展和創造性發展。
二 大學虛擬化對學校管理的影響
1 傳統的學校中心觀念面臨挑戰
傳統教育對于學校功能的塑造賦予了學校的文化權威地位,極大地強化了學校中心觀念,學校成為知識的主要傳播地,教師則成為知識的絕對象征。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不僅使傳統大學喪失了對高深知識的壟斷,而且使大學生的興趣結構和思維工具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隨著信息的泛濫,真正的危險可能不在于電子大學(虛擬大學)已成為大學的一部分,而在于今天的大學可能成為電子大學的一部分。”[12]當學校不再是知識獲取的唯一場所,傳統實體學校的中心觀念便會面臨嚴峻挑戰,教師的知識權威也會瀕于瓦解。這種變化引發了人們對學校教育的新思考:如何擴大教育的多樣性、建立靈活的彈性學習制度,以滿足學生的多樣化需求?從獨立的實體大學走向網絡的虛擬共同體時,如何在虛實融合的過程中保持自身的活力?
2 人才培養評價體系受到質疑
作為現代學校教學組織形式的班級授課制自誕生以來,在推動教育的普及發展和現代化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表面上的教育普及和受教育者數量的絕對增多實際上卻以吞噬學習主體的多元化、多樣化發展為代價,使傳統學校同質化和標準化的人才培養評價體系受到質疑。在傳統學校中,學生接受教育常被當作是滿足其求職謀生的需求,因此是否設置了熱門專業或未來就業前景好的學科被視為人才培養評價體系的主要判斷依據,而獲取學位也就自然成為了學生接受教育的直接目的。互聯網創設的虛擬平臺為學生獨立人格和個性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寬松的成長環境,使學生擁有了更加寬泛的知識結構和更多的學習自主權。基于此,大學的定義與人才培養評價標準需要被重新界定:應改變傳統學校辦學的同質化和標準化定位,轉而將多樣性和豐富性確立為新的辦學定位,以能為學生的多樣化發展提供更多選擇的可能。
3 大學權力結構遭遇分化和重組
高等教育的繳費制度彰顯了學生作為教育消費者的身份,而大學的虛擬化使學生通過跨專業、跨校購買優質教育資源的消費行為更加頻繁便捷。尤其是以網絡為基礎的“教育超市”[13]的出現,通過提供多樣化的課程菜單選擇、彈性化的學習時間分配以及個性化的學習指導,充分滿足了教育消費者的自主選擇需求。當學生接受教育行為的消費屬性不斷被強調和明示,學生的利益訴求與參與學校事務的管理意愿也就愈發強烈,由此不斷助推著學生群體在參與學校決策中所占權利的份額不斷攀升。當學生的參與意愿與學校傳統管理職能產生對立甚至沖突時,原有的權力制衡局面即被打破,學生受教育權和學校管理權的既往比例也會發生相應的改變。因此,大學虛擬化促使傳統學校的權力結構必須重新進行調整,只有保障“學生增權”和“學校減權”的適度張力,才能通過利益的分權制衡實現彼此的和諧共處。
三 大學虛擬化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大學虛擬化對學校管理的影響,勢必會對學生的學習產生重要影響,這些影響主要體現為師生角色、活動形式、課程資源、學習時空等基本要素發生了變化:
1 從“制度性權威”到“魅力權威”:教師角色的功能轉換促進學生的主體性發展
在傳統學校中,教師因教育資源匱乏而擔負著知識傳遞的主要角色,并決定知識的分配和學生角色的賦予,“這種由外在賦予教師法定地位所決定的角色權威,是一種‘制度性權威’。”[14]而教育信息資源的空前擴張和開放性,使學生獲取知識的來源渠道更加多元,故教師逐漸失去了對知識的控制地位,必然會從“權力階層”轉化為“參與階層”,即從“學生學習的控制者”轉變為“學生學習的協助者”。這一身份的轉換,一方面促使教師突破知識傳播者的單一形象,越發關注虛擬環境下教師承擔的多元角色;另一方面使學生的主體性得以彰顯,故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個性發展成為可能。但在網絡教學模式下,師生處于一種分離狀態,正如馮銳[15]所言:“網絡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再是單純的授與受的關系,而是一種無中心、無等級、無權威的關系,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居于從屬地位,也不可能受制于另一方的束縛。他們只能平等地、民主地、自由地共存在網絡教育活動之中。”當教師褪去“制度性權威”的光環而成為一個以助學者身份出現的“魅力權威”后,通過主動將網絡的教育特性內化為個人的魅力品質,教師就能從與網絡爭奪學生的尷尬境地中脫離出來,從而與網絡一起共同助推學生的成長。
2 從“群體化”到“非群體化”:組織活動的結構轉型助推學生的主動性發展
傳統的學校制度化教育被深深打上了大工業時代追求專業化、標準化的歷史烙印,現代學校的班級授課制更是大工業時代人才培養同質化的時代縮影。在制度化學校里,無論是智力活動還是體力活動,學校均嚴格控制著學生的思維方向和活動形式,并通過學校、年級和班級的嚴格劃界控制著學生的時空位移——“這種劃分限制了學生個體的社會化范圍,條塊分割、區域劃分使得學校成了封閉的代名詞,即使在班級這樣的群體中,個體的異質性仍然導致教師在分配知識、賦予角色中有失公允。從根本上說,傳統社會的教育很難真正實現教育機會的均等。”[16]這顯然與網絡時代人們對自由、平等、多元、差異等價值理念的追求相去甚遠,更與人們對個人發展的主動性、差異性等需求背道而馳。大學虛擬化使傳統教育以群體化為特征的固定模式逐漸具有了非群體化的新特征,即學生身份的獲得不再限于某一所學校的學籍注冊,而是可以同時獲得若干學校或其它教育機構的認證;學習資源的獲取渠道也將突破單個學校,而擴展至跨校、跨區、跨省甚至跨國。最為重要是,這一非群體化的組織形式把對學習資源、時間、地點和進度的控制權交還給了學生,讓學生成為了掌控學習舞臺的主動選擇者,使學生在網絡環境中實現個人最大化發展的理想成為可能。
3 從“同一培養”走向“多元塑造”:課程資源的多元供給成就學生的多樣性發展
教育資源的多寡直接關系到網絡學習者的學習選擇,也影響著學生平等接受教育的廣度和深度。受制于制度化教育和技術發展水平,傳統學校的課程具有載體固態化、呈現靜態化、內容單一化、實施封閉化等特點,因而課程作為教育資源的功能和價值發揮有限。隨著教育資源的不斷豐富和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不同學科之間的滲透和融合日益頻繁,學科界限也逐漸消解,而具有融通性、多元化的網絡課程資源恰恰滿足了學生創新求變的發展訴求。網絡課程的出現,不僅為傳統課程的吐故納新創建了虛擬平臺,更使課程作為教育資源的服務功能得以擴張。可以說,大學虛擬化為學生學習帶來了這樣一種可能:允許學生在自己最合適的時間和空間,學習自己需要的課程內容;新的課程資源不再限定修業年限,也不再限于學校和教室。也就是說,學習的發生超越了時空的界限,并動態地與終身教育相伴。
4 從“統一標準”到“選擇性教育”:學習時空的彈性運作推動學生的個性化發展
傳統的學校制度化教育一般通過對學習時空資源的統一分配來控制學生的學習活動:①從時間要素的分配來看,傳統學校通常以“學制”來度量學生的學習時間總量,以學年、學期和學時來掌控學生的學習進度,以升級和降級來控制學生的時間流動,并以入學和畢業來決定學生在某個學習階段的起點和終點——這種時間配置形式反映了傳統教育時間的一維性和靜態性,使學生個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動服從。而大學虛擬化呼喚打破時間的固有形態,進行學習時間的彈性化及柔性管理,使學習時間不再固定于學年、學期和學時。②從空間要素的分配來看,傳統教育通過學校、年級、班級來分割學生的活動空間,學生被限制在以班級為基本單位的物理空間內,“這就注定了不在同一個學校的人難以成為同學,不在課堂則難以聽到這節課,不在物理空間上靠近就很難在同一課堂上發生互動。”[17]而網絡學校的發展使得學習的場所突破了有限的物理空間,并且網絡空間的無限性和流動性更使傳統的空間形態進一步衍生出虛擬空間,由此催生了“無年級課堂”、“無年級學校”以及“學分銀行”等新型教育組織的出現,并賦予了學習時間和空間更多的個性化特征。基于此,Negroponte[18]把網絡時代稱為“真正的個人化時代已經來臨了”。
四 大學虛擬化對受教育權的影響
大學虛擬化對學校管理和學生學習均產生了重要影響,直接推動著受教育權的內涵與受教育權的義務主體發生變化,這些變化或將成為大學虛擬化進程中受教育權的新內容。
1 受教育權內涵的延伸:學習自由屬性愈發凸顯
受教育權指受教育主體為了人格的自我發展和完善,而具有的一項要求國家提供教育機會與設施并不得侵犯其受教育自由的基本權利[19]。在我國,受教育權的實現是由以同一性和標準化為基本特征的學校教育制度提供的,更多地強調國家的統一保障義務,至于知識學習中的可選擇性卻被嚴重遮蔽,因而造成了受教育權的自由權和社會權的屬性此消彼長。隨著不同群體對多樣化教育需求的增長,原來由國家提供的以保障受教育權為目的的同一性教育與學生的自主學習選擇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亟待受教育權的內涵發展為突出學習者本位的新理念和教育的可選擇性,這種可選擇性在高等教育階段體現為可供選擇的學習自由。本研究認為,在大學虛擬化的進程中,應將受教育權概念拓展為學習和接受教育的權利——這一定位既能反映學習者本位的思想,更能凸顯互聯網時代主體的選擇自由,即權利的發展越來越傾向于表達個人意志和行為的自由。學習自由的內涵和外延十分豐富,其影響范圍幾乎囊括大學教學和管理的各個方面。基于此,對受教育權之學習自由屬性的考察,既要從“應然”層面追本溯源,又要從“實然”層面關注其運行現狀:
①在“應然”層面,學習自由表達了學生作為權利主體為追求自身人格的完善而進行自主學習與多樣選擇的權利本質,因而在本體論上“對于學習自由的理解不宜簡單等同于學習中的選擇自由(轉專業、轉學的自由等),也不宜等同于接受教育的自由(選學校、教師、班級和課程的自由等)”[20]。這是因為,學生在學習活動中是否自由,并不直接取決于可自由選擇的范圍大小——真正的學習自由植根于人的求知本性,是一種個體用感官去自主認知外界事物、獲取信息并最終形成思想的自由狀態。顯然,從本體論角度對學習自由進行探尋,有助于從正義和公平的價值上厘定學習自由的本質。
②在“實然”層面,鑒于學習自由必須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才能實現,因此受教育權投射在教育的實踐操作上就表現為教育選擇權、課程參與權和教學評價權的不斷發展。其中,教育選擇權是指作為主體的學生有選擇網絡學習資源(尤其是學校、專業、課程、教師等核心教育資源)、學習方式、學習時空等的資格和自由;課程參與權是指學生有參與課程設置、獲得選課指導的自由權利;教學評價權是指學生有參與教學管理、質量評價等教學過程的自由權利。這三種具體權利均強調權利主體——學生的主動參與和選擇自由,并依托于網絡環境下彈性學習制度的創建得以保障。
2 受教育權的義務主體發生變化:從單一走向多元
國家是保護和落實受教育權的基本義務主體。除國家之外,受教育權的實現還需要家庭、學校、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其它義務主體的共同維護與合力保障。換句話說,公民能否享有受教育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實現其受教育權,主要取決于這些義務主體的相關作為。從實施教育的過程來看,國家主要通過學校這一機構對學生進行教育,故學校自然成為了學生這一群體受教育權的主要義務主體。隨著互聯網教育的迅猛發展,網絡教育作為現代社會新的學習方式,將逐漸發展成為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等傳統教育方式之外的重要教育形態,由此,“網絡教育成為21世紀受教育權實現方式的一個重要標志”[21]。受教育權實現方式的多元化,意味著不同義務主體之間的互動溝通也將更為頻繁和多元。當前,學校、企業及其它教育機構正借助不斷發展的數字化虛擬技術,圍繞網絡教學平臺的研發建設和優質教育資源的開發共享,合力推進學生受教育權保障體系的實現。
而單就學校的變化來說,在傳統實體大學中,學生的身份和成績認定在同一所學校內獨立完成;而在大學虛擬化時代,傳統的固定學制和單一學籍管理完全被顛覆,學生可以在多個學校注冊,根據學習需求自主選擇多個學校的課程和教學計劃,并且只要達到學習標準,即可獲得相應的成績和證書。由此,學生身份和成績的獲得從一所學校認定變為多所學校認定,受教育權的義務主體也從單一的某所學校走向多元的多所學校——這就對網絡時代受教育權的學校義務主體提出了新的要求:學校應尊重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和可選擇性,為受教育權的充分實現創建更佳的網絡教育環境。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唯有最大限度地尊重學生的受教育權,傳統大學方能在虛擬化的進程中獲得新生。
[1]張達明,陳世瑛.21世紀辦學新模式——虛擬大學[J].現代教育科學,1997,(5):10-13.
[2][12]王建華.大學的三種概念[J].高等教育研究,2011,(8):8-15.
[3]蔡建中,丁新.美國國家技術大學三次轉折對我國遠程教育的啟示[J].開放教育研究,2006,(3):10-16.
[4]張力.美國虛擬大學運行機制初探——以鳳凰大學為例[D].成都:四川師范大學,2009:15-16.
[5]董秀華.從網上看國外虛擬大學教育發展研究[J].教育發展研究,2002,(5):53-55.
[6]耿益群.美國“西部州長大學”辦學特點分析[J].比較教育研究,2003,(12):50-54.
[7]Donat B N P.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of the virtual university and other forms of distance learning: The case of the African virtual university[J].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2001,(4):577-588.
[8]Paul W, John D. The virtual university for small states of the commonwealth[J]. Open Learning: The Journal of Open, Distance and e-Learning, 2009,(1):85-95.
[9]李來.“虛擬”大學何以不再虛[N].科技日報,2015-4-20(8).
[10]賈英健.論虛擬生存[J].哲學動態,2006,(7):24-29.
[11]厲以賢.學習社會的理念和建設[J].高等教育研究,2000,(5):21-25.
[13]劉俊學,鄧永宏,王小兵.教育超市:高等教育的一種有效組織形式[J].中國高教研究,2005,(2):73-75.
[14]裘偉廷.虛擬學習社會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291-292.
[15]馮銳.網絡教育文化之內涵及其特征[J].電化教育研究,2003,(7):29-32.
[16]王曉東,高宏卿.現代遠程教育理論與應用[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24-27.
[17]張義兵.解構與整合:網絡發展對制度化教育的影響[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3):45-52.
[18](美)尼葛洛龐帝著.胡泳,范海燕譯.數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193
[19]申素平.受教育權的理論內涵與現實邊界[J].中國高教研究,2008,(4):13-16.
[20]陳恩倫.學習權利研究[A].勞凱聲.中國教育法制評論(第5輯)[C].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1-208.
[21]勞凱聲.公民受教育權利的性質及實現方式[A].勞凱聲.中國教育法制評論(第10輯)[C].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2:1-17.
The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Virtualization on School Education
ZHANG Hong1,2CHEN En-lun1
With the emergence of virtual universities, the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virtualization on school education has attracted researchers’ attention. Thus, the paper firstly defined the concepts of virtual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virtualization,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virtualization. Subsequently, thepaper focused on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virtualization on school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school management, student learning and the right to education.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at university virtualization trigge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chool management and caused the basic elements of student learning to be deconstructed and reorganized. Meanwhile, theinfluencesofuniversity visualization on the school management and student learning promoted the changesof connotation and obligation subject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ccordingly. The university virtualization indicated the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 of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in the digital age, andthis trend will bring new impacts on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createchallengefor the operationsystem environment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
university virtualization; virtual university; school education; student learning; the right to education
G40-057
A
1009—8097(2018)09—0033—07
10.3969/j.issn.1009-8097.2018.09.005
本文為重慶市教委人文社科項目研究基金項目“‘互聯網’時代網絡教育立法保障研究”(項目編號:16SKGH04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張虹,西南大學在讀博士,重慶師范大學講師,研究方向為教育政策與法律,郵箱為ccyy516@126.com。
2018年4月23日
編輯: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