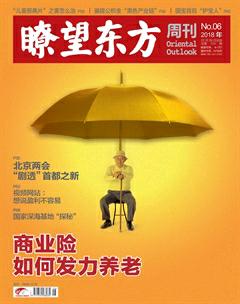“抱團養老”:“看上去很美”?
近期,杭州市余杭區一個“抱團養老”的故事引發全國關注。在一座200多平方米的三層別墅里,13位志同道合的老人組成了“新家庭”,他們簽署了《結伴養老協議書》,像家人一樣互助互愛,互不干涉隱私,融洽相處已近半年。
“抱團養老”存在哪些風險,如何規避這些風險讓老年人更好地頤養天年?公共服務如何跟進?
“抱團”之前,先簽契約
劉慧慧(北京金誠同達(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由老年人自發組織的養老模式,就像一群人一起創業,公司剛成立時大家志同道合,可是在出現分歧與磨難時需要各成員相互理解、扶持、包容,才能維持組織的存在和發展。可以說,社會養老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身體、心理、財務等糾紛,在“抱團養老”模式中一個都不少。
抱團的老人身體素質各異,成員們是否自愿照顧生病的同伴?如果老人們發生糾紛,大家庭有沒有“調解”“仲裁”機制?在財務管控方面,如果大范圍推廣“抱團養老”,勢必牽涉到形形色色的遺產、房屋等問題和矛盾。
猶如公司股東入股需要簽署協議,“抱團養老”也應先契約后成團,盡可能將各種問題考慮周全、約定成章。參照有限公司股東合作協議,“抱團養老”協議中應盡可能詳細地列出以下十大要素:一、宗旨;二、成員資質條件;三、成員的日常住宿、吃穿及相關費用;四、成員的照料;五、任務角色分配;六、成員的具體權利義務;七、禁止行為;八、成員一致行動決議;九、退團及退出后的事項;十、糾紛解決方式。
要實現“抱團養老”模式的更多成功案例,一方面,社會應針對老年人“抱團養老”提出更加完善的養老服務體系,讓社會資源特別是醫療資源向“抱團養老”傾斜。另一方面,國家應完善配套法律體系,政府層面作出制度性鼓勵,既要有物質上的支持,更要有政策上的支持,特別是在房屋產權、子女財務支持方面做出有利于老年人的規定,在保證老人老有所住、財務相對自由的前提下,“抱團養老”才會出現合適的溫床。
遺產問題怎么解
陳濤(中華遺囑庫管委會副主任,律師)
“抱團養老”是利用既有社會關系自發形成的養老模式,核心成員一般以親朋好友為主,輔以面試、介紹其他成員方式加入團隊。老年人從被動接受到主動選擇養老方式,成員在文化修養、職業經歷、家庭背景、生活習性等方面相對接近,更容易形成長期、穩定的關系,相對于專業養老院,養老成本也更經濟。
但自發的組織也存在不足之處,高齡、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需要更專業的護理,“抱團養老”住所的養老基礎設施如醫療服務等一般難以達到要求。同時,法律風險較大,以杭州市余杭區“抱團養老”為例,成員之間簽署了協議,但協議本身是否經過專業人士審核?
根據報道,別墅主人——一對老夫婦征募了其他養老團的成員,成員們與別墅主人夫婦存在房屋租賃關系。養老團發起人作為出租人,對承租人具有法律上的安全保障義務,這一點在協議中如何合理體現?
此外,“抱團養老”還存在遺產繼承上的問題。喪偶老年人長期共同生活,可能產生感情,如果再婚,他們的繼承關系將更加復雜,需要提前規劃,以避免家庭不和睦的情形。
再婚夫妻一方去世,沒有遺囑的情況下,遺產將按照法定繼承的方式處理,再婚配偶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有權繼承再婚老伴的個人財產。由于老年人長期共同生活,財產容易產生混同,形成共同財產,產權歸屬很難清晰,未來可能產生糾紛。這些問題都需要提前規劃,通過訂立協議和遺囑來解決。
因此,對這種新的養老模式應采取謹慎鼓勵的態度,不能草率決定立即大范圍推廣,需要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改進。
大范圍推廣仍需時日
高云霞(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助理,原養老研究中心主任)
以杭州的“抱團養老”案例為例,該模式的顯著特點包括:(1)老人自發、自愿;(2)遵從一定的協議或合約,公開財務支出情況;(3)有環境適宜、設施相對齊備的場所;(4)實質是一種互助養老,主要由參與的老人共同組織開展生活服務和互幫互助式照料,并提供精神文化娛樂等功能。
早在2008年,河北邯鄲就有村莊建設“互助幸福院”,讓農村空巢老人自我管理、自助服務;2014年,山東煙臺成為全國首個“抱團養老”工程試點城市。
這類案例越來越多,反映了三個必須正視的現實:一是我國老齡化現象加劇——到2030年,老齡化人口將達到25%左右;二是老人與子女分居現象日益突出——2016年民政部統計顯示,中國城鄉空巢家庭超過50%,這意味著,傳統、周到、低成本、情感慰藉等到位的家庭養老已經無法滿足需求;三是現有的社會和機構養老無法滿足需求。
2017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超過2.4億人,每千名老年人口擁有養老床位數僅31張左右。當前我國養老服務主要集中在如何提供機構、居家和社區服務,對象重點集中在經濟困難老人和失能失智等特殊老年群體,專門針對健康老人的服務項目形式則相對較少。“抱團養老”這種模式的出現,正好響應了這類老人的需求,是對我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一個有益補充。
“抱團養老”有一定的推廣意義,但大范圍推廣仍需要時日。在推廣之前,有關部門應做到三點:
公共服務部門首先要對“抱團養老”行為進行及時的信息采集及動態關注、需求評估及資源轉介,排除管理盲區;
當地政府尤其是社區服務部門對老人所在活動場所可能出現的安全管理問題、意外傷害、法律糾紛等方面采取必要的干預;
公共管理部門應盡可能為這些相對集中的老人開辟服務通道,如醫療照護問題以及上門服務、老年精神文化服務等等,多為老年人提供一些服務項目選擇。
可以和社區養老服務結合起來
王平(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
“抱團養老”需要一個較大的住所,如何通過個人自籌來解決?杭州案例中正好有一戶老人自有大面積別墅,更多的案例中,一些城市老人考慮過合租城郊農民自建住宅。但在城郊尋找交通、環境等要素相對優質的農民自建住宅,并非易事。此外,相比入住后生活服務都有配給的養老院,“抱團養老”更考驗入住老人的自身素質和社交能力,對于高齡老人可能并不適合。
“抱團養老”可以和社區養老服務結合起來。地方有關部門、社區對“抱團養老”情況要做到心中有數,予以支持、提供服務。
社區工作者需要從實踐中概括、總結出一套可行的規范、協議模式,供老人們參考使用。“抱團養老”不是聯誼活動,而是嚴肅的社會組織形式。僅僅依靠朋友、同學、戰友之類的舊情很難長久維系,需要靠契約精神幫助成員們明確“群己界限”,更和諧地共同生活。
對于“抱團養老”的住房,在消防、安全、衛生、無障礙通行等方面,應該有一套標準。十幾名老人入住相當于一個微型養老院的規模了,社區不宜過度干涉老人的生活,但應該提供專業人員幫助老人們對共同居住的住所進行適當的改造、檢查和維護。
年紀越大,越需要額外的社會服務。杭州案例中的老人們就雇傭了三位服務人員,為大家做飯和打掃。社工組織在此時也可以適度介入,為老人們選擇保姆、清潔工等提供相應的建議和服務。
“抱團養老”為應對老齡化提供了思考的方向。老人們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應該為他們點贊,在不干涉他們現有生活和快樂的前提下,社會、政府有必要在服務和政策上為他們提供更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