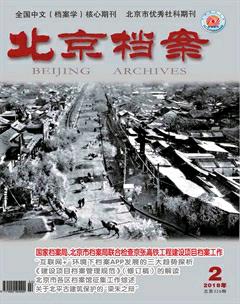從龍樹寺到陶然亭
孫英+靳瀟颯
提及北京,人們通常會想到故宮、頤和園、天壇等氣勢恢宏的皇家建筑。的確,作為元、明、清三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形成了獨具一格的皇城文化。但是,皇城文化只是北京的特色而非全部,與之鼎足而立的還有士人文化、平民文化,以及衍生而來傳統商業文化、民俗文化、壇廟文化等,它們共同構成了北京多元的文化形態。其中,士作為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又是傳統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他們身上承載的士人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清一代,士人多集中在宣南地區活動,他們唱和詩文、縱論國是、辯章學術,推動了中國文化和思想的發展進程,同時帶動了這一地區會館、商業場所等平民文化的繁盛。值得注意的是,宣南一帶的陶然亭也為士子們聚會、講學提供著場所并形成了一代又一代宣南士人文化團體。由此孕育出的考據之學、經世致用之學,皆深刻地影響了整個清代學術和思想的走向。陶然亭也因此成為了宣南文脈的承載地。
一、龍樹寺與宣南詩社
陶然亭一帶歷史悠久。北宋時,這里曾建有興誠寺。明萬歷時期興誠寺重新修整。清初,這一地區因河流縱橫、塘湖錯落,水文地貌宛若江南而頗受士人青睞,他們探幽訪勝、登高極目,一起在寺旁有幾百年歷史的龍爪槐下聚飲。在清初一些人的詩集中常常能看到“年年九日興誠寺”“十年三醉興誠寺”“薊門長嘯還攜酒,拼得如泥醉不歸”[1]這樣的詩句。可見,從清代開始,陶然亭附近的興誠寺就已經成為文人雅士集會的重要場所。但是由于興誠寺簡陋,遠不及康熙三十四年(1695)修建的陶然亭,因此該寺雖有文人探訪,然終究偏僻冷靜。
到了道光朝,興誠寺迎來了鼎盛。道光二年(1822),興誠寺被松筠庵的僧人月亭和尚買下,成為松筠庵下院,并改寺名為“龍槐寺”,又稱“龍樹寺”“龍樹閣”“龍樹院”“龍樹庵”。月亭和尚為浙江海寧人,生平極善經營,加之松筠庵名氣較大,又為明嘉靖諫臣楊繼盛(字椒山)故宅,崇拜楊椒山氣節之人也常來拜訪,故而松筠庵內常常游人如織。月亭僧人也得以結識京城諸多名人官吏,如嘉慶朝工部侍郎鮑桂星,宣南詩社成員林則徐、吳崇良、陳用光、朱珔、梁章鉅、謝階樹、錢儀吉、董國華、程恩澤、潘曾沂等。此后,龍樹寺便逐漸與當時南北聞名的宣南詩社聯系在一起。
宣南詩社,又名消寒詩社。起初是一些志趣相投的京城士人在冬日圍爐、飲酒、賦詩,“繼以射,繼以書畫,至十余人,事亦韻矣”的組織。詩社創始人陶澍曾賦詩云:“憶昔創此會,其年維甲子。賞菊更憶梅,名以消寒記。”[2]隨后,因詩社人事變遷,活動一度中斷。后來在社員董國華的倡導下,恢復詩社活動。復興后的消寒詩社不斷發展壯大,其活動也遠遠超出了消寒的范圍且有了固定的集會時間,因此也就改稱為“宣南詩社”或“城南吟社”。為了營造良好的環境,宣南詩社成員鮑桂星斥資在龍樹寺內建了蒹葭閣,以供各位詩社成員集會使用。自道光三年(1823)開始,鮑桂星、朱為弼、錢儀吉、張祥河等人便經常前往龍樹寺游覽、吟詩頌對,從鮑桂星“蒹葭閣下秋水白,相期險韻還同拈”到吳嵩梁“年年文酒追歡地”,從朱為弼“蒹葭閣畔屢相晤”到陳用光“昨宵夢醒蒹葭閣”,此一時期詩社文風之勝,可想而知。當時的翰林院侍講沈兆霖形容龍樹寺集會盛況便說:“茲地盛殤詠,名流幾徵逐”,翰林院編修何紹基也說:“每當春秋禊,勝地集輪鞅”。
參加宣南詩社和龍樹寺集會的,有很多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陶澍、龔自珍、林則徐、許乃谷、魏源、張穆、梅曾亮、姚瑩、黃爵滋,甚至連不大參與宴游的曾國藩也曾借龍樹寺宴請座師季仙九。[3]他們時常商榷古今上下,暢談政治得失。面對風雨如晦的朝局,一些社員倡導經世致用之學,以革除積弊、整肅朝綱、抵御外辱。據說,鴉片戰爭前,黃爵滋那道有名的《禁煙疏》就與龍樹寺交游分不開。[4]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鴉片戰爭中抗擊英軍的姚瑩出獄,當時一些主戰派社員在龍樹寺為姚瑩設下宴席,以詩酒之樂慰問姚瑩,以示聲援。
之后,由于朝局變動加之詩社社員或亡故或外放,文壇蕭索,龍樹寺便日漸冷落下來。到了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國本動搖,朝廷自顧尚且不暇,在京的官員、文人心有顧忌,不敢在此時來龍樹寺集會。但是詩酒舊地,余韻未央,雖然龍樹寺日漸沒落,但是活動并未完全斷絕。
同光之際,清政府在鎮壓了太平天國和捻軍等農民起義后,迎來了“同光中興”。政權相對穩定后,文壇也活躍起來。彼時張之洞、潘祖蔭、陳寶琛、李慈銘、王愷運、王懿榮、吳大徵、黃體芳、張佩綸等“清流派”官員鑒賞金石、詩文唱和,他們集會的地點就選在了龍樹寺。除此之外,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著名學者王先謙、駐英公使郭嵩燾等也會來龍樹寺或聚會或散心。然而,不論是當時的大環境還是龍樹寺的境況,都顯露出殘敗凋零的光景。辛亥革命后,龍樹寺被拆毀,寺內的龍爪槐也早已枯死,空留下“看山樓圯隔晴嵐,龍爪槐枯倚斷龕。舊事宣南難省憶,野鳧無數落荒潭”的感慨。如今,除了地圖上標識的“龍爪槐胡同”外,人們幾乎都不記得這里曾有一處文人雅集的名勝。百年古剎就此落幕。
二、陶然亭的近世起伏
雖然龍樹寺不復存在,但是宣南的文脈并沒有因此斷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士人精神也并沒有中斷。當時,許多仁人志士目睹了北洋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政局動蕩、民不聊生,他們積極奔走呼號,組織各樣的社團和研究會,希望能挽大廈于將傾。在龍樹寺被毀后,他們把集會活動的地點選在了離龍樹寺不遠的陶然亭。
陶然亭因亭而聞名。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時任工部郎中的江藻于慈悲庵西側建敞軒三間,并題名“陶然”,取白居易詩句“更待菊花佳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之意。《順天府志》曾記載:“(陶然亭)坐對西山,蓮花亭亭,陰晴萬態。亭之下菰蒲十頃,新水淺綠。涼風拂之,坐臥皆爽,紅塵中清凈世界也。”[5]優美的景致吸引了士子們前來歡聚暢飲,陶然亭之名逐漸傳遍京城,為廣大士人熟知。道光年間,經世派代表人物林則徐、魏源、黃爵滋、龔自珍和張維屏等人在龍樹寺集會之余,也常在陶然亭相聚。林則徐更是為陶然亭題聯一副:“似聞陶令開三徑,來與彌陀共一龕”。[6]光緒年間,維新派代表人物、戊戌變法的主要發起者康有為常與梁啟超、譚嗣同在陶然亭聚會,商議各類變法事宜,譚嗣同在其《城南思舊銘并敘》一文中便談及他在陶然亭和慈悲庵活動的概況。維新變法運動失敗后,作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廣仁,其靈柩也曾存放于此。維新運動失敗后,革命黨人孫中山、秋瑾、章太炎等都曾在這里參加過政治性集會,商討革命方略。endprint
陶然亭還與新文化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919年前后,一些知識分子有感于民國初年的社會亂象,深刻認識到非有新國民,民國無以立。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界名人們經常在陶然亭聚會。久而久之,陶然亭便成為新文化的一個代號。
1919年7月1日,李大釗、王光祈、陳愚生、張尚齡、周太玄、曾琦、雷寶菁等人聯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成立了“少年中國學會”,出版《少年中國》月刊。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鄧中夏等與在京的“輔社”成員在陶然亭商討“驅張運動”,之后在陶然亭山門外合影留念。同年8月中旬,周恩來帶領十多名“覺悟社”社員按照約定前來北京。在此之前,周恩來剛剛經歷了半年的牢獄之災。出獄后,周恩來主持“覺悟社”召開了年會,決定聯合各地進步團體,采取一致行動,他首選的就是“少年中國學會”。16日,“少年中國學會”“覺悟社”青年護助團”“曙光社”“人道社”等幾個進步團體在陶然亭舉行團體會議,會上提出了“改造聯合”的主張,發表了《改造聯合約章》和《改造聯合宣言》。[7]這次的陶然亭聚會不僅推動了知識分子“到民間去”的思想轉變,同時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這之后不久,李大釗、鄧中夏、高君宇、張申府等就開始籌備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直到大革命前夕,陶然亭都是李大釗和“少年中國學會”的秘密活動場所。當時陳愚生亡妻的靈柩安葬在陶然亭湖畔,他們以為陳夫人守墓的名義,租賃了陶然亭慈悲庵南配殿的西房作為革命活動的場所。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慈悲庵的內后院的兩間南配房就成了中共北京市黨組織秘密活動的地點。可以說,共產主義的理想和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為陶然亭注入了勃勃的生機和活力。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陶然亭不僅見證了革命者的奮斗歷程,還見證了他們的凄美愛情。很多去過陶然亭公園的人都知道,在公園石橋南錦秋墩的北坡前有兩座墓碑,其中一個是中共早期領導人高君宇的,另一個是他生前女友石評梅的。為了探求中國問題的出路,高君宇先后參加了蔡元培倡導的“進德會”和“新聞學研究會”,并與同時聽課的毛澤東相識。1919年“十月革命”后,高君宇等同志經常到李大釗那里,聽他介紹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他幫助李大釗組織北京共產黨小組,并擔任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首任書記,領導北方地區的青年革命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高君宇加入了黨組織,并以代表身份參加了次年的共產國際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作為黨的早期領導人,高君宇全身心投入到黨的事業中去,他參加了黨的二大、三大,在國共合作中,他同李大釗一起參加了國民黨一大。之后,受黨的委托,高君宇還曾擔任孫中山的秘書。在外地為革命事業奔波的同時,高君宇沒有忘記自己的家鄉山西,1924年他回到山西,開始籌建山西黨組織。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操勞過度,本就患病的高君宇于1925年3月5日病逝。
在高君宇的一生中,石評梅曾是他的摯愛。石評梅當時是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學生,她熱愛寫作,創作了大量的現代詩、散文、游記、小說,并與好友合編《京報副刊·婦女周刊》和《世界日報副刊·薔薇周刊》,被譽為民國四大才女之一。兩個有著共同追求和興趣的年輕人,卻因為家庭包辦婚姻沒能在一起。高君宇的突然病逝,讓石評梅十分痛苦,后悔沒能在生前接受他的感情。在高君宇墓碑上,石評梅題寫詩句:“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閃電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7]1928年,年僅26歲的石評梅因悲傷過度,走完了自己短暫的一生。根據她的遺愿,好友將她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實現了二人“生前未能相依共處,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遺愿。建國后,高石墓幾經遷移,最終在1884年重回陶然亭舊地。
對高石墓的保護,周恩來曾說過:“革命與戀愛并不矛盾,留著它對青年人也有教育”。現在看來,陶然亭里的高石墓不僅教育了青年,同時也展現了陶然亭留存下來的革命文化。
三、結語
從龍樹寺到陶然亭,恰似近代中國走過的百年歷程。在此過程中,既有屈辱挨打的悲憤,也有自強不屈的傲骨;既有說文解字的小學訓詁,也有應時而生的經世學派;既有綿延相承的傳統文化,也有為共產主義獻身的革命情懷。這當中一以貫之的,首先當數陶然文化中所蘊含的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因為不論是以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經世學派,還是之后為了國家復興繼起的維新派、革命黨、中國共產黨人,他們所秉承的都是中華民族傳統中一直以來“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這就決定了當國家處于危難之時,他們雖然開出了不同的“藥方”,但從沒有脫離時代的需要而自吟自唱、喃喃自語。這一民族精神因繼承歷史而厚重,因順應時代而鮮活。
其次,陶然文化離不開宣南地區對不同文化的兼收并蓄。陶然文化屬于宣南文化的一部分,而宣南的文化豐富多樣、各具特色,集通俗、儒雅、莊重于一身,濃縮了北京各個層次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間的共存、交流、互鑒,有利于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清朝從乾隆年間開始一直到清末,許多文人墨客都會被天橋的氛圍所吸引,這其中就包括宣南詩社的成員們。他們曾多次到天橋吟詩唱和、聚會游賞,涌現出一大批反映民間文化的佳作,為后人了解當時民間生活和社會風情習俗留下極為真實、寶貴的史料。
再次,陶然文化中的革命文化是最具特色的精神標識。革命文化是陶然文化的一大亮點,在陶然亭這片土地上留存下來的紅色遺跡是共產黨人在烽火歲月里不懼生死的斗爭精神的最好證據,是黨的歷史和信仰的立體化、具象化體現,是陶然文化中的寶貴財富。陶然革命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它代表了新的時代精神,推動陶然文化順應歷史潮流,為有百年歷史的陶然亭注入了生機和活力。它所弘揚的艱苦奮斗、不怕犧牲、心系人民、自力更生、不屈不撓的精神,永遠值得人們銘記。現在當人們徜徉在陶然亭公園中時,必不會忘記革命先烈為了崇高的信仰,犧牲生命換來的安定富足的生活,也必然會激勵一代代青年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參考文獻:
[1][3]北京市宣武區檔案館.龍樹寺與宣南詩社[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2,13.
[2]王永厚.林則徐與宣南詩社[J].文獻,1991,1:275
[4]金肽頻.安慶新文化百年1915-2015隨筆卷[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6:336.
[5]正江,丁山.陶然亭[M].北京:旅游出版社,1983:15.
[6]林則徐全集(第六冊)[M].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3215.
[7]中共忻州地委黨史辦公室.高君宇[M].1988:23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