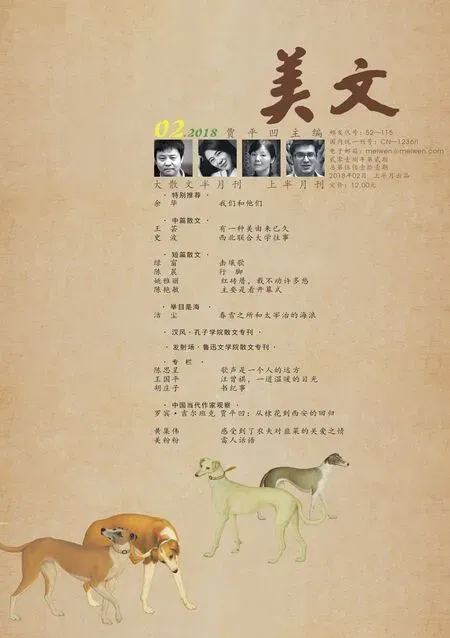行腳
◎陳晨

陳 晨 全國公安文聯理事,魯迅文學院第三十三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作品散見于《人民文學》《萌芽》《散文家》等報刊。出版作品集《我的戰友帥哥》《我的大海》。曾獲冰心散文獎等。
“每個出家人,心中都有一個行腳云游的夢想。行走,是最好的修行。到明年,我就出家滿十年了。過了年,我會跟著我們大和尚去行腳。”
吉昌法師跟我說這番話時,正襟危坐,一臉的心馳神往。吉昌是我家附近一座寺廟里的青年僧人,熟讀佛教典籍,博學而精進,有時也寫一些文字。我得空時便去寺里坐坐,喝茶,聽禪。我并非虔誠有慧根的佛弟子,但紅塵萬丈,需要有一處安放人心的道場,幫助我掃除心靈的塵埃。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行腳”這個詞,聽他說得如此鄭重,不由得對“行腳”向往起來,遂問法師,我是不是也可以跟著一起去行腳。
吉昌法師說,佛家講隨緣,如果時間、身體狀況允許,可以跟著走一段,能走幾日就走幾日,不一定非要走完全程。到時候也會有一些居士參加行腳團。
一晃過了正月十五,新年祈福的香客漸漸少了,寺廟恢復了往日的秩序,開始籌備行腳的各項事宜。行腳團選了九名僧人,寺廟的方丈弘遠法師親自率團。整個行程將歷時三個月,目的地峨眉山。
出發的日子定在二月初二,龍抬頭的日子,天氣晴朗,無風。
清晨七點,鐘聲響起,簡短的拜別常住寺廟的儀式之后,在方丈弘遠的率領下,九名身著僧服、頭戴斗笠的僧人依次排著隊,踏上了行腳云游的歷程。
我和其他六名居士緊隨其后。
蜿蜒的隊伍在城市里無聲地行進著,剛剛啟程,所有人都神完氣足,腳步輕捷。
太陽越升越高,城市漸漸熱鬧起來,晨練的老人,買菜的主婦,行色匆匆的上班族,送孩子上學的家長,來來往往穿梭不停。汽車聲、自行車鈴鐺聲、說話聲,眾聲喧嘩。塵世里的蕓蕓眾生,忙忙碌碌,各自按照既定的人生軌跡運行著。路遇的行人,不時會對行腳團投來好奇的眼光,還有人干脆停下腳步,駐足觀望。
換一個時空,也許我也是觀望者中的一員,被庸常的生活推動著,在自己的節奏里過完一日又一日,像是沒有目標的水流,不知道將流向何方。但今日,走在行腳團的隊伍里,仿佛聽到了遠方的召喚,有了奔赴的目標,也有了俯瞰萬物的悲憫。
一口氣走了十公里,我們走到了城市的邊緣,走上了國道。
在休息點停留時,走來一群男男女女,嘻嘻哈哈地對著僧人們指指點點:“看啊,那個和尚這么胖,紅光滿面,肯定吃葷的。”“肯定是假和尚,出來騙錢的。”僧人們聽而不聞,垂目靜坐,居士們忍無可忍,欲上前理論。
弘遠法師雙手合十,溫和地示意居士們不可爭執。待那群不友好的男女走遠,弘遠法師講起了仰頭而唾的典故。他說,《四十二章經》里佛陀說:“如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而墮其面。如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飛其身。”惡罵、誹謗、譏諷、嘲笑,不一定對別人有傷害,反而傷害的是自己。內心無明之人,需要我們幫助和扶持。
故事都聽過,道理也都明白,但此刻從弘遠法師口中說出,自有一番莊嚴和慈悲。眾居士紛紛稱善。
雖然路遇小小的風波,但我內心卻有了小小的歡喜。古代僧人在行腳途中,山高路險,一路乞食,他們遇到的艱難險阻一定比我們更多,遭受的白眼和輕慢也一定更多,但為什么那么多僧人還要跨越千山萬水去行腳云游呢?也許,對修行的人來講,行走中的磨礪,就像蚌遇到了沙礫,是彌足珍貴的機緣,是修成正果的要件。一顆渴望精進的心,一定會欣悅地迎接各種挫折,無畏無懼,法喜充滿。
這一日,行腳三十公里,傍晚在郊區的一座寺廟掛單。寺中住持對弘遠法師大名早有耳聞,好生敬重,禮遇有加。
寺廟條件有限,素齋簡單,但時蔬新鮮,別有一番滋味。寮房簡陋,倒還潔凈,行腳團成員分住男寮女寮,一人一鋪,多人住一個房間,彼此氣息相聞。步行一日,到底疲憊,大家止語、入靜,很快就沉入了夢鄉。一夜安穩。
第二日清晨,四點半,打板聲響,遠處有雞鳴。大家紛紛起床,安靜地洗漱,隨后去大殿上早課。寺廟規模不算大,但儀規整齊,不管是出家人,還有在寺廟修行的居士,都端莊嚴肅。一個小時的早課結束后,眾人雙手合十,魚貫而出,去齋堂用膳。
寺廟用齋極有儀式感,寬敞的齋堂里數十人一起用齋,但聽不到一絲嘈雜的聲音,所有人都靜默和悅,微笑著用規定的動作向義工示意餐食的多少。在這里,所有的食物都得到了最大的珍惜,所有的餐盤都吃得干干凈凈。佛家特別講究戒除貪念,多余的食物是修行的障礙。
在專注的用齋過程中,平生第一次,我對滋養著我身體的食物充滿了感恩。一顆種子,要經過充滿艱辛的萌發、成長,經過陽光雨露的哺育,經過無數人的勞動,最終才以食物的狀態呈現在我們面前。此刻,我珍惜食物,是對一個已逝的植物生命的憐惜,是對供養著人類的萬物的感恩。
告別了寺廟,行腳團開始第二天的行程。一路不斷有小小的挫折,也有小小的歡喜。
第二日的行進速度明顯慢了很多,主要原因是長時間的步行讓行腳團所有成員的腳上都長滿了水泡,后腳跟都磨破了皮。皮囊是最不可靠的倚仗,很多智慧果敢之士,內心火熱,激情澎湃,有明確的目標,有堅定的信念,但常常在皮肉的折磨下敗下陣來。
好在,弘遠法師之前曾有三次行腳云游的經驗,知道每一個階段可能會出現的困難,提前給大家打了預防針。所以,盡管一行人走得齜牙咧嘴、一瘸一拐,但沒有人喊苦喊累。
傍晚仍在中途的寺廟掛單。夜間休息時,脫去鞋襪,好好地撫慰了一番我的腳,感謝它為我受累受苦,感謝它忍辱負重,感謝它帶我去遠方。
第三日,天空下起了小雨,初春的清晨空氣清冽,春寒料峭。正在行走中,路遇一老者,上前合掌行禮,自稱是佛弟子,受過五戒。他說前面不遠處有一寺叫靈音寺,寺中住持是其堂弟,請行腳團前往歇腳。
弘遠法師見其言辭懇切,就答應率眾參訪靈音寺。跟著老者來到一座小山底下,盤山而上,至山頂,有一寺院,雖不大,建設得還算精巧。寺中住持遠遠迎來,禮數周到。
參訪寺中大殿時,遇見一個小沙彌,聰明伶俐。弘遠法師眼睛一亮,笑瞇瞇地問小沙彌:“幾歲啦?出家幾年啦?”
小沙彌答:“今年十歲,出家三年。”
弘遠法師又問:“讀書了嗎?”
小沙彌答:“開始讀了,寺里有師兄每日教我。”
弘遠法師說:“出家第一步,要先讀好書,才能看佛經,知佛說,會佛義。”
小沙彌點頭稱是,說:“再過幾日我就要去佛學院讀書啦。”
弘遠法師微笑點頭,頗為贊許,并讓吉昌法師拿些錢來結緣,給小沙彌買書。
離開寺廟,走到半山腰,弘遠法師突然想起還沒問過小沙彌的名字。吉昌法師趕緊返回寺廟去問,回來說小沙彌名叫弘果,弘遠的弘,果清的果,果清是此次行腳團里的青年僧人。大家笑了,都說好有緣。
弘遠法師聽了,嘴角含笑,若有所思。休息的時候,他又念起了弘果的名字,說:“近年出家人數銳減,如此伶俐的小沙彌,既收入佛門,一定要好好培養,使其成為法門龍象。”說著,又回頭望著,仿佛是在尋找小沙彌的身影,又仿佛是望向了久遠的未來。
我以前跟弘遠法師并不熟悉,有時在寺廟里遠遠地望見他,總覺得他儀態森然,不怒自威,難以親近,但此刻,他的神色竟然像一個惜才的老師,又像一個憐子的父親。作為寺廟的方丈,弘遠法師平日一定沒少為佛弟子的日益減少而憂慮,所以,今日看到荷擔如來家業后繼有人,難免真情流露。
次日清晨,在掛單的寺廟用過齋飯,我向弘遠法師、吉昌法師及行腳團其他成員告辭。假期結束,我必須返程了。
弘遠法師率眾雙手合十,含笑示意,轉身踏上了新一天的征程。初升的太陽映照著他們,霞光在黃色的僧袍上閃著溫暖的光芒,有風吹來,僧袍在風中衣袂飄飄。我目送著他們越走越遠,一直走向我目力不及的遠方。
三個月的行程,他們只走了三十分之一,出發時是早春,回來的時候將是初夏。在跨越整個春天的行走中,他們會收獲春風的問候,收獲春雨的洗滌,收獲春花的獻禮,收獲草木的萌發,收獲群山的迎送,收獲流水的告白,收獲心靈的蘇醒,收獲升騰的禪悅,也會收獲意料之中的白眼、侮慢、挫折和磨礪。他們在行走中修行,在行走中證悟心中所惑,在山水中參悟禪意,也在不期而遇的人際交匯中度己度人。
而正在返程路上的我,也許注定會在塵世里平凡一生,但人生處處是道場,“明月清風,不勞尋覓”,我們每天走著屬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山一程水一程,跨過山河莽蕩,渡盡人世劫波,何嘗不是另一種方式的行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