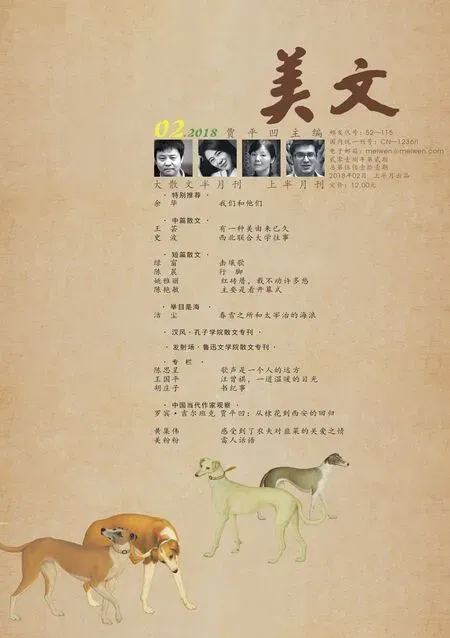貼地行走與自由飛行
◎譚杰
相較于小說、詩歌、戲劇等,散文可以說是擁有更高自由度、更為開放的文學體裁。這種自由開放,賦予它承載了多樣性與豐富性,讓我們讀到斑斕繁蕪的世界,也幫助我們撥開現象的迷霧,獲取人生的真諦。同時,也因為自由開放,它對散文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傾注更加純粹真摯的情感,擁有更廣闊的胸懷和博恰的智識,以及用精取弘的文學素養。
習習對生活和散文寫作是持有高度的尊重和敬意的。她“堅持要求自己安安靜靜地寫作,寫自己認為的有文學品質的散文”。在這樣的文學自覺下,她的創作始終堅守散文的底氣——“個性的呈現,對生命、對生活深邃的切入”,在橫向方面不斷拓展寫作內容的廣度,在縱深層面對生命個體和歷史時代進行深沉思考,在散文文體方面,她就散文作為文學而提出了更多的書寫的可能性。
習習的作品有一種難得的熨帖感。正如《黑蝴蝶讓我們目眩神迷》的題記所寫的,如同拉著你一起在陽光底下話故人、聊舊事,那些昔日影像就在太陽的明影兒里活潑地蒸騰起來,鮮活靈動,又帶有溫度。這講敘是片段的、零散的,又能隨時接續串聯,一切自然而然。
習習在散文中將一個“真”字鋪展開,以此來關照生活和人生。
梁實秋在《論散文》中寫道:散文是沒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時也是最不容易處置,因為一個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絕無隱飾的可能,提起筆便把作者的整個性格纖毫畢現地表現出來。習習擁有女性作家普遍具有的敏銳細膩、多思善感、純真沉靜等特質,她將對生活的豐富感知進行咀嚼和回味,轉化為寫作的靈思。

譚 杰 畢業于山東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2011年起于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工作,主要從事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在 《當代小說》《文藝報》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參編 《2008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中國短篇小說經典》《2009年中國當代文學年鑒》《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必讀·短篇卷第二輯》等。
習習的散文善寫“小”,以小見真,且具有“大事化小”的能力。她的“小”并不是規避歷史時代,去抒寫細碎瑣屑的小情小調,也不是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宣泄個人色彩濃重的心緒或者情感。她在將眼光投向歷史時,并不是記史數典,塑英雄敘偉事。她的“小”,是從蒼茫的塵世中,攫取打動人心的部分片段,將細微之處放大,照射到現實和生命個體中去;她頻頻書寫的那帶有記憶烙印的生活經驗,是對時代和歷史的貼近,對俗常細節的還原與提煉,對平凡人可愛、可憐、可笑、可嘆面貌的立體刻畫。
《黑蝴蝶讓我們目眩神迷》描寫的是在“工業時代”依附于工廠周圍的工人們聚居生活的大院里的俗常人事。寥寥片段,濃縮了七八十年代的時代風貌和平頭百姓的生存狀態,讀來是似曾相識的鄰里和猶在眼前的人世百態。《一種類型的群居》交代了形如平躺茶壺一般的工廠大院里的日常。這大院里的世俗,尤其是由“貧窮和無知帶來的習性”——比如偷窺的習慣,比如分配不均、爭風吃醋,比如表達不滿的粗鄙動作,當然還有一家有難,眾人紛紛施以援手的善良……這些細節或者說片段的截取,體現出習習體悟生活的深意和盡可能冷靜還原生活的本真態度。它們再現出時代的面貌,將讀者記憶中的已經模糊的人事瞬間喚醒,并由此牽引出一系列與之有關的遐想。而生活在茶壺院兒里的人:萬事精通、頗有威望的瘸腿舅姥爺,通情達理卻也有迂腐古板的一面;人群里特立獨行、被街坊鄰里私底下嘲笑又因為組織大合唱而被另眼相看的知識分子四眼兒,想要獨立要自由卻被嚇止,最終如愿以償在大家遺忘的角落里默默無名地生活下去;正在長大的知識分子六一,如小大人一般機靈,也有他的淘氣和倔強;做事投機、用情愚癡的大紅,聰明卻把聰明用錯了地方,身體上承受的斷指之痛并沒有讓他消沉半分,直到癡愛姑娘的芳心許給了雙胞胎弟弟,終于背井離鄉;漂亮卻心意難測的鄰家姑娘蓮娃……所有的人物品性都是多樣的、豐富的、立體的,沒有好人與惡人的嚴明區分,他們是腳踩在大地上的普通人,是院落風俗和文化的建設者。這些小人物,人性里既有閃光面,又有不易被發現的幽暗面,既強大堅硬又柔軟脆弱,如同是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邊呼吸成長起來的。
習習在表達上的節制使得她的散文結實耐讀,猶如散發著光亮的精美瓷器。
習習熱衷于書寫俗常人生,這俗常中的人事無疑是瑣碎的、司空見慣的,然而又是包羅萬象的,要有熱愛生活和屏息靜氣的心,才能發掘出那些有著獨特光輝的部分。在將生活編織進寫作時,習習的書寫節制又通達。這節制既有情感的節制,又有語言的節制。
“不多不少,這次先說這些”。如題記所言,她的書寫不執著于鋪陳渲染,而是抓取與人事相關的核心片段。素描勾勒出輪廓和細節,沒有濃墨重彩的粉飾,沒有旁枝斜逸的雜亂。她平靜而又扼要地力求描摹出舊時光中人事的本質樣貌,讓讀者自己在這人事無常的變化中體味時光和人性的隱匿的力量。
《黑蝴蝶讓我們目眩神迷》中,“我們這群人,像被一只無形的手——吊車的大爪子一樣,隨便揪起一團,丟進了一個茶壺——我們的大院。”一句話描摹出生活的區域形狀——平躺的大茶壺,以及大院里雜而不同人群構成和相對封閉的群居生活模式。她用提綱挈領的詞句來點明要寫的事件,猶如先想到特質,再來敘述佐證。《舉著胳膊走路的人》中,“我們大院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很復雜”,“那是讓人難忘的一天”,“兩個知識分子的交鋒……”,“但是,終有一天,舉著手走路的四眼兒會讓大家另眼相看的。”“要說說合唱了”……這種凝練的書寫方式有效而直接地截取最能人物的片段,把筆力集中在有聚焦效果的事件上,避免了冗長的關于背景和銜接的贅述。
語言的節制則體現為用詞上的通透與練達。盡管在書寫時節制情感,克制平靜,精心提煉,習習在用詞煉句、敘述口吻上卻并不生硬,反而流暢生動,恰如其分。《我們乏善可陳的冬天》篇,講述了以六一為中心的孩子們的冬日生活。心和胃全都空空蕩蕩的乏善可陳的冬日,六一大腦里的知識成了大家打發時間的重要談資。六一給大家講鬼故事,在精神和物質上給大家提供供給,然而,卻集體引起了不適……不管是事件本身,還是用詞,都飽含了冬的意味。“貧寒的長冬鋪天蓋地地來了”,“六一媽的尖叫聲像摔了一地的冰碴子”,聽鬼故事的尕女子牙齒嗒嗒嗒的亂磕著……她的語言里沒有過多的修飾形容,如清透的流水流淌而過,隨大地起伏,或無聲滋潤,或就勢落下。語言的通達與凝練減少了作家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和隔閡,消除了閱讀的障礙,平添了感染力和自然感。
從習習的作品中,我們可以觀測到歷史時代的樣貌,觸摸到俗常的肌理,還有平凡小人物的喜憂與獨特。她觀察俗世的細致入微,對人情世事的悲憫與疼惜,使其作品具有很強的辨識度和審美意味。“我熱愛寫作,它只遵從內心的指使,它賦予我精神上的自由,讓我常入無人之境,讓我可以在一個人的疆場上萬馬馳騁。在繁雜躁亂的生活中,它沉靜入心,可以不被打擾,而且,它與世間萬物物理性的進程不同,它永遠都在成長,它只會愈加繁盛。”自覺生活、自覺寫作的習習,對待散文寫作有自己的思考和態度,因這熱愛,賦予她一股高昂自由的力量,這力量會支持她在寫作上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