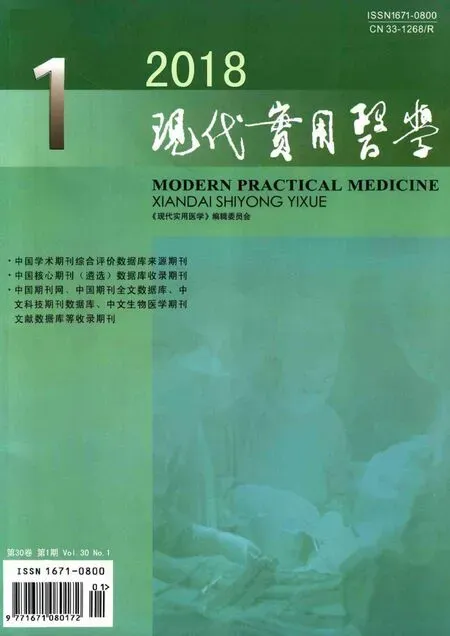專職康復師對全髖置換術后患者關節功能與心理的影響
徐敏,方玉飛,胡樹紅,楊愛玲
全髖關節置換術(THA)在臨床的應用日益成熟,為許多的骨性關節炎[1]、骨無菌性壞死及股骨頸骨折[2]的患者帶來了福音。但 THA手術患者長期的病痛,手術創傷,經濟負擔,尤其是困難的術后康復鍛練與術后康復鍛煉帶來的疼痛,往往使患者出現一定的抑郁與焦慮的負性情緒[3]。寧波市第二醫院關節外科引入專職康復師,作為患者整體康復與護理團隊的一部分,結合規范的圍手術期心理護理,為THA患者制定個體化的功能與心理的康復計劃,取得了一定的經驗。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本院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間骨科中心關節外科收治的擇期全髖關節置換術(THA)的患者103例。其中男40例,女性63例;年齡44~94歲,平均(71.16±12.50)歲;換髖部位:左51例,右52例;疾病類型:骨性關節炎37例,股骨頭壞死38例,股骨頸骨折28例。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實驗組(52例)與對照組(51例)。實驗組男22例,女30例;年齡44~94歲,平均(73.42±11.57)歲。對照組男18例,女 33例;年齡 46~ 94歲,平均(68.84±13.09)歲。兩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對照組 責任護士負責患者圍手術期的常規護理、心理康復護理、關節康復宣教及出院指導等工作,并在日常工作之余,協助患者進行康復鍛煉,但鍛煉的時間、次數及幅度無限定。
1.2.2 實驗組 在完成常規護理工作以及心理護理的基礎上,由專業康復師介入全髖置換術后關節功能康復,具體工作內容如下:(1)制定計劃。根據患者的個體情況,與手術醫師及責任護士討論后制定相應的康復計劃;(2)計劃內容。需包括在術后恢復的不同時間選擇各種康復鍛煉動作的時機及持續時間,運動的頻率與次數等;(3)計劃實施。由康復師對患者及家屬進行示范,講解肢體擺放的位置與角度,如何站立及行走鍛煉,運動實施的要點,運動的幅度次數,并協助與監督患者的康復鍛煉;(4)根據訓練的效果,對康復計劃進行必要的修訂;(5)制定出院后的康復計劃及注意點,制成文書交于患者,親授示范動作,指導避免危險動作。電話隨訪跟蹤至患者基本康復。
1.2.3 觀察指標 安排一名護士(未告知分組情況),對患者進行評分及術后跟蹤隨訪。對患者入院24 h內、出院前1 d、術后3個月及6個月門診復診的各個時點進行Harris髖關節量表、抑郁自評量表(SDS)與焦慮自評量表(SAS)評分。
1.3 統計方法 數據采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處理。計量資料已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獨立樣本 檢驗;計數資料比較用2檢驗。<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兩組術前及出院前1 d Harris評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0.80、1.96,均>0.05);術后3個月及6個月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3.27、5.06,均< 0.05)。見表1。兩組術前SDS、SAS評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0.83、0.92,均>0.05);實驗組出院前1 d、術后3個月及6個月SDS評分均低于對照組(=2.07、2.02、2.69,均<0.05);實驗組出院前1d、術后3個月及6個月SAS評分均低于對照組(=2.81、2.61、2.91,均<0.05)。見表 2。
3 討論
需要進行THA手術的患者,由于長期病痛的折磨以及勞動能力的喪失,往往還存有焦慮、抑郁等不良心理[4]。Duivenvoorden等[5]的研究表明,焦慮與抑郁的存在與術后關節功能的康復起相互作用。在常規的臨床工作中,患者的康復鍛煉通常是在護士指導下進行的,由于缺乏專業的康復知識,加之護理工作的繁重,使得康復指導趨于簡單,患者理解不深,效果欠佳[6]。為了獲得更好的康復效果,本院引入了專職康復師全程負責實驗組患者的術后康復。
本文結果顯示,專職康復醫師介入THA患者的心理與關節康復,在早期就能改善SDS和SAS評分,而在出院后3個月及6個月時點的隨訪中發現,改善更加顯著(均<0.05)。專職康復醫師介入對不良心理術后康復的影響,可能與患者看到康復師的積極介入擁有更好心理暗示效應相關;而更重要的可能是隨著關節功能的改善,患者的焦慮與抑郁心理也自然的得到了緩解。在康復師的專業指導及協助下,較之對照組,實驗組患者的髖關節功能的改善在出院時即有一定的提高,并在隨訪中,Harris評分的改善更加顯著(均< 0.05)。這一結果可能與專職康復醫師更加專業的示范教育、規律而保證的鍛煉時間、個體化的康復計劃、以及門診長時間的隨訪與指導有一定的關系。

表1 兩組Harris評分比較 分

表2 兩組不同時間SDS、SAS評分 分
專職康復師介入本科整體康復護理團隊的時日尚短,對于骨科患者術后的康復特點的掌握還有待深入,加之患者眾多,完全由康復師負責全部的康復工作也并不現實。如果能把專職康復師的專業技能,與整個團隊的康復護理工作有機結合起來,應該能給患者帶來更多的福音。
[1] Lars Engeseter,Ingvild Engeseter,Anne MF,et al.Low revision rate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patients with pediatric hip diseases:evaluation of 14 403 THAs due toDDH,SCFE,or perthes’disease and288 435 THAs due to primaryosteoarthritis in the Danish,Norwegian,and Swedish Hip Arthroplasty Registers(NARA)[J].Acta Orthop,2012,83(5):436-441.
[2] Nils PH,Anne Garland,Cecilia Rogmark,et al.Early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n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a nation wide study of 24699casesand118518matchedcontrols[J].Acta Orthop,2016,87(6):560-566.
[3] Krupic F,Garellick G,Gordon M,et al.Different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in immigrants and patients born in Sweden:18 791 patients with 1 year follow-up in the Swedish hip arthroplasty registry[J].Acta Orthop,2014,85(3):221-228.
[4]Rasouli MR,Menendez ME,Sayadipour A,et al.Direct cost and complications associatedwith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inpatientswithpreoperativeanxietyanddepression[J].J Arthroplasty,2016,31(2):533-536.
[5]Duivenvoorden T,Vissers MM,Verhaar JA,etal.Anxietyanddepressivesymptoms before and after total hip and knee arthroplasty:a prospective multicentre study[J].OsteoarthritisCartilag,2013,21(12):1834-1840.
[6] 凌艷,孫正勤,陸卉,等.專職康復護理對生物型全髖關節置換術后功能恢復的影響[J].中華現代護理雜志,2014,20,(25):3181-3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