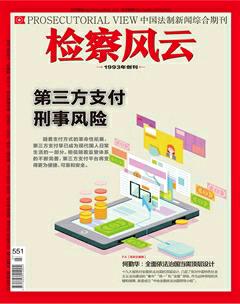明星制造與媒介參與
楊皓
早在20世紀30年代,英國學者就開始關注到人們對于媒介的使用問題,“媒介素養”理念也在當時的英國濫觴。彼時的媒介素養源自于精英文化脈絡,強調保護媒介使用者免受不良媒介信息的侵害,屬于一種“免役式觀點”,而后學界更進一步把受眾在接受信息時的參與因素納入考慮范疇,媒介素養理論由此開始強調對媒介的質疑和批判性思考。
經過將近90年的發展,媒介的定義已經與從前大不相同。在互聯網的作用之下,社交媒介給普通人帶來了發聲的機會,人們也從媒介使用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媒介參與。如果說媒介使用基本意味著被動、單向的接收過程,那么媒介信息處理則代表著受眾主動、積極的處理策略,而媒介參與更進一步,受眾不僅接收、處理信息,而且參與生產信息。
在媒介參與的時代之下,媒介素養理論有了新的視角,其更多聚焦于公眾媒介參與行為,并以其為核心發展出種種研究。
萬眾造星
在媒介參與成為民眾與媒介相處的主流狀態時,明星的定義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不論是20世紀80年代印刷媒介為主導的文字建構的明星形象,還是90年代以來電子媒介為主導的圖像視聽所建構的明星視覺化的消費符號,傳統媒介始終站在明星塑造的中心地位。追星族的交流更多限于粉絲會這一類面對面的交流,在關于明星的話語空間中絕大多數時間處于一個被動接受信息的狀態,對明星的塑造與建構缺少能動的干預與影響。
但在互聯網的作用之下,情況完全不同了。網民可以在網絡上對自己喜歡或者厭惡的明星肆意發表評論甚至捏造事實。粉絲行為不再是簡單的追星和對偶像的膜拜、對偶像相關物品的追捧,他們逐漸參與到偶像的制造和包裝中,滲入了偶像成長之路的方方面面。粉絲的權力日益擴張,對明星的星途和娛樂文化產業產生巨大的影響。
舉一個例子,當某一個明星被爆出某個丑聞時,其最為忠實的粉絲可能會在網絡上竭盡所能幫其澄清(如在2016年吳亦凡被爆約炮事件中粉絲力證網絡上流傳的音頻與視頻為后期合成),這樣的粉絲無形中參與了明星的正面形象塑造,而且這往往會比明星官方的公關團隊的公關工作更為有效;相反有的粉絲在面對類似事件時,可能會在網絡上表現出失望,甚至“粉絲轉路人”“粉絲轉黑子”的狀態。這類粉絲有著令明星十分懼怕的力量,因其曾經對明星抱有過好感,當他們被負面新聞所影響時,他們的言論很可能極具感情,以至于可能讓原本的粉絲群體出現大規模動搖。
民眾在追星的同時,利用媒介參與了明星的塑造,從明星宣傳、內容生產,到劇集接拍、代言落地,甚至團隊人員構成等關乎“命脈”的事宜都有粉絲涉足。某種程度上,粉絲群體試圖成為偶像的“全盤操盤手”。
另一方面,也必須認識到,由新媒體塑造的去中心化明星,相比傳統媒體塑造的明星會更多依賴自己的粉絲。娛樂明星、體育明星等公眾人物紛紛在網絡上開通微博、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賬號,以達到和粉絲進行溝通更為便利之目的。以鹿晗的微博為例,其粉絲量高達4218萬,單條微博的互動留言數量也是輕松就可以突破5萬。
粉絲們開始有機會與自己的偶像直接交流。人們并不關心賬號背后的使用者是明星本身或者其運營團隊,民眾真正需要的是在網絡交流中的參與感,這是前所未有的。除社交網絡上的互動之外,貼吧、論壇等網絡公共討論空間也使粉絲在虛擬網絡社區里獲得了符號狂歡的快感。各種帖子集合了網民對明星的想象與解構,明星形象的塑造與建構在紛紛攘攘的多場域的對話與互動中形成了疊加效應,共同構成了一個粉絲凝視與想象下的明星形象。
這種想象形象其實并非明星的真實形象,也非明星想要呈現給大眾的形象,而是網民根據自己好惡結合明星特點臆想出來的一種虛假形象。但這種虛假形象確確實實根植于粉絲的心中,并成為粉絲的私人擁有物,平時不允許被人侵犯。但當明星發生丑聞時,粉絲可能選擇將其拋棄,而拋棄的實質乃是對明星想象形象的再定義,也即明星的再塑造。
法國當代社會學家埃德加·莫蘭說,“明星是一種既有神性又有人性的生物,在某些方面,他們類似于神話里的英雄或者奧林匹斯山的神……明星是一種混合人格,我們無法從他身上分辨出哪一個是真實的人,哪一個是明星制塑造出的人,哪一個又是觀眾想象出來的人。”
明星夢
上文已述民眾在媒介參與的作用下參與明星制造的種種,其實這只能算是媒介參與的初級表現,更有進者乃是“明星夢”的崛起。
網絡直播在這幾年飛速發展。根據商業資訊平臺虎嗅網的統計,截至2016年5 月,已有108家網絡直播平臺獲得融資。
人們只需要一臺電腦或者一臺手機,就可以實現網絡直播。原本高高在上的大眾傳播模式不復存在,一對多的傳播方式再也不是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所獨有的傳播特權,人們在利用互聯網不斷解構原本的大眾傳播方式時,找到了自己登上“主席臺”的機會。借助直播平臺,在網絡上漫無目的沖浪的網民可以挑選自己喜愛的直播頻道滿足自己的窺私欲、好奇欲等等欲望;富于表現欲的人們則借助直播平臺展現自己,滿足自己心底的明星夢。
按照新聞學相關知識所述,從前充當一對多的大眾傳播發言人的記者、編輯人員,往往需要具備多種素質,因為大眾傳播會在無形中對受眾產生影響,媒體的信息對受眾具有一定的引導作用,這也即是新聞傳播學界常提到的涵化理論。
因此一對多的傳播方式一旦變得平民化、易得化,勢必會產生諸多意想不到的問題。2017年12月,某知名游戲主播在直播網絡游戲過程中被爆出疑似使用外掛,事件不斷發酵,從單純的一件主播爭議事件發展成為網絡上的一大熱點議題。除此之外,2017年還發生過年輕的網絡主播口出狂言飆車發生車禍、游戲主播直播時毆打自己女朋友等等惡性事件,網民對網絡主播的素質開始關注并展開討論。
人們越來越關注到,活躍著的網絡大主播們,已經近似明星群體,他們有著自己的粉絲群。由于他們比傳統意義上的明星與粉絲的互動更多,所以其粉絲更容易被主播所影響,比如目前網絡上流行的種種網絡用語絕大部分都是出自各大網絡主播之口。endprint
因此網絡主播在形式上打破了傳統媒體對大眾傳播壟斷的同時,某種程度上也打破了原本的社會文化體系,利用社群在網絡上的集聚,各種亞文化非常容易在青年群體中形成認同。另一方面,網絡直播內容本身會潛意識地建構起觀眾的自我價值并影響觀眾的價值判斷,觀眾在選擇所看主播的同時便是在實現自我價值。
無論是看直播抑或是當主播,都是對傳統的媒介使用方式的顛覆,網民從造星階段得到解放,進入了人人皆可成為明星的網絡“明星夢”階段,大眾傳媒的中心化被解構推翻,社交媒體的文字遲滯交流也被視頻化所演進,媒介參與又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從“瀕死”到“還魂”
在社交媒體與網絡直播還沒如此盛行之前,社會學、傳播學學者對媒介使用過度的民眾們就有著種種擔憂。他們認為人們耗費在諸如電視或網絡上用于消費象征符號的時間與精力,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種自我按摩,也可稱之為自我褻瀆。這是一種放棄自己思想,交出自己靈魂的行為,因為這樣的 “虛度時間”的方式與古典知識分子強調的理性論辯與德行的矜持相違背。
電視與前互聯網時代大眾媒體所創造的種種媒體產品之所以對人們產生了致命的吸引力,其關鍵并不在于它們傳送的訊息本身,而是所創造的種種內容在傳播過程中留下的一些極為微小的不可猜想的留白部分。正是這個留白部分讓人們有著想象、遐思與感覺的空間,而這種空間恰恰讓媒介使用者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并愿意以這樣的方式“虛度光陰”,即便這些媒體所傳播的內容往往表現出媚俗、廉價等缺陷。
社會學家葉啟政對人們沉迷電視或網絡媒介所提供的內容有過以下評價,以手的細微動作與以眼與耳為主的視聽覺來替代角度運動,成為人體運動、也是接近虛擬世界的方式。于是,這就產生了如法國社會學家保羅·維希留所說的圖景:人以“靜坐人”或乃至“靠躺人”的狀態來呈現自己,這是一種接近“零能量”的方式在“平靜運動空間”里呈現著“瀕死”狀態。
按此說法,在滿足了放棄理性深度思考與物理運動之后,人類達到了某種意義上的“瀕死”狀態。推及如今,媒介參與替代了簡單的媒介使用,但無法否認人們仍然是簡單且缺乏思考的狀態,人們因消磨時間卻進入再也無法抓住屬于自己時間的狀態,人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從媒介參與的主體變為了媒介參與的客體,成為了被媒介使用的客體。
我們不妨延續保羅·維希留的“瀕死”狀態說法,稱目前的媒介參與盛世為“還魂”。人們不滿足于“靜坐人”的靜止狀態,尋求動態的自我演出,正如主播們在攝像頭前張牙舞爪、粗話亂飆的圖景,不正是人被媒介異化的還魂演出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