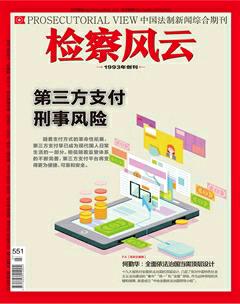極端工具理性與人的身份確證
張寧
1996年7月5日,世界上第一只克隆成功的哺乳動物——綿羊多莉誕生。克隆羊的誕生,引發了人們的很多思考,其中一個焦點問題就是人類可不可以克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石黑一雄原著并參與編劇的好萊塢科幻電影《別讓我走》,講的就是一個關于克隆人的故事。
凱茜、露絲和湯米三個少年是好朋友,他們一起生活在英格蘭鄉村的黑爾舍姆寄宿學校中。這所學校很隱秘,近乎與世隔絕,他們對世界的認知完全通過課堂學習和模擬表演來實現。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師忍不住告訴他們真相:黑爾舍姆學校里的孩子都是為了給人類捐獻器官而被創造出來的——他們是醫學實驗品:克隆人。通常在進行三四次捐獻之后,他們的生命就會終結。
接下來,影片并未如很多好萊塢大片一樣講述這些“異類”如何為了獲得自由與人類展開斗爭,而是展現了凱茜、露絲和湯米這三個青年男女的感情糾葛。這就常常讓我們忽略了他們是克隆人的屬性,因為他們的內心世界和我們正常人類并無二致:他們有愛,他們有恨,他們也有嫉妒、孤獨和自我迷失。于是我們會恍然發現,所謂克隆人,除了不是胎生,其他和我們并無二致,沒有家人的克隆人甚至渴望找到那個和他們一模一樣的人類母體。此時,當我們和凱西一樣,看著他深愛的湯米被推上手術臺,任憑醫務人員摘取器官,不禁會問:他們只是人類的醫學試驗品嗎?作為和人類相同的生命個體,他們何以沒有人的權利和自由?
是的,二十年前克隆羊的成功降生,預示著從科學技術上講對人類進行克隆已經不是難題。這對人類的確充滿誘惑,用技術手段解決人類自身的衰亡問題,從科學、現代化的角度又完全合理。試想,如果克隆一個人不可以,那么克隆一個器官可不可以?克隆一只手臂、克隆一個內臟呢? 貌似可以,因為這好像和生產義肢是同樣的道理。那么克隆一顆大腦呢?好像又不可以。是什么原因抑制著這樣的技術的發展呢?是道德、倫理。馬克斯·韋伯將合理性分為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人類反思生死,考量生命,建立信仰,這些都屬于價值理性范疇。當人們不再思考生命的意義,而只是為了活著而活著,那就可稱為工具理性。如果為了活著把科技推向一個極致的高度,而價值考量化為烏有,這就是工具理性的極端表現。于是,就會出現克隆人。
影片沒有讓黑爾舍姆學校里的年輕人選擇逃亡,甚至與人類為敵,但從情節上看,成年后他們并沒有被嚴格管控。那么他們為什么不反抗?他們為什么不逃跑?故事開始時有這樣一個情節:足球被踢出了操場的柵欄外,盡管那是一道很矮的柵欄,但包括湯米在內的所有孩子沒人敢越過那道柵欄。因為有一個關于柵欄的魔咒已經深深種在了他們心中——越過柵欄,將被肢解而死。這是人類對他們的規訓,這樣的規訓似曾相識。這樣的克隆人和人類早期社會里的奴隸又有何本質分別?這值得我們每個人反思。黑爾舍姆“人”沒有父母家人,不必為衣食煩惱,讀書、學習,接受藝術教育,每天過著看似快樂無憂的生活,這里幾乎成了柏拉圖的理想國。然而他們的宿命就是為智慧的人類獻祭。當年的希特勒不就是這樣利用尼采的超人哲學的嗎?
誠然,從目前情況看,克隆人一時半會兒還不會出現,因為我們還沒有充分的準備。或許我們永遠也無法有這樣的準備,但人類科技的發展是不可能停滯的,面對類似的關口是遲早的事情。事實上,工具理性的表現遠不止石黑一雄筆下克隆人這一樁假想案例。從當年希特勒的“生命之源”計劃到當下的青年人為了找工作而報考熱門專業,都可以看到其幽靈般的身影。當所謂科學、所謂技術、所謂現代文明越來越強勢入駐人類思想、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我們就越來越少地進行“價值”“意義”“信仰”的思考,取而代之的是有關“工具”“效率”“程序”的行動。利用克隆人來滿足自己的生存意志,人還成其為人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