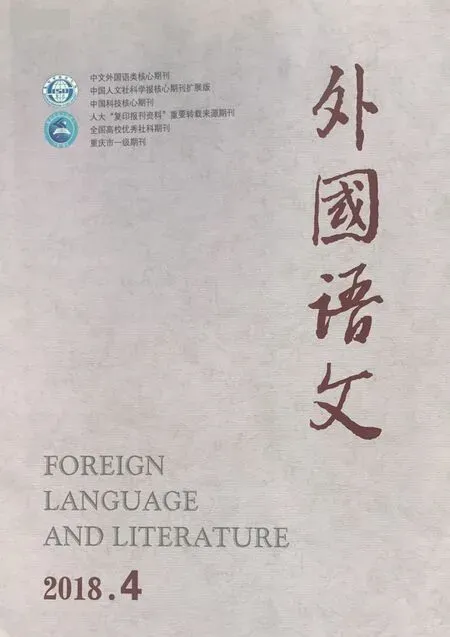翻譯家方重的譯者行為批評分析
周領順 張思語
(1. 揚州大學 翻譯行為研究中心,江蘇 揚州 225127;2. 揚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揚州 225127)
1研究背景
在翻譯研究漫長的時期內,東西方翻譯研究的重點都集中于翻譯的性質、翻譯的標準和翻譯的技巧等方面,而對翻譯的主體——譯者,則缺乏系統的、有深度的研究(穆雷 等,2003:12;周領順,2014:27)。20世紀70年代之后,西方翻譯研究開始出現重要轉向,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都得到了拓展。隨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描寫翻譯學的興起和文化研究取向的盛行,譯者的主體性逐漸得到重視。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翻譯家受到了關注,而蘇籍翻譯家方重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周領順 等,2014)。
方重(1902—1991)是我國著名的文學翻譯家、外語教育家、中古英語專家和比較文學學者。他通曉希臘文、德文、法文、古英文、中古英文、古法文和俄文等語種,是20世紀翻譯領域和文學研究領域中一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者。方重學貫中西,深知翻譯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20世紀30年代后期,方重開始了長達40余載的中西方文學作品翻譯實踐之路。1977年,美國學術學會主席、喬叟研究專家羅明斯基訪問中國期間,專程拜訪了這位七旬老人,稱他“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①。
方重是我國喬叟譯介和研究領域的開拓者,翻譯喬叟作品歷經30年,研究喬叟及其作品長達60年,并根據研究的新發展不斷修訂譯作。方重別開生面地采用散文翻譯,其譯文注重敘事的藝術性,但遇到抒情的短詩,則照樣以詩歌的形式對應之。他的譯文中規中矩,行文縝密清麗,從而造就了譯本樸實平淡、自然無飾的語言風格和清澄深遠的文學意境。《喬叟文集》于1979年再版,深受讀者喜愛,文中的倫敦方言、雙韻體以及諷刺和幽默被處理得恰到好處,讀起來朗朗上口(汪順來,2013)。其喬叟譯文,人物語言聲吻相合,惟妙惟肖(鄭清斌,2010),很好地體現了原作的精神風貌。
1944年方重在赴歐講學期間,開始向西方學術界廣泛介紹我國大詩人陶淵明的詩文。他翻譯陶淵明詩文45篇,并翻譯了一篇我國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蕭統所寫的《陶淵明傳》,后輯為一冊,冠以《陶淵明詩文選譯》(簡稱“《陶選》”)之名,分別在香港和上海出版。這部譯作以蕭統的《陶淵明傳》統領全書,共選詩文98篇,以《五柳先生傳》一文置于卷首,儼然是陶淵明的另一個簡要傳記,并附《歸去來辭》《閑情賦》和《桃花源記》三篇,基本概括了陶淵明的文學創作面貌。為了準確傳遞詩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方重的翻譯在詞匯、句式和修辭手法上對詩文作了靈活處理,向西方世界傳播了中華文化深層的精神實質。
目前,國內對方重的研究主要有三類。第一類,對方重譯著的研究,如王瑤《讀方重的〈陶淵明詩文選譯〉》、曹航《論方重與喬叟》、孫紅梅《論方重先生在〈陶淵明詩文選譯〉中的翻譯特點》等;第二類,對方重學術成就的述評,如李維屏、曹航《方重學術成就評述——紀念方重先生誕生110周年》、謝天振《方重與中國比較文學》、文所《方重教授和他的教學科研成果》等;第三類,對方重為人治學的追憶,如其亞《謹嚴治學一生,桃李遍布天下——記方重教授》、鄭清斌《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上外建校60周年紀念方重先生座談會紀要》等,但尚未見到譯者行為批評視域中有關翻譯家方重的討論。
周領順(2014:12)將翻譯研究視域分為“翻譯內”和“翻譯外”兩個層次。“‘翻譯內’指的是翻譯內部因素及其研究,主要關涉的是語碼轉換上的問題,因此也可以稱為‘語言內’(intra-linguistic)。‘翻譯外’指的是翻譯外部因素及其研究,主要關涉的是社會上的問題,因此也可以稱為‘語言外’(extra-linguistic)。”具體而言,翻譯內部因素涉及語言文字的轉換和意義的再現等翻譯本身的因素,包括微觀上的風格、語氣、情態、詞彩、詞性、標點、句法結構、語篇、詞匯及其聯想意義、韻律和意象等從內容到形式的再現,以及策略和方法、翻譯標準、翻譯單位和意群的具體運用等等,翻譯外部因素則是一些關涉翻譯活動之外的超出翻譯本身的因素,比如宏觀上有關翻譯史、翻譯性質、翻譯標準、翻譯單位和意群的劃分、文本選擇、個人譯風、接受人群和環境、翻譯效果、歷史和時代、審美以及個人和團體目標等因素。翻譯內部的,指的是翻譯實踐本身的事,或者說針對的是翻譯實踐;翻譯外部的,指的是一切關涉翻譯活動的事,既關涉翻譯的外部條件,也關涉評價的角度。只有內外考慮,才可能使翻譯批評盡可能做到全面、客觀和公正。因此,本文從翻譯內和翻譯外兩個層次,論述譯者方重的譯內行為和譯外行為。
2翻譯外:方重的有關思想及其譯外行為
2.1 翻譯目的
方重明確提出,“搞翻譯,要有一個明確的目的——介紹世界上各國文化之精華,促進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搞文學翻譯,說難也不難,主要應有興趣和恒心……有興趣的,都是有希望的;而希望正是在于自己對翻譯所抱之正確目的。” (方重,1983)
早在20世紀40年代,方重便致力于陶詩英譯。“方先生之所以會想到要把陶淵明的詩文翻譯成英文,根據我所接觸到的材料,最直接的原因也許有兩個:一是他在英美兩國訪學期間認識了一批學者,他們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確實懷有真誠的感情,并高度評價中國文學和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謝天振,2005:59)他在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擔任客座教授期間,有緣認識了特里威廉兄弟(E . M. Trevelyan和R. C. Trevelyan),他們都對中國的詩歌饒有興趣,其中大特里威廉還曾與亞瑟·韋利合編了漢詩英譯的小集子FromtheChinese。在那里,他還結識了著名學者迪肯森(G. L. Dickinson)。迪肯森曾親自到訪中國,且刊行了一本《中國佬書信集》(LettersfromJohnChinaman)。“在這本書里,迪肯森沿用當年哥爾斯密所著的《世界公民》的題材與方法,假借一名中國知識分子的語氣,義正詞嚴地指責英國在20世紀初伙同西方其他霸權主義者入侵我國的蠻橫行徑。方先生曾指出,迪肯森的這一正義的呼聲曾‘轟動一時,扭轉了當時西方思想界的一股逆流,抬高了中國數千年固有文化的巨大形象’。”(謝天振,2005:59)
“方先生翻譯陶詩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從接觸到的英譯漢詩的材料中發現,盡管這些漢學家、翻譯家對中國懷有非常友好的感情,但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隔閡,他們對漢詩的理解和表達存在著一些誤譯。”(謝天振,2005:59)與此同時,他們對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認識也不夠充分。以亞瑟·韋利為例,他編選過一本《中國古詩一百七十首》(倫敦康斯特布爾出版有限公司,1918),在該書的序言里,他稱陶淵明為“中國最突出的一名隱士”,但“不是有所創見的一位思想家,不過由于他別有風趣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尚,因而不失其為一個偉大的詩人”云云。這樣的評價讓方先生深感遺憾,所以他要親自翻譯,為的是不讓我國古代這樣一位偉大詩人的“高風亮節”“被世人忽視,或甚至曲解”(方重,1984:2)。
2.2 選材
翻譯的第一步是選材。原文的品位和價值的高下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譯文的優劣,許多翻譯家的譯作自問世以來,一直為人津津樂道,原因之一即是他們在選材上的過人之處。有人說:“通觀翻譯史”,在“選擇原書一層”上能做到像嚴復那樣“處處顧到”者“實未之見”(羅新璋,2009:150)。賀麟也評價道:“講嚴復的翻譯,最重要的就是他選擇原書的精審。”(羅新璋,2009:14)“甚至現在看看他的譯書書目,也可以推斷他是有計劃地介紹‘西方’救民濟世之道的種種學問的。”(陳原,1997:214)相較之下,同時期的“譯人”林紓卻因選材而引人詬病。在鄭振鐸看來,林琴南一生雖先后翻譯外國小說多達一百五十六種,但其中僅有六七十種是著名的,“其他的書卻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譯的”(楊全紅,2007:69)。既是“不必譯”,“他的一大半的寶貴的勞力是被他們(懂外語的口述者)所虛耗了”(楊全紅,2007:69)。
由此,不難看出廣大學者和譯者對選材的重視程度。在這方面,方重也不例外。翻譯哪些作品,要慎重選擇,切忌“揀到籃子里都是菜”(方重,1983)。他認為,翻譯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文化交流,這體現在他的翻譯作品中,早年致力于喬叟的研究和翻譯,其后為教育之需編譯了一些教材,晚年出版了《陶選》和莎士比亞的《查理三世》……無不是斟酌再三的結晶。就《陶選》翻譯而言,也有方重對陶淵明心懷仰慕的因素。譯者在文化氛圍許可的情況下,會盡可能地選擇適合自己審美情趣的原作進行翻譯,譯者總傾向于根據自己的行文風格、氣質風度和美學傾向來選材。正如傅雷在《翻譯漫談》中所說的,“選材就如交友,有些文章不適合我,那就沒有必要翻譯;而有些在第一眼看到時就仿佛我的老朋友。”(羅新璋,2009:692-696)傅雷所說的話,正說明譯者和作者須有相同或相似的品位和興趣,方重希望有更多的讀者能像他一樣,真正地知陶、樂陶、愛陶。
2.3 譯者素養
在長期的翻譯實踐中,方重先生認識到文學翻譯與文學研究的密切關系。他認為“文學翻譯應以研究為基礎”(方重,1983),在動手翻譯之前,必須對作者及其作品進行深入的研究,挖掘作者的生平、時代背景、思想風潮和當時的文學傾向,從歷史的角度在宏觀和微觀上彌補譯者與作者的時空差距。好的詩人或小說家,其修養一定不凡。要譯好其作品,就應努力使自己具備詩人或小說家所具有的理想和情感。當然,修養也是因人而異,因時代而異的。翻譯喬叟作品時就要注意喬叟作為詩人在文學、哲學、宗教等方面的修養,要注意14世紀英國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對詩人的性格、氣質也要熟悉,只有這樣,才能捕捉詩的靈魂,步入詩人創造的意境中,用另一種文字再創造該意境。譯詩歌如此,譯小說也如此(方重,1983)。
以譯詩為例。《無咎詩三百序》寫道:“詩者,感其況而述其心,發乎情而施乎藝也。”*參見https://baike.so.com/doc/7683306-7957401.html詩歌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學形式,是一種闡述心靈的文學體裁。詩人按照一定的音節、聲調和韻律的要求,用凝練的語言、充沛的情感以及豐富的意象,高度集中地表現社會生活和人類精神世界(王麗媛,2014:66)。“一個詩譯者的正確使命是應該向詩人學習,要虛心領會其理想、品格、風貌、情操。要真正譯出一篇詩來,不能不懂得詩人的心靈修養……一位偉大的詩人就是一位偉大的‘詩國’的創造者。凡是世人推崇的這種‘創造者’,無不經受過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大磨煉,并有不朽的表達才能。他們所看到的天地是廣闊無垠的。他為人類開拓了豐富多彩的文藝園地,能做我們精神境界的引路人”(方重,1987:457),“譯者要做好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事業,必須先將詩人或思想家的歷史地位與生活背景搞清楚,然后認真專研其著作,才能譯出好作品”(謝天振,2005:56-60)。
方重在著手英譯陶詩之前,查閱了大量書籍,甚至收集了當時國內外幾乎所有的英譯版本。查明建教授認為,方重的譯文之所以能夠真正抓住陶詩的靈魂,譯得境界全出,一方面與其精益求精,40年磨一劍,不斷修改,以臻完美的翻譯態度有關;另一方面與其研究型翻譯理念有關。凡其所譯,必先研究,因此方重的譯本既是文學性強、與原著了無隔閡的文學譯本,也是學術研究譯本(鄭清斌,2010:151)。方重以研究為基礎的文學翻譯理念對后來的陶詩譯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譚時霖的《陶淵明詩文英譯》(1992)、汪榕培和熊治祁的《陶淵明集》(2003)等,都是在反復研讀原著的基礎上,認真考證,潛心領會詩人的理想、品格、風范和情操,悉心體驗詩人的心靈修養,深入了解詩人的時代背景,知人論世,然后才得以在陶淵明詩文英譯的天地里馳騁的(黃中習,2002)。
2.4讀者意識
方重(1983)認為:“搞外國文學翻譯,還要對讀者負責……一篇譯作,不經過反復的推敲……就不往外寄……今天譯一句,明天譯一段,邊譯邊學,循序漸進,日積月累,必有好處。” 要對讀者負責,首先體現在譯者對譯文質量的把控上;要保證譯文的質量,譯者應首先不斷提高自身的翻譯能力,不可急于求成。方重以30年譯喬叟、40年譯陶詩的經驗告誡青年譯者,譯文出版前,應經過仔細推敲,方可交稿。其他像魯迅、梁實秋、錢鐘書、楊憲益、傅雷等20世紀中國的翻譯大師,之所以能譯出許多后人都無法超越的優秀譯作,成為大師,除了與他們早年在國內接受良好的母語文化教育和熏陶及后來留洋深造,切身感受并習得異國文化與語言的緣故之外,正是他們在實踐中積淀的翻譯技巧與能力,鑄就了他們在中國翻譯史上的豐功偉績。
3 “翻譯內”:《陶淵明詩文選譯》和方重的譯內行為
3.1普通詞匯的求真性處理
方重自20世紀40年代起就致力于陶淵明詩作的翻譯,他在翻譯時力圖再現原詩原意。就詞匯而言,他使用了多種方法再現原字(詞)。比如在陶淵明有關“飲酒”的詩作中,他并未拘泥于“酒”(或者暗含的酒)的字面意思,而是選擇以多種形式呈現原詩的精神。例如《形影神》這組詩中的“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茍辭”句。韋利(Waley,1918: 73)譯為“I beg you listen to this advice —/ When you can get wine, be sure to drink it”,汪榕培和熊治祁(2003: 79)譯為“I hope you accept what I have to say/ And drink the wine they offer while you may”他們都保留了wine一詞。《形影神》是哲理性詩歌,是詩人針對東晉末年佛、道、玄宣揚的神不滅、求道升仙、放誕無為等觀點的駁斥。在《形贈影》中,作者借“形”之口極陳世人對死亡的恐懼:天地山川經年不變,花草樹木兀自隨著自然繁榮凋敗。而人枉有靈性,一旦逝去便絕無可能歸來。“我”并無成仙之術,有朝一日終會死去。如此這般,不如得酒便喝,無須推脫。王瑤(1956:39)認為,與wine相比,drink更側重指喝酒這一行為(the act of drinking alcoholic beverages or the act of swallowing)。方重(1984: 77)譯為“I wish you would take my words to heart,/ And drink, while offered, and say not ‘nay’”。方重譯本簡潔明了,毫不拖泥帶水。《形影神》作成三年后,陶淵明又寫下了《飲酒》組詩。此時政治動蕩,朝局混亂,正直的陶淵明絕不肯為社稷建功,因此這組詩雖是酒興之作,但時局之影、平生歷程、清操與卑微之分,綽然可見。在“其九”中有句:“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韋利(Waley,1918: 72)譯為“Let us drink and enjoy together the wine you have brought:/ For my course is set and cannot now be altered”,汪榕培和熊治祁(2003: 117)譯為“Let’s forget about it and have a drink,/ But I will never change my mind, I think”,而方重(1984: 103)則譯為“Let us now raise our cups and rejoice;/ Never shall my life’s course be altered”,“其九”寫的正是有田父勸說改道,陶淵明堅定信念,再次表明自己隱耕山野的志向。末尾兩句“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是詩人借舉杯歡飲勸誡友人切勿再提勸仕一事的事。既是舉杯歡飲,raise the cups顯然比drink和have a drink更加具體、形象,雙方也因著舉杯會意了并未宣之于口的“切莫再提”。相較另外兩個譯本,方重譯本更簡潔、穩重,也更加準確,求取了原文的真意,還原了真實的語境。
這種翻譯方法還體現在疊詞的翻譯上,如陶詩中頻繁出現的“依依”一詞。方重把“依依在耦耕”譯為“So tenderly my heart Clings still to the soil”(方重,1984: 7)、把“依依墟里煙”譯為“Where chimney smokes seem to waft in mid-air”(方重,1984: 41)、把“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譯為“Are you straining your voice for the distant blue?/ Yet back and forth, how unwilling to depart!”(方重,1984: 87)等,他根據不同語境,靈活調整譯文。譯者用了三個不同的動詞描寫依依不舍,不肯散開,不愿離去的情景,就像一位高明的醫生,看了三個癥狀相同的病人,卻診斷出了不同的病情,并且對癥下藥,開出了不同的藥方一樣(許淵沖,1981)。
3.2文化負載詞的務實性處理
王佐良(1989:18-19)說:“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的文化人,譯者一方面要深入了解外國文化,另一方面譯者還得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不僅如此,他還要不斷地把兩種文化加以比較。他在尋找與原文相當的對等詞的過程中,就要做一番比較,因為真正的對等應該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義、作用、范圍、情感色彩、影響等等都相當。”在翻譯陶詩的過程中,其獨特風格和深厚文化內涵的再現同樣重要。例如:虛舟:the barge of Time、星紀:(the stars are heading for)、神淵(the magic face of waters)、曲肱(pillowed on the benched arm)、華嵩:the sacred mountains。
這些詞來自陶淵明所作《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詩。其中,“虛舟”出自《莊子》“列御寇”篇:“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虛而遨游者也”(田晉芳,2010:74),形容一種大智若愚、放任自流的人生態度,陶淵明借此嘲諷自己,竟在官場虛度了數年。方譯以“時間之舟”(the barge of Time)替換“虛舟”,并將詩句轉譯為松弛的船槳徒勞無功的揮舞,漫無目的地漂流在洪流之中。盡管譯文摒棄了原文的表象,卻更加形象而富有象征意義;“星紀”原為古代天文學、星相學的專門名詞,有的注釋者就據此考定了此詩的寫作年代(田晉芳,2010:74)。方譯省略了相關考證,將其譯為the stars(are heading for),即“星辰所指方向”,簡明通俗,巧妙契合了星辰運轉與歲月流逝的關聯,求得了與原文原意相當的功能。“神淵”的翻譯也如此。“神淵”歷來飽受爭議,它是否指代祭祀所用的水淵?有人干脆采用異文“神萍”,主張“萍”是“屏”的同音通借,指古代傳說中的雨師屏翳(田晉芳,2010:7)。方譯避開了這個困境,將“神淵”譯為“the magic face of waters”。方重的務實性處理,還體現在他把八首出現官職名稱的詩都代之以詩文的主題,從而放棄了原文的形式:
和郭主簿(Life’s Simple Diet)、和胡西曹示顧賊草(Soul’s Desolation)、五月旦作和戴主簿(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ifth Month)、和劉柴桑(My Cot in the West)、酬劉柴桑(Autumn Again)、贈羊長史(A Message)、酬丁柴桑(A Friend, a Friend)!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A Complaint
“曲肱”出自《論語》“述兒”篇:“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田晉芳,2010:7)它形象地表現出安貧樂道、守節固窮的精神,方譯此處采取了直譯,是求真性處理。而“華嵩”在漢語中自有崇高神圣之意,方重將其意譯為“圣山”(the sacred mountains),說明他是為了更好地務實于讀者而把它作為可讀性較高的文學語言來對待的。
總之,方重對于文化負載詞的翻譯,采用的方法靈活多樣,有的避開表面形象而求取真意;有的避開原文難以求真的歷史信息而求取功能的相當;有的為突出可讀性而作為文學語言對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3.3句法和篇章轉換于“求真”與“務實”之間
在句法層面,方重主要使用了調整譯文詞序、在譯文中增加主語及修辭再現等技巧。以《歸園田居》(五首)為例。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當為辭去彭澤縣令歸田次年所作(王瑤,1956:27),第一首描寫他的歸耕之樂,第二首寫他的交往純樸,第三首寫耕種的實感,第四首寫探訪遺跡,第五首寫耕余之歡。《歸園田居》(其一)共20句,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前八句陳述詩人因鄙夷仕途而歸田,中八句描寫平和靜穆的田園風光,后四句抒發詩人的恬淡心境和愉悅心情。(汪榕培,1998)比如“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句,韋利(Waley,1918: 77)譯為“When I was young, I was out of tune with the herd:/ My only love was for the hills and mountains”,汪榕培和熊治祁(2003: 53)譯為“I’ve loathed the madding crowd since I was a boy/ While hills and mountains have filled me with joy”,但方重(1984: 51)則譯成“For my youth I have loved the hills and mountains,/ Never was my nature suited for the world of men”。在形式上,上述三種譯本都添加了主語“I”,這是譯者考慮到英語語法和中英不同思維模式所做出的合理選擇,以便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但方譯中的詞序也發生了變化,將其譯成了“少本愛丘山,性無適俗韻”。
內容上,前兩句“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看似平實,實則難譯。“韻”的原意是“和諧的聲音”,也可以泛指“聲響”和“聲音相應和”,在特指的時候可以代表“氣韻”或“神韻”,進而表示“情趣”“氣質”和“性情”。本句中“韻”即“氣韻風度”(王瑤,1956:27)之意。再如“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句,韋利(Waley, 1918: 77)譯為“I had rescued from wildness a patch of the Southern Moor/ And, still rustic, I returned to field and garden”,汪榕培和熊治祁(2003: 53)譯為“So I reclaim the land in southern fields/ To suit my bent for reaping farmland yields”,而方重(1984: 51)譯的是“Back to my land I cling to solitude,/ To till the soil in the open south country”。此句表現的是詩人自知不懂技巧,不若到南面的田野去開荒而返歸田園之意。詩人陶醉于躬耕之樂,與生活和自然融為一體,不同于西方游離于生活之外的田園詩人。在形式上,方譯顛倒了兩句的次序,實則還原了原詩的邏輯,也更符合英文讀者的寫作習慣。可見,方重的譯文是在理解原詩、忠誠于詩人的基礎之上,求得了譯者行為中“求真”與“務實”間的平衡的。
在篇章上,方重在充分解讀原詩的基礎上,對譯文進行了靈活分割。如在《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中,他并未遵循中國古典詩歌單篇的通常形式,而是根據詩篇的思想將內容分成了三小節:第一節即景抒情,就五月初一早晨景色抒發感想;第二節上升到對命運和人生的感慨上;第三節(實即原詩最后一句)警句式地結束全詩,點明當下即刻的生活所能夠超越的主題。這樣調整后,意旨更加豁亮,格式也更加活潑。
4 結語
翻譯家方重是學者型譯者,他的翻譯活動和學術研究是分不開的。正如王秉欽(2004:212)所說的,這類譯者“翻譯什么,研究什么;研究什么,翻譯什么”。作為學者型譯者,方重正是在充分研究陶淵明生平、思想及其作品的基礎上,對陶淵明的大部分詩文進行了翻譯。他并不拘泥于詩文的字面含義,重在表達原詩的內在精神,“在翻譯方法上偏重意義,認為翻譯的目的就是讓外國人看得懂,沒必要字字對應”(周領順,2014:167)。為求完整傳達原詩意境,他并未刻意追求譯文的“音韻美”,相較于亞瑟·韋利和汪榕培譯本更加準確。不可否認的是,方重遣詞用句都力圖再現陶淵明的“超脫”情致,保留其思想精華,這與他傳播中華文化的翻譯目的并行不悖;他作為一名譯者,既進行翻譯外的努力,也進行翻譯內的嘗試,內外的思想和行為一脈相承,并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既“求真”于原文和作者,又盡可能“務實”于讀者和社會。方重是一位成功的翻譯家,他的翻譯思想和理性的行為,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研究成果可給后來者以有益的啟發,為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提供指導或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