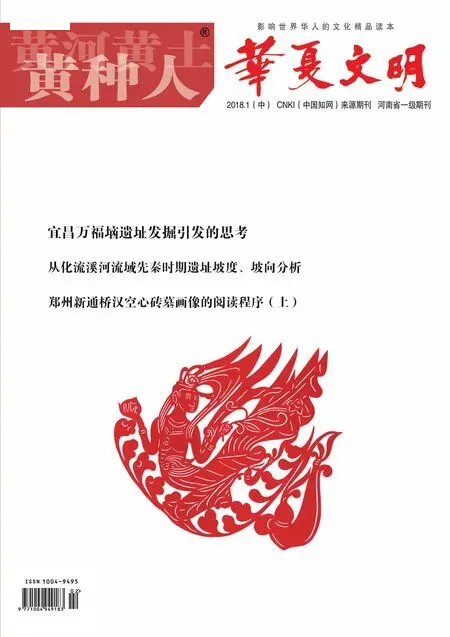洛陽出土的五代石硯芻議
□趙菲菲
硯臺,是我國傳統的文房用具,以其獨特的神韻與藝術價值被譽為文房四寶之首,在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傳播過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相對筆、墨、紙而言,硯臺材質多樣,有石、陶、瓷、澄泥、銅、漆等,大多能長期保存下來。除少量傳世品外,考古發掘是我國古硯臺的一大來源。考古工作者在洛陽地區的考古發掘中,就曾發現1件形制、造型較為罕見的五代石硯。(圖一)
這件石硯出土于洛陽隋唐城外郭城南約2公里,龍盛安置小區B區的一座五代墓中(編號 C7M4539:3)[1],現藏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此硯呈箕形,由深紫紅色石雕琢磨制而成,硯首與硯尾略弧,硯面自硯尾向硯首平緩下傾,四角稍尖,平底,硯面周邊有子口可承蓋。硯蓋四剎陰刻兩周實線,蓋面中間靠下部陰線淺刻一只頭頂飾開叉角的鹿,昂首翹臀,兩前肢略彎曲,兩后肢直立,做恣意站立狀。硯面與子母口周圍殘存有墨痕。長11.9厘米、寬10厘米、高2.9厘米。
一、概說
洛陽地區五代時期的硯臺形制基本沿襲唐代箕形硯,如早期洛陽十七工區93號墓出土的1件晚唐—五代硯臺、二十九工區出土的4件晚唐—五代硯臺、機瓦廠采集的硯臺,以及二十九工區出土的1件五代—宋硯臺,均為箕形陶硯[2]。這幾件硯臺,除二十九工區1件箕形硯硯尾底部有雙足痕跡(可能在燒造前削平)外,所有的箕形硯均為硯首略窄、硯尾稍寬、硯尾底部有二足。其中,十七工區出土的箕形硯硯首作三曲形,呈三道粗凹槽,有水池之用。其余的箕形硯均無修飾,是典型的箕形陶硯。此外,二十九工區354號墓出土的后晉平臺斜面灰陶硯,斜面呈箕形。背面為長方形框,凹下,陰刻銘文28字,似一首七言律詩。硯前、后側有桃形圖案,左側有回字紋飾,右側上端刻一鷹,下有五言絕句一首,并有紀年“天福二年八月營造記之”[2]。這件硯臺是洛陽地區早期出土五代時期硯臺中的精品,通體呈平臺形,硯面作箕形,背面為長方形框,既延續了唐代箕形硯的形制,又有宋代抄手硯的風格。

圖一 五代石硯(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收藏)
近年來,洛陽考古出土的五代硯臺見諸簡報的僅2件,其中,后梁高繼蟾墓出土的箕形陶硯[3]亦是硯首略窄,硯尾稍寬,硯尾底部飾有二足,沿襲唐代箕形硯風格。另外一件,就是龍盛安置小區出土的這件五代石硯,該硯跟上述見諸發掘報告的洛陽五代時期硯臺均不相同。首先,質地不同,上述硯臺均為陶硯,而龍盛小區的這件硯臺為石硯。石硯在漢代以前、宋代以后較為多見,魏晉南北朝時期瓷硯與陶硯等新種類硯逐漸涌現,到唐至五代時期,硯臺的質地主要以陶硯為主,石硯較為少見。其次,形制不同。這件石硯是由硯身與硯蓋組合而成的盒式箕形硯,形制雖為箕形,但是硯身平底無足,硯蓋上刻畫一閑庭信步的梅花鹿作為裝飾,意趣悠然。漢代以后,我國出土硯臺多不帶蓋,因而這件五代帶蓋石硯就顯得獨具特色。
二、形制特點
洛陽出土的這件五代石硯,造型別致,在我國考古發掘出土的硯臺中較為少見,目前僅三門峽市博物館收藏的1件帶蓋箕形紫石硯(圖二)與其相似。三門峽市博物館收藏的這件石硯,屬唐代石硯,是1985年在該市糧食局上村嶺糧庫工地施工中發掘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這件硯臺也作箕形,由硯身和蓋兩部分組成。硯尾較硯首寬,底部于硯尾處飾二梯形足,硯面自硯尾緩緩下傾至硯首,硯池內殘存大量墨痕,周邊有子口可承蓋。蓋一側,楷書“紫石硯”,四剎飾陰刻線二周,線內畫如意流云紋,蓋面近硯首處也淺刻如意流云紋。近硯尾處,雕一頂有開叉角的梅花鹿,鹿四肢均隨意彎曲,做行走回首狀,且鹿口銜仙草,可能寓意鹿(祿)回頭,所刻鹿紋通體施黑彩。通高2.6厘米、長15.8厘米、寬12厘米。
洛陽龍盛小區五代石硯略晚于上述三門峽唐代石硯,形制與紋飾相似,但也存在差異。其一,底部特征不同。三門峽唐代石硯硯尾底部仍有足,具有唐代箕形硯的典型特征。洛陽的五代石硯已演化為平底。其二,鹿的形態也略有差異。三門峽唐代石硯所飾鹿銜草回首,可能有祿回頭之美好祈愿,且鹿身明顯繪出梅花斑點,做行走狀。洛陽五代石硯則以簡練的線條刻繪出鹿的形體神態,鹿身不見梅花斑點,做站立狀。其三,蓋面紋飾有區別。三門峽唐代石硯蓋面的紋飾比洛陽五代石硯略豐富,周邊及首部加飾如意流云紋,且鹿銜仙草紋遍施黑彩,整個蓋面顯得更為厚重。總之,與三門峽唐代石硯相比,洛陽的這件五代石硯整體造型與紋飾更簡練,于實用之外,透露出文人的豪邁奔放與灑脫不羈,是這一時期洛陽乃至全國硯臺中的精品。

圖二 唐代石硯(三門峽市博物館收藏)
三、洛陽五代石硯取材
三門峽市博物館所藏唐代石硯,取材系虢州石中的紫石。細觀洛陽五代石硯,呈紫紅色,與三門峽唐代石硯石材極其相似,唯色澤更為鮮亮,石質更加純凈細膩,應該也是取材虢州石。虢州石是歷史名石,又名紫陶石,產于河南省盧氏縣北部及靈寶市南部,質地細膩,柔滑如膚,潤澤似玉,硬度較軟,易于刻磨,是制作硯臺的優良石材。虢州石中鐵紅色石多,紫色石數量較少,尤其是紫紅石,石質優良、圖案精美者更少,因而虢州石中的紫紅色石,被歷代文人雅士所珍愛,多用來刻成硯臺。
虢州硯,又名稠桑硯、鐘馗硯,以其色彩斑斕、柔而不綿、發墨不滲等優點,為歷代文人墨客、皇室貴族所青睞。唐代名人留下了不少相關記載,如杜佑《通典·卷六·食貨六》載:“弘農郡,貢麝香十顆,硯瓦十具,今虢州。”[4]李匡乂(又稱李濟翁)在《資暇集》中對其作了詳細的描述:“稠桑硯,始因元和初,愚之叔翁宰虢之耒陽邑,諸季父溫凊之際,必訪山水以游。一日于澗側見一紫石,憩息于上,佳其色,且欲□□□□□□□□隨至,遂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復無刓缺,乃曰:不刓不麩,可琢為硯矣。既就琢一硯而過,但惜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步許,往往有焉。又行乃多,至有如拳者,不可勝紀。遂與從僮挈數拳而出,就縣第制斫。時有胥性巧,請斫之形出甚妙,季父每與俱之澗所。胥父兄,稠桑逆肆人也。因季父請,解胥藉而歸父兄之業,于是來斫。開席于大路,厥利驟肥。士客競效,各新其意,爰臻諸器焉。季父大中壬申歲授陜令。自元和后,往還京洛,每至稠桑,鐫者相率輒有所獻,以報其本,迄今不怠。季父別業在河南福昌邑。下至于弟侄,市其器,稱福李家,則價不我賤(然則其石以為諸器,尤愈于硯)。”[5]由文獻記載可知,虢州石硯早在唐中期就已經出現,并深受廣大文人的喜愛,被列為皇室貢品。此外,宋代文人的著作中,也有對虢州硯極高認可的記載,如書畫泰斗米芾在《硯史》中論及虢州石,稱其“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回硬,墨磨之則有泥香”[6]。時至今日,虢州硯在一些收藏機構和收藏家眼中,仍然極具收藏價值,或可與端硯、洮河硯、歙硯、澄泥硯等四大名硯相提并論,為我國歷史名硯之一。
四、結語
洛陽這件五代石硯,整體造型雅致,雕琢精細,線條流暢,美觀大方,硯蓋所飾梅花鹿生動逼真,意態盎然,在我國同時期硯臺中較為少見,稱得上洛陽乃至我國五代時期硯臺中的上佳之作。此硯取材為虢州石中罕見的紫紅石,色澤油潤,細嫩純凈,也是虢州硯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故而,這件五代虢州石硯具有極高的藝術與歷史價值,為我國硯臺之海增添了精品,也為洛陽乃至我國五代時期硯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附記:本文中三門峽紫石硯照片由三門峽市博物館館長李書謙、保管部主任郭婷提供,在此謹表衷心感謝!
[1]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龍盛小區兩座小型五代墓葬的清理[J].洛陽考古,2013(2):50-58.
[2]洛陽市博物館.洛陽市十五年來出土的硯臺[J].文物,1965(12):37-50.
[3]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后梁高繼蟾墓發掘簡報[J].文物,1995(8):52-60.
[4]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8:114.
[5]李匡乂.資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5:22.
[6]米芾.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譜錄類 09硯史[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84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