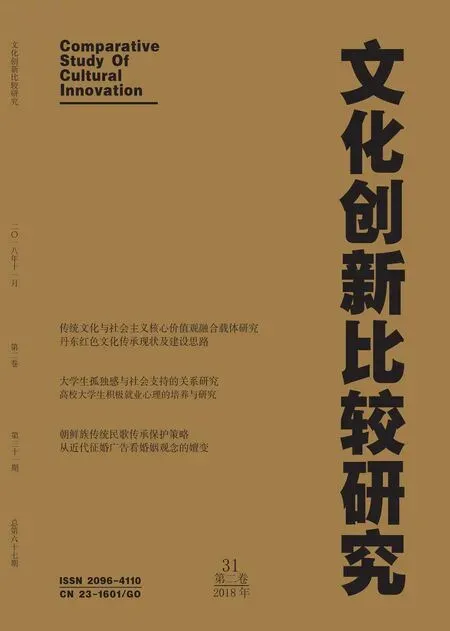從飲食角度看中日文學(xué)
——以《水滸傳》與《心》為例
王啟正
(巴彥淖爾市臨河區(qū)第一中學(xué),內(nèi)蒙古巴彥淖爾 015000)
“民以食為天”這句中國諺語道出食物是人物質(zhì)上的依賴物,而人在精神上的依賴物當(dāng)屬文學(xué),尤其是隨平民文化而興起的小說。中日文學(xué)和飲食文化師出同門,除了有共同受《詩經(jīng)》影響下而產(chǎn)生的獨特的留白,也有受地理影響而產(chǎn)生的東亞文化的相同點,比較文學(xué)家或美食家喜歡在文學(xué)或飲食各自領(lǐng)域?qū)χ腥瘴幕M行對比,但若將飲食與文學(xué)結(jié)合思考,并對中日文學(xué)加以比較,我們會看到更多從未發(fā)現(xiàn)的美感,除了可以增強我們自己的文化自覺或自信之外,也能對日本文化多一份理解與包容。
1 中國的飲食與文學(xué)
先說中國飲食,中國的飲食更注重調(diào)味,即用龐雜多樣的次要元素來凸顯主元素,如川菜中的魚香肉絲,菜品的主味是魚香的甜辣,口感是肉感,色澤為紅,但其往往會加入筍、木耳等并沒有味道的蔬菜,為了補充硬脆的口感與白黑綠的色澤。試想:若僅有肉的魚香肉絲,是否會因缺乏對比以致麻痹舌頭,從而嘗不出肉的豐腴了呢?但調(diào)味并不光是襯托,筍、木耳也為菜品提供了深層次的品感。這與日本料理有著極為顯著的不同。總而言之,中國的飲食中主料與輔料是菜品的首要元素,一個精細的廚師總是從這兩方面考慮菜品的選材,并通過這兩方面的配合發(fā)揮一道菜的真正味道。
再說中國文學(xué),食物上的特點很明顯地折射到了文學(xué)上,以《水滸傳》為例,在《風(fēng)雪山神廟》一章中林沖受一系列情形所逼,最終投靠梁山,從故事中的情節(jié)我們不難看出,林沖上梁山并不是一個完全的、原始的自發(fā)行為,而是在多方外力推動下完成的。在誤入白虎堂之后,林沖絲毫未改本性,情愿在滄州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絲毫沒有上山當(dāng)土匪的念想。
在《刺配滄州道》中押送路上林沖受兩個端公設(shè)計陷害,并被魯智深相救后,他也僅表示 “饒他兩個性命”,仍不愿落草為寇,執(zhí)意去滄州做一個好囚犯。之后,在管營、差撥的妥協(xié)與陸謙、富安二人的步步緊逼的情況下,才借著酒勁兒將情感全部釋放,最終完成了性格與命運的巨變。通過這一切的情節(jié)我們不難看出,在林沖性格的完成過程中,所有的推力與襯托都來自外界,哪怕最后的激情殺人也借了不少酒勁。文中另外一個較為重要的人物李小二,除了表面上起到聯(lián)系人物環(huán)境的作用之外,他更有一個深層次的作用,即用其保守、冷靜來襯托林沖的更保守更冷靜,在得知陸謙、富安二人的到來與陰謀后,李小二勸林沖 “小心不為過”“莫焦躁”,卻不知后文林沖比他更為周全,哪怕在激情殺人之下,也冷靜而有邏輯地砍頭祭天,收拾行李,還不忘帶上半壺冷酒向東走去,因為西邊兒有集市。李小二起到了襯托的作用,正如前文所提的魚香肉絲,用一道勝過一道刺激的輔料來完成主料。如果用一個恰當(dāng)?shù)谋扔鱽砜偨Y(jié)此段那便是兩位主角像是鐵軌上的火車,其他的一切配角與其他要素都是鐵軌與信號系統(tǒng),引導(dǎo)主角前往某處。
2 日本的飲食與文學(xué)
接下來看日本的飲食,在日本的飲食文化中,食物的味道被分成了相對獨立的單元,并使用了極少的調(diào)味,以此呈現(xiàn)食材最原始本質(zhì)的味道,先以較有代表性的壽司為例,從整體上講,在壽司宴中,各個壽司以淡味到濃味的順序相對獨立地享用,相鄰壽司間還會利用姜來阻止味道存留延續(xù)形成“串味”。從個體上講,壽司在其內(nèi)部也是米飯與魚肉的單純的結(jié)合,兩者涇渭分明,高級的壽司往往注重肉的新鮮度,還原其中味,其他的日本傳統(tǒng)食物,如懷石料理,牛片,或多或少地遵循此規(guī)則。
再看小說,以夏日漱石的代表作《心》為例,在《心》中主人公自然為先生,在先生幼年受騙—愛上小姐—害死情敵—最終自殺的過程中,“我”只承擔(dān)了一個講述串聯(lián)者的任務(wù),是一個利用信營造結(jié)局的工具人。例如,前部分疑似作為主角的“我”,其行為大都是與先生有關(guān),“我”的家事在完成引出先生的感慨的使命后就草草地結(jié)束。其中“小姐”或多或少的曖昧舉動是促使先生反詰內(nèi)心與考慮自身情感的導(dǎo)火索,自小姐出現(xiàn)后,信中對自身感情的剖析篇幅大量增加,K的任務(wù)也只是先生的內(nèi)心深處陰暗面得以釋放的一個“物體”,K加入這場爭奪小姐的戰(zhàn)斗的過程也即是先生陰暗性格的暴露過程,與其說是K之死改變了先生的性格,不如說是暴露了先生本身的內(nèi)在性格,而這也正是該小說的主題,正如日本飲食的顯著特點,重點在突出主要角色的本質(zhì)與內(nèi)在的性格。
3 中日文學(xué)共性
當(dāng)然,作為師出同門的中日文化其文學(xué)與食物中的共性也極為顯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留白”。此詞最先用于描述中國畫,但其在飲食與文學(xué)領(lǐng)域也同樣適用。例如,西方菜中常出現(xiàn)作為主食的豆、薯味,多半?yún)⑴c了與其他食材共同的料理,而看似例外的面包,其實也融入了黃油,奶油的參與和烘烤,這與我們的大饅頭是兩樣的。中日飲食中主食脫離了共同程序,作為單獨的一項出來,如米飯、面條這樣的主食,自然承擔(dān)了飲食中獨特的留白任務(wù)。
在中國文學(xué)上除了《詩經(jīng)》與“唯見江心秋月白”等名句之外,《紅樓夢》也多次使用了留白的手法,三十五回末與三十六回始,寶玉叫黛玉,卻又在下章無有后續(xù),這便也是一個留白了,其實讀者不難猜出,此后便是寶玉如何安慰黛玉,而若不采取這手法,將細節(jié)再寫,難免重了三十四回的老套,而眾觀整個紅樓,無論是各個各物的話中話,局中局就連飯桌上的一肴一菜,一行一動,都充滿意味,而作者從不真心點出,最多也只是借角色之口對讀者再稍加指點,全憑留白靠讀者想象。
而在《心》中,作者有意對先生的來歷、身份、其特殊古怪的行為、性格,妻子都半遮面,在最后信件到來前,先生與“我”最后一次相會散步并許諾告其真相時,也使用清淡筆法,除了留了個神秘吸引讀者之外,還有一層以清淡現(xiàn)狀烘托信件而帶來的高潮爆發(fā)的意味。
4 結(jié)語
中日飲食小說的共性一是由于兩國在地理上的相似與鄰近,二是同受儒家佛教的影響,個性之處則中國地處大陸,對外交流相對頻繁,加之氣候多樣、物產(chǎn)豐富,使得飲食與文化走向“雜”,而日本地處島國,文化相對封閉,使得飲食與文化走向了“純”。在近年全球化的時代,中日之間產(chǎn)生了巨大的交集,中國的飲食影響到了日本,發(fā)明了日式拉面“雜”的食物,中餐也在日本受到普遍歡迎,近年日本的斷舍離、簡約的設(shè)計風(fēng)格與生活理念,也深受中國年輕人喜愛,,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兩國在物質(zhì)文化,精神文化上的友好往來與相互學(xué)習(xí),進行兩國的文化及文學(xué)比較研究,不但在學(xué)術(shù)上能有所建樹,更能開闊國民視野,促進文化交流,在擺脫民族主義上起到積極有意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