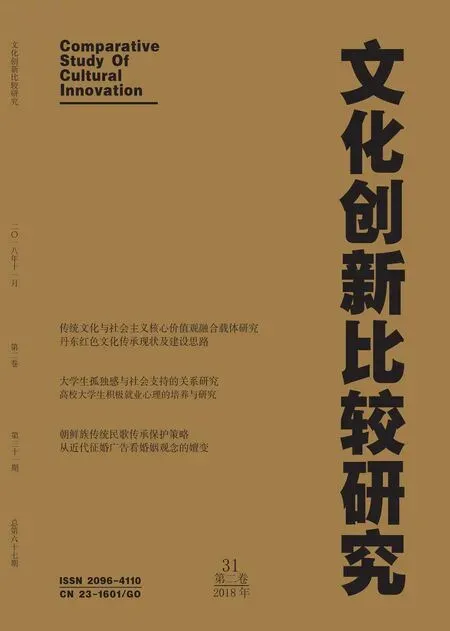儒家思想與日本近代化
孫作文
(棗莊學院外國語學院,山東棗莊 277160)
1 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承
儒家思想傳入日本的具體時間仍無定論,但一般研究認為,據《日本書紀》和《古事記》記載,285年,朝鮮百濟博士王仁攜《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經典到日本,儒家思想開始傳入日本。6世紀,百濟五經博士相繼來日,將大量的儒家經典帶到日本,并為宮廷貴族講授儒學。大和政權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后,將儒家的“德政”思想作為治國、施政之道[1]。比如,圣德太子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參考,制定了晉升以才能為本,以德、仁、禮、信、義、智命名的冠位十二階制度以及訓誡群臣的日本第一部成文憲法 《十七條憲法》。隋唐時期,兩國間使者交流頻繁,中國的文化制度和思想進一步被吸收,并在其后的大化改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7世紀的大化改新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以唐朝制度為藍本,建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權體系。701年,日本以儒家思想為基調,編訂了有名的《大寶律令》。隨后各地設立學校、大學寮等教育機構,學習《禮記》《春秋左傳》《周易》《論語》《尚書》《孝經》等課目。
北宋時期,在先秦儒學的基礎上,吸取佛教、道教和哲學思想精華,儒家思想體系進一步成熟化,南宋朱熹創造了理氣世界觀集大成的朱子學。朱子學又稱宋學、新儒學,主張天人合一,講究“格物致知、居敬窮理”。廉倉、室町時代新儒學在日本主要依靠五山禪僧傳播,江戶時代開始從從屬于禪宗的狀態脫離。相國寺禪僧出身的儒學大師藤原星窩從16世紀開始推崇理學,提出儒學正是適用于約束封建倫理規范的思想,標志著儒學開始實現獨立狀態。其弟子林羅山主張天地有上下之分,人倫有尊卑之別,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古今不可亂。其思想與幕藩秩序維持的統治目的相一致,因此江戶時代朱子學被尊為官學,衍變為了官方意識形態。江戶后期,除朱子學派外,倡導人的主體精神和實踐的明陽學派、呼吁從古典中探索儒家思想真義的古學派等各儒家學派林立。伴隨著各個學派的興起,各地設立教授四書五經和中國啟蒙讀物的學校、私塾、寺子屋,儒學開始從皇室公卿的上層社會擴散到平民大眾中。比如,商人出身的石田梅巖,吸收儒家思想,主張商人應追求正當利潤,遵循正直、簡約的職業倫理道德,創立了著名的町人倫理思想的石田心學。
近代之前,儒家思想的影響從政治理念擴散到倫理道德領域,并與日本本土的神道思想和從中國傳來的佛教思想相互滲透結合,共同凝結成了日本的民族精神的“和魂”。
2 全面向西方學習的近代化歷程
18世紀,幕府體制的種種矛盾顯露,沉重的年供和高利貸導致民不聊生,武裝起義接踵不斷。為緩和社會矛盾,維護幕府體制,德川幕府在享保、寬政、天寶年間分別進行了三次改革,但抑商重農和限制人口流動的政策有悖歷史發展的趨勢,更加招致農民和商人的不滿,三次改革均以失敗告終。同時,在日本實施鎖國政策的200年間,世界局勢發生著巨大變動。相繼進入資本主義時代的西方各國為了延伸勢力范圍,打開了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的國門。1739年開始,俄羅斯試圖與日本實現通商,19世紀初期在中國獲得勢力范圍的英國也開始向日本接近。內憂外患形勢下,諸藩開始實施改革,登上了幕末的政治舞臺。諸藩鼓勵洋學,各藩設立的藩校最初學習以朱子學為主的儒學科目,后期引進洋學和國學內容。學習西洋炮艦技術,制造購買西洋武器。實行殖產興業,藩營的西式機械生產工場相繼設立,民間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出現了近代化的胎動跡象。
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馬修·佩里司令率四艘軍隊抵達日本,堅船利炮威脅下日本被迫開國通商,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友好通商條約》,結束了閉關鎖國狀態。一睹昔日大國中國在鴉片戰爭后接連受辱,愛國藩主和有志之士開始擔心日本的淪亡。藩主和志士們將朱子學的尊王賤霸、春秋大一統的思想與日本神道精神相結合,希望恢復天皇大權,“尊王攘夷”的思想運動不斷擴展。薩英戰爭中的羞辱以及幕府鎮壓使各藩不滿情緒進一步高漲,“尊王攘夷”運動轉為激烈的 “倒幕”運動。改革中崛起的薩摩和長州兩大雄藩,成為倒幕運動的主力。兩藩倒幕勢力在愛國人士支持下于1869年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統治。武家專權的封建時代終結,日本歷史開啟了近代的新篇章。
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展開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改革活動,即著名的“明治維新”。頒布以向外學習為核心,強國卸辱為“五條誓文”。奉還版籍、廢藩置縣,加強中央集權。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實現四民平等。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創辦近代產業,生活樣式和風俗習慣全盤西方化,在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三大政策的引導下,日本迅速發展成為近代強國。
3 儒家思想與日本近代化
日本近代化雖然憑借的是西方文明,但傳統的儒家思想并未阻礙西方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也未因此退出歷史舞臺。相反,如同韓國學者黃健泰所說,“愛國志士的現代化行動中的精神支出和思想依據都是由日本儒家學說和理論提供的”[2]。主張 “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的朱子學在江戶時代被奉為官學,并得到廣泛學習傳播,起到了開啟民智的作用,為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認知世界、積極主動地向西方學習培養了理性的思維方式。如李守愛所說“此種客觀性合理主義態度,后來成為日本人接受西洋自然科學的母胎”[3]。此外,明治維新運動的先驅吉田松陰主張應勇于批判和改造不合理的體制。其中倡導勇于實踐改革的行動精神的明陽學對吉田松陰有著重要的導向作用。
另一方面,全盤西化的運動為日本社會注入了新鮮血液的同時,也給明治政府的統治帶來威脅。如在教育制度方面,最初明治政府實施完全西式的教育。但隨著追求自由、民主、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的西方思想的普及,反政府的自由民權運動風潮掀起,對此,明治政府修正了全面歐化的教育政策,將教育目的改為維護國家統治。1890年起草的教育敕語中強調教育應以“忠君愛國”“忠孝一致”的儒家家族主義思想為基礎,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民族精神。形成了在倫理道德方面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科學技術方面向西方學習的教育方針。可見,儒家思想抵制了西方個人主義對日本社會的入侵,有效避免了變革時期的社會動蕩。此外,明治維新后開辦的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多是曾受過儒家思想熏陶的官僚,實業家的意識形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儒家思想為日本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經營提供了方法和理論上的支持。日本企業之父涉澤榮一提出了著名的“論語加算盤”理論,主張“經濟道德合一”,將儒家思想運用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經營中。儒家思想為日本近代化客觀上提供了有效地幫助。
儒家思想似日本歷史長河中一股源源不斷的文化底流,已經沉淀為日本民族靈魂的重要部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以不同的方式推動著其社會發展。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日本始終主張“和魂洋才”的思想,如上所述,儒家思想和“和魂”是一脈相承的。正如朱子學家兼洋學家的佐久間象山提出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日本將儒學的有效范圍的限定在日常道德方面,同時積極攝取西洋的知識和學問。以現實和合理的態度進行取舍、整合,使儒家思想和西方文明交相輝映,成功地迎接了近代化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