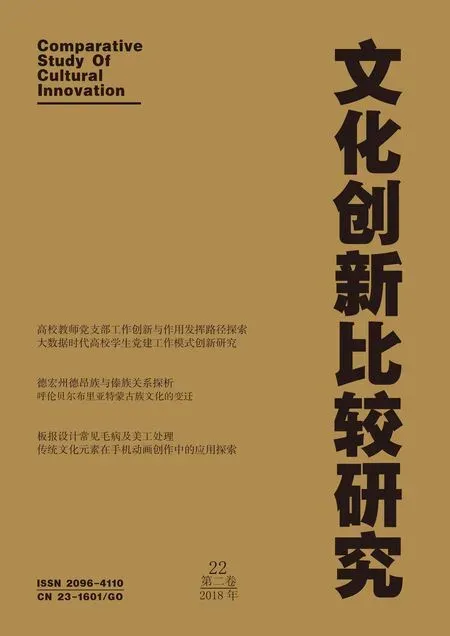薇拉·凱瑟小說中道家生態思想闡述
牛艷爭
(淮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安徽淮北 235000)
科技的迅猛發展使得人類社會在高度享受物質文明成果的同時伴隨著一系列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要延續人類的生存就必須開創一個新的文明形態,也就是生態文明。黨的十八大從建設“美麗中國”的高度把生態文明置于貫穿五大文明建設的始終,要求全黨全社會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足見生態文明建設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對于如何解決關乎人類生存的種種困境,我們完全可以從扎根于農業文明、提倡“順應自然”的中國傳統道家文化中找尋答案。道家認為人類只有知道自然的根本規律,才能夠認識天地萬物的限度,從而限制自己的行為和不切實際的欲望,才能明智。道家古老的生態美學智慧追求的是一種人與自然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審美境界。薇拉·凱瑟雖然生活在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時期,但是各種伴隨而來的現代危機使得凱瑟意識到人類只有遵循大自然的發展規律、回歸到自然的懷抱,才能解決人類的生存危機和人的異化問題。她的作品中表達了對于現代人生存狀態的關注及其對消費文化的生態批評,顯現出了深刻的生態意識,這些生態思想與傳統的道家學說有著很多驚人的契合之處。
1 “自然、無為”的生態實踐觀
《拓荒者》是凱瑟早期小說的代表作,女主人公亞歷山德拉以及艾佛和土地之間都形成了和諧統一的關系,反映了凱瑟對于人與土地之間關系的倫理思考和憧憬之情。在父親約翰·伯格森那里,人與土地形成的是主客體二元對立的關系,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唯有亞歷山德拉意識到人類只有熱愛土地、保護土地、并順應土地自身的發展規律,人與土地之間才能形成一種相互融合的關系。正如小說最后結尾所說的那樣:“多么幸運的田野!它終于敞開胸懷接受了像亞歷山德拉那樣的顆顆赤心,然后又把它們奉獻給人間——在金黃的小麥里,在沙沙作響的玉米里。”人類轉變成為“土地共同體”中平等而普通的成員,而不是土地的征服者。自然不具備主觀意圖,它對待人類的態度是友善抑或是粗暴都是在依照自己的規律而行,而這種自然規律是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的。在凱瑟的土地哲學觀中,拓荒者只有保持對土地的熱愛和尊重,與土地、自然形成和諧關系,才能永葆大自然原有的生機和美麗,大自然才會給人類以豐厚的回報。
以“道”為核心的道家思想主張天道無為,道法自然。“道”為本體,是產生萬物的過程,人類亦產生于這一過程,那么人類就應該將自然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自然、無為”作為道家生態美學智慧,在人與自然的關系這一層面上,要求人類順應自然的本來勢態,不妄為,自然自在地生活。老子這種“自然無為”的思想在莊子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莊子·天道》中提出了“以己養養鳥”和“以鳥養養鳥”兩種對待自然的不同態度,意指如果人類肆意妄為,違背萬物的自然本性和自然發展規律,必然導致萬物的毀滅。莊子在《至樂》篇中還說:“天無為以為清,地無為以為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得道者應該以天地為效法對象,以無為為止樂。人類應該以一種謙恭親和的態度對待自然,遵循自然法則。否則,自然生態的平衡與和諧就會遭到破壞。“自然無為”的最終目的是要人類以順應自然之道為宗旨,不可為了過分追求物質利益而過度開發自然資源,隨意破壞自然的發展規律。由此可見,薇拉·凱瑟對于人地關系的描寫蘊含了濃濃的道家“自然無為”的生態實踐思想。
2 “貴生、愛物”的生態平等觀
道家“道法自然”的這種基本理念奠定了道家生態平等觀的基礎。老子《道德經》第25 章言:“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道都是整體環境的一個構成部分,不分高低貴賤,享有同等地位。人和其它自然存在物都有各自的內在價值,任何事物都是平等的。老子還說:“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道德經》二十七章》)這便是“貴生愛物”的慈悲情懷。莊子則進一步提出“物無貴賤”的思想,認為從自然的常理來看,萬物是齊一的,本沒有貴賤的區別,人與物的平等便是其中一種體現。人應該尊重自然,與自然為友。相反,如果人類持有優越于萬物的這種偏見,就會想要奴役自然,會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和獲取私利而破壞自然,從而破壞事物的自然之性和自然狀態。“貴生、愛物”表達的中心主題是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統一,最終目的是敬畏和愛護自然萬物,保護生態環境。對于道家這種貴生愛物的思想,著名的生態倫理學創始人之一阿爾伯特·史懷澤懷著極為欣賞的態度說過:“我們樂于承認,與我們相比,在中國和印度思想中,人和動物的問題早就具有重要地位;而且,中國和印度的倫理學原則上確定了人對動物的義務和責任。”
凱瑟的作品中也多處體現出老莊的生態平等觀。比如在《啊,拓荒者!》和《我的安東尼婭》的這兩部小說中,凱瑟描寫的很多場景都是以動植物為唯一主角。這些動植物千姿百態:長草深處的啾啾蟲鳴,柔和的、永不疲倦的麥浪,天鵝絨似柔軟發光的暗紅色的天人菊,肅穆的田野,散發出香甜味道的松木等等。凱瑟使用自然文學描寫動植物的手法,對這些動植物形象進行全方位的、細致入微的刻畫,賦予了它們和人類共同的重要性。在凱瑟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出動物、植物和人類所形成的平等關系,他們共享自然,相互融合。
除了對于動植物的形象生動地刻畫,凱瑟的生態平等思想還體現在兩個典型人物身上。一個就是《啊,拓荒者!》中的瘋子艾佛。艾佛是一個典型的動物保護主義者和物種平等主義者,尊重并觀照周圍的一切生命,也不允許別人去傷害它們。他視自己為自然的一部分,居住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所有的行為方式都遵循著自然法則,同時還擔當了捍衛自然的角色。他屋前的池塘是野鳥的棲息地,他把它們都看作自己的伙伴,他說:“常常有許多奇怪的鳥到我這里來落腳,他們從很遠的地方來,給我做伴可好啦。我希望你們小伙子們從來不打野鳥,是吧?”另外一個人物就是麥麗。麥麗特別喜歡樹:“我喜歡樹木,因為我覺得它們比別的任何東西都能隨遇而安,必須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下去。我覺得這棵樹似乎知道我坐在這里所想的一切事。”麥麗與樹木之間形成了一種親密的伙伴關系,樹木似乎也有了生命,能感知麥麗所想的一切。凱瑟的這些描寫正是體現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平等關系,在對待自然萬物生命的態度上,薇拉·凱瑟與道家有著驚人的一致性。
3 “天人合一”的生態整體觀
“天”在古代人的概念里是具有多重精神屬性的。在老莊的概念中,“天”是事物自然而然的狀態,是沒有意志也不具備道德屬性的自然之天。莊子在《齊物論》中指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意指萬物和我們人類都擁有自然的共同本質屬性,所以就和人類合為一體。莊子是從事物共性和本源論的角度探討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即人與天的高度和諧統一。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追求的是超越現實的束縛,強調的是人回歸自然,與大自然“物我相融”的和諧境界。
薇拉·凱瑟在《啊,拓荒者!》中在描述亞歷山德拉和麥麗在一起的情景時寫道 “她們在強烈的陽光下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周圍樹葉織成的圖案像一張網;那瑞典女人是一片白色和金歡色;那機靈的棕色女郎在說說笑笑時,眼睛里點點黃色的閃光跳動著”。人和自然不同的色彩融合到一起,構成一幅美麗圖畫,此時很難說是人在自然中,還是自然在人心中。人與自然在經歷了文明與荒野的沖突和矛盾之后,最終走向了和諧,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小說《我的安東尼婭》中也有類似的場景描寫。經歷了重重磨難后的安東尼婭最終選擇回到大草原,與自然形成了和諧的生存關系,同時實現了自我,讓物我都呈現了更高境界的美,大草原也呈現出一種帶有人文氣息的自然美。凱瑟在其多部作品里都表達了同樣的信念:人類精神家園的最終歸屬是回歸自然的詩意棲居的生存狀態。由此可見,凱瑟對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圖景的描寫實則蘊含了道家萬物和諧共生、天人合一的生態美學思想。
4 結語
凱瑟和老莊雖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時代,但都是社會經歷巨大變革的時代。無論是戰爭還是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都使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遭到了嚴重破壞。隨之而來的是踐踏自然產生的嚴重后果,這也使得人們也都認識到熱愛、尊重自然、重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重要性,因此凱瑟和老莊產生相似的生態關注,他們的生態思想中有諸多契合之處也就不難理解。解讀凱瑟作品中所蘊含的道家生態思想,拓寬了凱瑟作品研究的向度;同時可以讓我們重溫中國傳統道家思想,喚起我們對生態文明建設、自然保護等這些永不過時的主題的關注,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