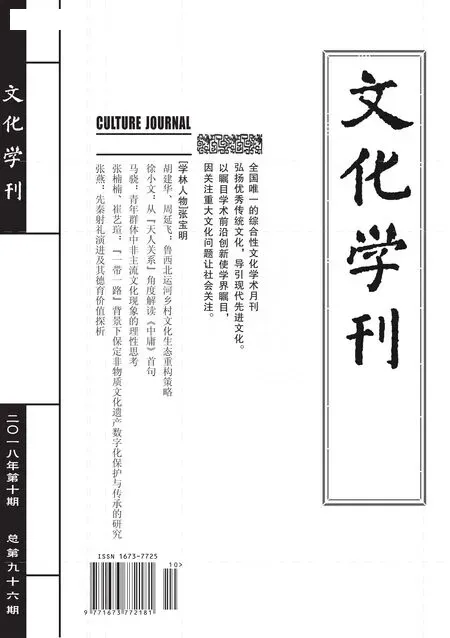國產歷史題材電視劇的情懷消費
蘇芊芊
(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近年來,諸多歷史素材被華麗改編重新搬上熒幕,如《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大軍師司馬懿Ⅱ之虎嘯龍吟》以及《那年花開月正圓》等。此類電視劇的普遍特色是“華麗視覺+基本史實+情懷消費”。情懷成為制片方打造的符合受眾期待的消費符碼,承載了商業價值及功用。
一、國產歷史題材電視劇的情懷書寫
縱觀《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大軍師司馬懿Ⅱ之虎嘯龍吟》《羋月傳》和《武媚娘傳奇》等情懷類國產歷史劇,不難發現其區別于《漢武大帝》《大明王朝1566》等正史劇的顯著特色:其一,劇中角色都由一線明星出演,輔之以華麗服飾、考究布景或明艷的濾鏡效果,傾力打造時尚品質與視覺美感;其二,重大事件符合史實,事件細節始末被制片方按需“戲說”演繹;其三,主要角色最初皆性格純良、避世無爭,因被情敵和政敵不斷施以致命性迫害,性格逐漸強大甚至“黑化”,最終對環境產生激烈反撲;其四,“情懷”特征強烈,劇中主要角色或清風朗月或率真執著,縱使人物性格最后轉向權謀強權,卻依然在私人感情或友情方面葆有赤子之心。
意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指引人們不斷進行當下與歷史之間的對話。作為以收視率為前提的歷史類電視劇,結合當下的社會情況和受眾期待對歷史做出許多情懷性戲說:關于愛情,劇中著力傳達出忠貞的、激烈的以及浪漫的現代情懷,司馬懿對張春華的專情,秦王對羋月的欣賞與體貼,武媚娘對唐太宗的崇拜無一不折射出現代人的情感期待;關于友情,司馬懿與候吉是主仆更是一生的摯友,司馬懿與諸葛亮是戰場上的敵人更是惺惺相惜、遙相感應的知己,武媚娘對徐慧、對高陽公主的友情是赤忱相待后遭背叛的由衷嘆息;關于理想、胸懷,曹操與曹丕對漢室的挾持與顛覆實出于結束戰亂解救蒼生黎民,羋月對義渠王的誘殺基于對秦國長遠利益的保護也是對已故秦王的承諾,出于為國革除弊政的考慮武則天扶植了寒門勢力含淚打壓了以長孫無忌為代表的士族門閥……
太多的情懷書寫呈現于當下的歷史題材電視劇中,沿著劇情的情懷導向深入思考下去,劇中涉及的重大歷史事件竟然都成了人物陷入兩難境地所做出的偶然性抉擇。于是,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必然性被悄然消解。歷史,在此類電視劇中成為披著“詩意”面紗的清純姑娘,在與現實泥淖的不斷周旋中終于蛻變為權力的女王。
二、消費語境下情懷的符碼價值
電視劇的創作集藝術、歷史、商業和政策導向等因素于一身,其本質是消費語境下用于大眾傳播的娛樂性作品,歷史題材電視劇也不例外。在消費社會語境下,文化生產的核心法則是商業標準,文化傳播實際上是面向受眾的消費行為。因此,受眾對于文化產品的需求和期待成為影響文化產品調性的主要因素。在我國,受眾需求對于電視節目的影響逐漸凸現,觀眾不再滿足于傳統模式下單一的節目輸出與被動觀看的傳播關系,即“觀眾消費電視文化產品,目的是獲得意義和快感。當目的達不到時,消費者就會提意見,甚至嚴厲批評。電視節目就會被停播,電視欄目就會改版”[1]。2011年前后,伴隨都市經濟的迅猛發展和人們日漸增長的現實壓力,“詩意”“理想”“自由”等情懷性詞匯開始在新媒體傳播平臺中病毒式擴散并贏得了都市受眾的認同,大量滿足受眾心理的打著良善牌、理想牌的“情懷類”歷史電視劇不斷涌現,并成為迎合受眾期待的消費符碼。
首先,劇中的情懷是對于消費經濟和速食文化的批判性符碼,契合了歷史劇中受眾對于經典文化主流地位的期待。自媒體時代,越來越多的節目以吸引粉絲為前提,以獵奇式、快餐式等面孔呈現,缺乏深入的價值空間與內涵。受眾在此類節目推廣初期大多愿意接受,但久而久之則會覺得其食之無味而產生厭倦心理。此時,情懷類歷史劇中的經典特質恰恰契合了受眾對文化內涵的需求,喚起了他們暫時斷裂的文化記憶,幫助他們尋回了內心平靜時的文化體驗。
其次,歷史劇中的情懷是彌補受眾現實缺失的代償符碼,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受眾現實生活中的精神與理想缺失。學者張頤武曾說“青年的事業發展‘完成不足’和生活要求‘實現不足’是永恒的主題”[2],點明了當下都市人在物質生活的重壓下很難顧全精神生活,更無從談及實現理想的現實狀況。在這種現實境況下,情懷類歷史劇對歷史人物進行了改造,使之具備當下受眾所期待的完美品質——執著于理想、忠貞于愛情、忠誠于友情、才華出眾而又能力強大。這類至善至美的人物形象顯然是大多數平凡受眾理想的人設形象,然而其在現實生活中卻絕不可能全部實現,從而承載了彌補受眾現實缺失的意義。
最后,劇中的情懷成為文化符碼以及品味符碼等,彰顯了其受眾的審美趣味。法國后現代文化理論家讓·布西亞德認為,在后現代消費語境下,商品尤其是文化商品的價值已不僅僅局限于其使用價值,其核心價值已經被符碼化,即其作為消費符號具有彰顯消費者社會地位和審美品味的意義。歷史劇中的情懷一方面彌補了觀眾的現實精神缺失,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其受眾的知識文化深度、格局胸懷廣度以及藝術欣賞素養,并將這部分觀眾與獵奇式、速食式節目的一貫觀眾區別開來。
三、歷史劇的當下情懷——從反消費到過度消費
作為消費語境下具有文化符碼價值的傳播形態,歷史劇中融入當下受眾的情懷期待本來無可厚非,其中所強調的“詩意”“理想”和“深情”等情懷與人間煙火也并無必然沖突。然而,當下情懷類歷史劇的突出問題是打著情懷的名義“將歷史打扮成一個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卻并沒有為這位姑娘塑造出多元的,能充分展現當下時代多樣性的立體豐滿形象。在受眾所期待的諸多情懷特質中,不同歷史劇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純良”“專情”“無爭”“胸懷”與“理想”。因為這些情懷特質最能引起當下受眾的共情,也最具有消費符碼價值。在這種情勢下,劇情的矛盾沖突則顯得千篇一律:純良遭遇迫害,專情難得始終,縷遭迫害致使角色最終強大……進而,絕大多數情懷類歷史劇難免陷入宮斗、權謀與情感競爭的窠臼。可以說,制片商打著情懷的旗號講歷史,卻未能講出一個具有情懷誠意的好故事。
消費語境以其強有力的滲透能力,將回憶、理想等本應該純粹的事物同質為功利性的消費符碼。當電視文本被置于消費語境下,其勢必會為了迎合受眾需求創造商業價值而對歷史素材進行改造,這種改造一方面追求華美的視覺效果,另一方面展現沖淡的人生境界。在許多情懷類歷史電視劇中,“情懷的懷舊傾向變成對傳統的消解,情懷的價值追求變成消費的符號化,情懷的智性訴求變成反智主義狂歡,這導致文化生產與消費過程中許多荒誕甚至怪誕的現象出現”[3]:濾鏡增強了視覺美感卻無法掩飾道具的粗鄙,女主人公精明睿智卻性格和善純良屢遭暗算而不自知,情懷和理想成為虛構世界中解釋重大歷史事件緣由的唯一的真。于是,受眾在這樣的電視文本中感受到了直接的情感宣泄,卻很難領悟到能與當下進行對話的歷史本該具備的人文內涵。
四、結語
誠然,講述歷史絕不是歷史題材電視劇的唯一目的。然而,在追逐商業利益的同時,契合當下精神、引領受眾審美也應是其作為文化傳播手段的責任之一。如何在電視文本中達到商業性、審美價值和社會責任的平衡統一,應該是當下歷史劇創作關注的核心問題。能以情懷作為切入點去對歷史進行重新演繹是歷史劇創新過程中的啟迪式思維,但絕不該將情懷局限于消費價值最大的幾種。歷史劇創作者們應該積極與當下現實進行對話,努力挖掘不同維度的人性表現,進而從不同視角反思歷史并對其進行演繹,完成充滿誠意的,具有真實情懷的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