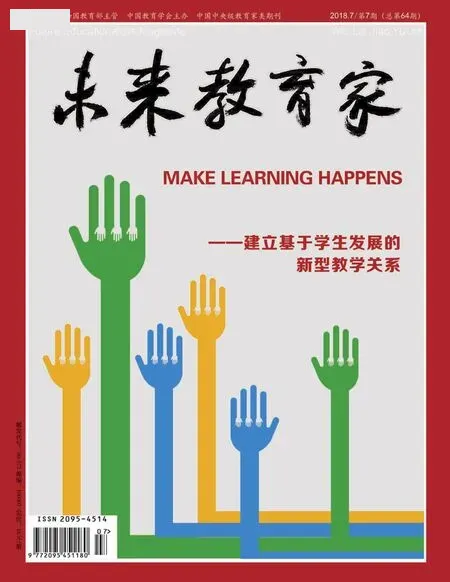讓教研回歸本位
——關于回歸教研本位的幾點思考
徐明 /江蘇省鎮江市教師發展中心主任
王飛/江蘇省鎮江市教師發展中心教師
教研活動是學校教育教學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本指向是學生的學業成績和素養提升,起點在于教師專業進步和教學改進,尤其在課堂教學與學習效率上的問題診斷和策略優化。然而,隨著教育理念、技術、方法的不斷更迭,一方面教研活動的基礎性、引領性地位日益凸顯;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斷出現了被動化、形式化、低效率的問題。究其緣由,也許不是我們的步子走慢了,很可能是路子走偏了。我們不能總是拼命往前趕,有時候也要回頭看看走過的路,回歸教研的本來面貌。
當前學校教研的幾個突出問題及其溯源
梳理多年來從事教科研工作的經歷,筆者發現,當前中小學教研活動主要存在三種偏向:
行政化偏向。可以稱其為“運動型教研”,指教育行政部門或學校為了某項大型活動,有時甚至為了招生宣傳,而進行的“一哄而上”式教研。比如,一些學校為了爭創**學校、**校園,以磨課為名開展教研,缺乏現實需要和證據分析,具有強烈的任務性、表演性,單純地為指令而教研。
概念化偏向。可以稱其為“碎片型教研”,指借助于某項課題研究、某個主題活動,而進行的“一錘子買賣”式教研。比如,一些學校借助“**課堂模式”“**課堂有效性”為名的課題研究,開展教研活動。但是對于建什么樣的“模”,怎樣才能“有效”,既沒有長遠的計劃,也沒有短期的目標,選擇的學科更不固定,像玻璃碎片一樣顯得雜亂,單純地為活動而教研。
時尚化偏向。可以稱其為“替代型教研”,指以寬泛的課程建設、新技術應用替代課程內容和學科知識,而進行的“泛泛而談”式教研。比如,當下一些學校熱衷于MOOC、翻轉課堂等“舶來品”,開展一些以展示新技術為內容的教研活動。不是說這些新技術不重要,但問題是僅僅局限于對新技術本身的研討,卻忽視了教學方法和技巧的研磨,更缺乏對師生行為和心理的關注,單純地為展示而教研,這種教研實際意義又有多大?
無論哪種偏向,最終都指向兩個具體問題:在客觀效果上,因為充斥著非學科性、學術性目的,目標不明,指向不清,因而造成表面上熱熱鬧鬧,實質上虛假繁榮、效益低下。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教師教學基本功的下降。特別是教師課堂講解力下降,講不清知識點之間的關聯;教師作業的精準力下降,習慣于網上抄題,不考慮學生學習體驗;教師試卷的命題力下降,甚至故弄玄虛,出一些偏難怪的、超出學生知識能力水平的題目,更有甚者還將廣告用詞引入試題,缺乏嚴謹。比如,某地某小學竟然出過這樣一道怪題:“鳥字的點,表示眼睛。”問:卵字中間的點代表什么?州字中間的點代表什么?滅字中間的橫代表什么?這樣的題目究竟有什么意義?在主觀感受上,因為缺乏進行教研行為的內生動力,教師只是把教研當作一件被動的、額外的、迫不得已的事,甚至有些不勝其煩、不堪其累。又因為不能把教研真正融合到自己的教育教學中去,教師也就無法領略教研工作的“實”“巧”“美”,往往適得其反、事與愿違。
這些偏向、問題的產生,是日積月累的一個過程,也是各種因素相互疊加的結果,從根本上必須反思其背后的思維邏輯特征。
功利性思維。教研的出發點是效率與技能,決定其成敗的標準只能是學習規律、認知規律、學科邏輯,既需要坐“冷板凳”的態度,更需要坐“冷板凳”的堅持。但是,在現實中,一些學校是為了創牌子、追求轟動效應;一些教師是為了評優評選、職稱晉升、績效考核。短視的教研目光直接導致無論是組織者還是參與者,都缺乏對教研本質全面而準確的認知,忽視教研活動本身具有的解釋現象、預測趨勢和改進工作功能的發揮。只求效應,不求實際效果。
營銷型思維。好的教研會培育人,促進學校發展,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一些學校往往反其道而行,只是為了“包裝”人,“包裝”學校。開展所謂的教研活動,經常是挑選幾個最優秀的教師,公開炫技、作秀,結果是少數人演,多數人看,重展示而輕應用。而對于大多數中小學教師而言,教研活動主要還是“應用性研究”,研究方法主要還是“行動研究法”。沒有大多數人的參與,沒有日常教育教學中的應用,教研也就失去了價值。
簡單化思維。教研活動原本是一個系統過程,需要有問題的提出、解決方案的演示、經驗的總結、改造性實踐等一系列過程,講究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實踐。然而在現實中,一些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想“畢其功于一役”,能夠找到促進教師發展、提升教育質量的“速成法”“速效藥”,希望通過一兩次的專家指點迷津,就能讓教師茅塞頓開、恍然大悟。
這三種思維充分說明,我們對教研活動的規律研究還是不夠,對質量提升的規律研究還是不夠,對人的成長規律研究還是不夠,操之過急、拔苗助長,必須正本清源,重新定位。
回歸教研本位的幾個追問
有好教研,就會有好教師。有好教師,就會有好教育。那么,什么才是好教研?教研活動的本位究竟在哪里?尤其對于一線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而言,我們首先要弄清楚幾個基本問題。哪怕這些問題在一些人眼里已經是司空見慣,沒有新意。
什么是教研?顧名思義,就是研究教與學的活動及其相關保障系統。也就是說,一項教研活動的開展至少要具備兩個基本要素:即活動、保障。從活動來看,既包括教師之間最基本的人際交往活動,也包括教師圍繞教研主題、問題而進行的提議、質疑、爭執等思維活動,還包括教師上課、記錄、交流、改進等實踐活動。從保障來看,涉及的方面就更多了。比如制度保障、技術保障、場地保障、經費保障以及和諧的人際關系保障,等等。
誰來做教研?教研活動參與主體通常有三類:一類是實踐性主體,即教師、教研組長、教學主任等;一類是支持性主體,也就是專家、學者等。還有一類是管理服務性主體,包括校長、教科研部門、教育行政部門等。有些情況下,也有家長、社會的參與,比如以家校合作為主題的教研活動。總的來說,管理服務性主體提供條件、保障,支持性主體提供理念、智慧,實踐性主體提供操作。
在哪里教研?教研活動的水平和層次,與其存在的環境是息息相關的。這事實上是一個體系的問題。宏觀層面,一個完整的教研體系包括國家、省、市、縣、學校五級教研體系,在哪里教研,就屬于哪個層級。但是,對于大多數教師而言,參加國家、省一級的教研,機會是不常有的。一般常見的教研活動場所主要還是集中在課堂、學校、區域(縣或市)。其中最為根本的還是校本教研、同伴教研甚至是個人教研。當然,隨著信息化時代的發展,網絡教研也是方興未艾。因而不同的教研與平臺決定不同的方式方法,我們既反對以大教研代替小教研,也反對以小教研代替大教研。
教研發展的基本走向是什么?這個可以從不同角度去認識。
就目標而言,正在從課堂質量轉向人的發展質量,但基礎始終都是質量。不管是提高分數,還是提升素養,我們的主陣地始終都是課堂,都必須要在日常的教育教學中潛移默化。從這個意義上講,關注人的發展,最基本的還是在課堂。比如,面對新一輪課程改革和高考改革,如何在走班制背景下關注學生的思想品德、心理健康,特別是關注學生作為一個完整人的全面發展,正在成為每一位教師而不僅僅是班主任的教育責任。有些地方和學校,甚至還催生出一些全新的教育角色,比如生涯規劃師、教育顧問,等等。
就主體而言,正在從單一學科活動轉向綜合拓展活動。根據專家測算,人類知識每三年就增長一倍,時代發展越來越呈現整體化、綜合化的趨勢,學科知識越來越呈現融合滲透。這就決定當前的教研活動必須向更廣、更深、更多的知識領域和層次邁進,通過不斷更新知識結構,樹立獨特的視角、界域、思維。過去,我們只需要研究基于某一個學科或學段的教研,現在則越來越需要研究基于項目實施的跨學科、跨學段的教研。比如,針對美育研究,音樂、美術教師應該怎么辦?語文、英語等其他學科怎么滲透?小學階段怎么教學?初中、高中階段又應該教會學生什么?這些研究都要系統、銜接。
就現實條件而言,傳統的教研尚未落實,又遭遇到新技術、新背景的挑戰。一方面,在現行的學校管理體系中,年級組往往比教研組、備課組更受重視,也更強勢,傳統教研功能趨于弱化。另一方面,以信息技術為載體的線上教研,從教師角度看,缺乏真實情境,忽視主體體驗,不能滿足教師真實需求,往往是“一頭熱、一頭冷”。
問題決定走向,問題就是走向。立足當下,我們的教研既要前瞻,又要回歸,但是首先要做好的還是回歸。只有打好基礎,才能面向未來。只有找準現實定位,才能向著理想狀態前行。
“本位”教研的幾個層面
教研活動有著自身規律,不能只做加法不做減法,需要處理好各方關系,需要從各自的本位出發,研究教研,服務教研。我們將之稱為本位教研,即區域本位、學校本位和教師本位。
對于區域本位:就是把方向、抓規范。所謂把方向,就是要對學科發展、教育發展乃至社會發展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要對本區域教研工作把好關、定好向。比如,上海市教研室就提出從三大功能走向六大中心,即在原有“研究、指導、服務”的基本職能定位基礎上,進一步建成“課程發展中心、教學研究中心、資源建設中心、質量監測中心、數據研究中心”。所謂抓規范,就是要建章立制,搭建平臺,讓教研成為常態。比如,鎮江市教師發展中心圍繞促進農村學校、薄弱學校教研水平提升,探索建立了“三邊學校聯盟”(即山邊、田邊、水邊三類學校),通過簽訂意向書、確定學科領銜學校等方式,建立區域合作的長效機制。
對于學校本位:學校是各級教研活動的落腳點。一個成功的學校教研活動,不是領導和同行之間相互檢查、監督的手段,而是一種群體協作的行為,是一種共同努力、共同進步的學校文化,就是要明目標、抓基礎。所謂明目標,就是要明確學校教研的目標和方向,整體規劃和設計學校、學科、教師各個層面的研究與組織機構,找到適合的教研主題和教研形態,從而提升教研效益與質量。比如,如何在教育信息化形勢下開展教研?如何在新課程新高考背景下開展教研?等等。所謂抓基礎,就是要腳踏實地,練好基本功,上好家常課。比如,廣州市天河區很多學校都以“講學稿”為抓手,努力提高教師備考質量和課堂教學水平。
對于教師本位:教師是組成教研活動的最基本單位,主要任務就是要揚個性、抓操作。所謂抓操作、揚個性,就是要樹立個性鮮明、獨樹一幟的教學風格,就是要有屬于教師自己的教學方法、教學模式,進而形成個性化的教學文化。就是要從最基本的教學規范抓起,從解決最基本的問題開始,讓教師明白“教什么”“怎么教”,讓學生懂得“學什么”“怎么學”。 比如,北京市昌平區南口中學古永啟老師,以化學實驗教學和實驗技術為突破口,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自主創新研究式教研。
“本位”教研的幾個支撐
教研活動不僅是一種行為方式,而且是一種文化價值,不僅要從教育學,而且要從管理學、社會學的角度去全方位認識。開展“本位”教研,必須具備三個方面的條件支撐。
理念支撐。無論是教育行政部門、學校,還是教師本人,都要厘清教育研究與教育改革的關系,切實把教研工作轉變為自己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不斷打破慣性思維、經驗主義,不斷掌握新的知識技能和行為方式,努力營造有利于教師學習、研究、合作的教研氛圍。比如,上海市圍繞打造專業性、學術性相結合的市、區兩級教研共同體,引進美國“常青藤聯盟”理念,連續八年舉辦了“常青藤”論壇。上海市教委高中部湯青主任也以“引導結構化”的理念開展單元教學教研,努力推動教師從經驗型向專家型轉變。
保障支撐。在制度層面上,通過輪崗試教、專題研討等制度確立教師合作的行為準則,用制度來保障對教師參加教研的精神激勵和物質獎勵。在物質層面上,積極加大必要的硬件設施和軟件設備的投入,對于教師參與教研給予充分的經費支持。某種程度上,一所學校在教研上投入了多少,這不僅是衡量校長是否真正重視教研工作的“試金石”,而且也是教研能否轉化為學校發展“生產力”的重要保證。在管理層面上,積極發揮教研部門的管理職能,捋順關系,加強協作,讓教師在互幫互學中形成和諧的人際關系。比如,蘇州市教研室專門將教研類帶頭人納入學科帶頭人評審,進一步促進一些學習型優秀教師成長為研究者。蘇州吳中區對教研實施補貼政策。
實踐支撐。教師成為研究者是新時代對教師提出的新要求,但是教師研究和專業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衡量標準是不一樣的,必須要充分認識教師教研活動的特點,源于實踐、用于實踐。在教研的目的上,側重于對教師所進行的具體實踐工作的理解、改進與提高,而不是一般情況下的普遍性認識和理論性表達。在教研的形式上,則更多以批判性反思、行動研究以及以課為單位的合作研究。比如,南通市的教研室,每年都利用暑假或長假組織各地各校的骨干教師、優秀教研員學習、研究考試說明、課程標準,然后分頭編寫各類教師、學生用的參考、教輔資料,始終以服務教學作為教研活動的方向和衡量標準。
綜上所述,讓教研回歸本位,既是教育管理者的責任,也是教育研究者的使命,更是廣大教師的職業追求。方向正確了,對于教育發展、學校發展、教師發展、教研工作都會煥發出活力和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