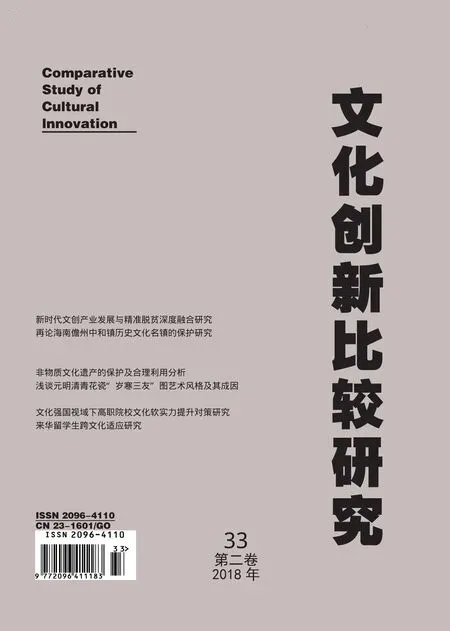環境美學視角下的儒家書院
岳 芬
(常州工學院,江蘇常州 213022)
儒家書院美學是尚未受到環境美學重視的中國傳統美學領域,書院對自然景觀的處置、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表達不僅關涉到中國山水美學精神,還融合了中國的傳統倫理思想和社會價值觀。
從環境美學的角度來看,儒家書院在位置的選擇、內部景觀的布置等方面同時兼顧人的教化與自然環境的保護。強調人的社會倫理職責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其基礎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解,因此,人的社會倫理職責中必定包含人對自然的責任。
1
在社會與自然的關系方面,儒家書院體現人與自然相互平等的主張,人的生存權與自然權利在書院中都得到實現。“當自然與治學兩種觀念相結合,書院作為學習處所與風景作為自然世界這種臆想的分野便在書院的精神生活中融合了”[1]。書院即是一個縮小的生態系統,它將自然引入人造環境中,盡可能地保持了自然的原貌。
精心布置的景觀也為人的棲息和靈魂的提升創造了條件,“當’自我’與生動而遠播的自然世界相處時,就會在與風景的積極互動中成長,于是山水間漫無目的的徘徊是對齋舍中靜坐學習的補益”[2]。人與自然物的互動促進了學識的增長,在潛移默化之間影響了學習者的品行。與18世紀現代哲學思潮不同,書院在倫理教化時并沒有將自然排斥在外,而是借助自然來豐富教育的內容。“書院的花園是沉思的花園。它為個人或團體的研學提供了靜止與漫步共存、自我修養與追憶圣賢共存的視界”[3]。書院嘗試著將人與自然結合起來,較之海德格爾式的詩意棲居,儒家書院在詩意之外還要求學習者領悟社會職責,其中也包括人對環境的職責。
儒家書院可以被看作另一種獨特的園林形式,它不同于江南私家園林,因為在自然景觀之外,它還被賦予厚重的思想境界和教化的功能。在中國傳統社會,人在書院中接受最初的教化,離開書院后,他們便將書院中的理念應用于社會交流之中。書院的自然觀因此得到傳播,最終形成一種社會責任。儒家對社會責任的重視反映在書院的每一個細節,模仿自然是為了回歸自然,而非超越自然。書院不僅是一個教育的系統,更是一個小型的生態系統,象征儒家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完美構想。
2
書院實現了自然與人的統一,人的德行與自然景觀實現了完美的呈現。“書院風景與園林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儒家關于自然的經典理念——‘比德’”[4]。也有人認為,儒家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是符合生態思想的。
儒學是以人為中心的傳統,它關心人被賦予的特殊地位。但是,儒學能關注人類與宇宙的內在關聯。從這種角度來說,它更具有天人和諧宇宙觀的特征。學習、修身以及人際關系構成了儒學的根基。但是,當人性得以實現時,“仁”作為人性之核心則成為了宇宙自身的中心。因此,成仁就是要超越人類自身,而這也是儒家生態學的根源所在。值得重視的一點是,儒學并不要求我們在人性尚未完滿實現之前便超越人性,而是說隨著人性的擴充它會包容所有生命。最終,儒家傳統中的“仁”就是生態學,因為用張載的話來說,“仁”就是“民胞物與”。[5]
儒家書院是對儒家修身理想的體現,在書院中,人是教化的中心又是自然的一部分,書院的每一個細節幾乎都能夠反映儒家的社會倫理精神和基本的教育理念:首先,書院體現了儒家尚禮的原則,作為儒家的核心理想,如何安排書院內的自然物都要遵照禮制的要求。其次,儒家天人合一的理想在書院中也得到表達。書院實現了自然與人的完美融合,自然為學習者提供了絕好的空間,書院對自然的安排可以看作是一種“道法自然的方式”[6],學習者時刻與自然之間保持相互溝通的狀態。最后,書院努力實現自然對人的包容,而不是人類對自然物的控制。人工建筑巧妙地掩映在自然物中,“在書院的實體存在中,無論是屋舍、園林還是風景,都不可以鼓勵地被理解”[7],很難具體區分哪里是自然、哪里是人類社會。
雖然書院是一種人工自然,它同原生自然之間有一定的區別,但是書院盡可能地保留了自然的原貌,而且儒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道家等多家觀念的影響,形成了一種綜合的宇宙觀。從景觀全貌來看,儒家書院秉承了中國傳統山水畫的特征,人和建筑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樹木和山石之間,自然反而成為書院的主角。
3
從儒家書院中蘊含的自然哲學思想來看,環境美學對儒家書院獨具特色的自然審美觀念的吸收,有助于環境美學與生態美學思想的交融。從跨文化的角度來看,環境美學走向生態美學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被動的文化交融模式,環境問題倒逼現代文明對自身進行檢討,并且主動吸收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榮格等心理學家很早便指出現代西方文明主導下的人類的精神問題,并且希望在其他文化智慧中找尋出路:
從精神層面來說,西方世界處于岌岌可危的境況當中。我們越是蒙蔽自己的雙眼,以為自己擁有美好的靈魂,用這種錯誤觀點來掩飾殘酷的事實,那么西方世界所面臨的危險就更大。西方人給自己點燃了一支香片,生活在香片散發的陣陣濃煙當中,好讓煙霧把自己的臉罩住,自己看不到。但是,我們會給其他膚色的人留下怎樣的印象?中國和印度會怎樣看待我們?我們在黑人當中會激起怎樣的情感?至于所有那些被我們奪走了土地、被我們用朗姆酒和性病滅絕的人,他們又會怎樣看待我們?[8]
自20世紀初,精神危機顯然要比環境問題引起更多的關注,但是,它并沒有像環境問題那樣引起廣泛注意,直到20世紀中后期,精神危機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加劇再次爆發,而且,這次的精神危機不僅牽涉到文化沖突與認同感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人與整個自然的矛盾。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矛盾在人與自然的對立面前顯得微不足道,環境問題促使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文化不得不重新審視東方智慧,以期獲得更多智慧來解決生態危機。
在文化上,技術也促使西方文化超越東方文化占據統治地位,西方現代技術為人類探索自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卻在人與自然之間設置了障礙,正如榮格所看到的那樣,“我們用技術優勢把東方的物質世界攪得天翻地覆,但與此同時,東方也在以其優越的心理成就讓我們的精神世界陷入混亂之中。我們根本不會想到,當我們在外部世界壓倒東方的同時,東方竟然有可能在內心世界緊緊地控制我們”[9]。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之間的差異,也能夠反映環境美學與生態美學之間的區別。相對于環境美學而言,生態美學堅持以更為全面的視角看待人與自然的問題,并且更重視不同文化和思想之間的關聯。因此,生態美學更多地吸收了東方傳統思想以充實其自然觀念。
在生態批評角度而言,吸收東方思想之后的生態審美觀念也更具審美的張力。如王諾所說,生態批評的主要任務是“以生態思想為指導的文學外部研究,從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個角度探討文學的思想文化蘊涵”、“以生態美學為指導的文學內部研究,探討文學獨特的生態審美及其藝術表現”[10]。雖然這一劃分仍然值得商榷,但是,將生態美學作為生態批評的任務之一,體現了對文學研究的深度思考。
儒家書院剛好為此提供了理論靈感和精神動力,書院的環境讓身處其中的學習者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功利主義的目的,追比圣賢的愿望同天人合一的理想凝結在一起,使得功名利祿這類從屬于社會精神生態范疇的精神問題得到緩解,甚至被遺忘于浩如煙海的卷帙中。書院巧妙地處理了知識德行與現實功利的矛盾,對于改天換地、征服自然這類現代人的知識觀也具有借鑒的作用。
小結:從觀念的層次來說,環境美學是對環境問題的初步反思,對自然美的認知為保護環境提供了最初的倫理依據,生態美學則進一步探討造成環境問題的根源,在審美的基礎上,生態美學進而將自然的權利等倫理問題置于自然審美之上。在生態美學的研究視域下,環境問題不僅指生態環境的破壞,同時也包含了對人類精神困境的反思。
儒家書院是對儒學天、人(自然)哲學和社會理想的呈現,它將流動的思想轉化為固定的審美形態。場所的意義突破了空間的限制,精神流動起來,人與環境的融合改變了接受知識的方式,儒家學子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僅可以更透徹地領悟圣賢之道,還可以更為直觀地感受自然精神和哲學精神的交融。部分書院或同一書院的部分景觀還融匯了道家、甚至佛家的旨趣,儒釋道的多元思想將書院從單純的修身場所提升為更高層次的精神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