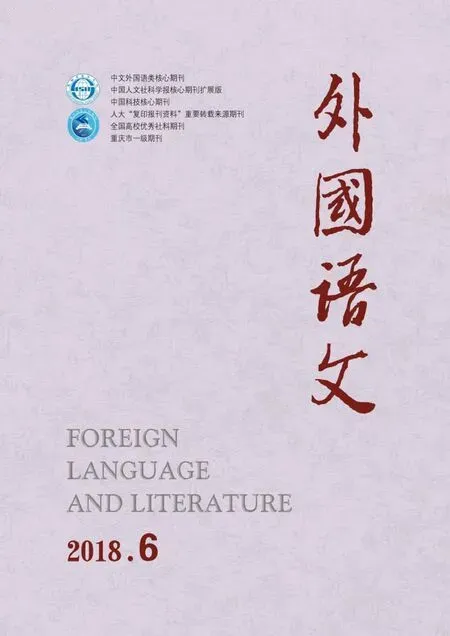比較文學何去何從
——蘇珊·巴斯奈特教授訪談錄
張 叉 蘇珊·巴斯奈特
(1.四川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1;2.華威大學 現代語言學院,英國 西米德蘭郡考文垂市 CV4 7AL)
張叉:您對于比較文學的看法是如何幾經轉變的?
蘇珊·巴斯奈特:我常給新晉博士研究生的建議是,研究是一個有機過程,它是成長和發展的。學生帶著一定的想法而來,但是如果在第一年之末他們的這些想法都還沒有出現改變的話,那么他們就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到第二年,不少學生便陷入困惑,而這也是成長的必經階段,因為改變總是令人困惑的,有時還會讓人感到痛苦。然而,若是沒有改變,便不會有任何成長,也不會有任何進步。
我相信,比較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因為人類總是傾向于將甲同乙進行對比。只要學習文學,模式和關聯便隨之產生。由于在不同的國家接受了教育,學習了不同的語言、文學與歷史,所以文學比較便不可避免了。
由于我對比較文學領域如何在19世紀從法國興起和發展以及對這一領域為何出現了很多爭議懷有興趣,所以撰寫了一部《比較文學批評導論》(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1993)。我在1970年代成為華威大學講師的時候,發現在比較文學中存在著一些荒唐的規則,比如,禁止對用同種語言寫成的文本進行比較,而不顧這些文本分屬于不同的文化。這樣,英國作家和美國作家就視為不宜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原因是比較應該跨越兩種不同的語言。與此同時,在美國,比較文學似乎意味著任何東西都可以拿來進行比較——畫作與詩歌、歌劇與小說,這好像也顯得離奇古怪。
我在那部書中追溯了比較文學的兩股分流——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發現二者皆有所欠缺。我注意到,許多學者對這個學科的“危機”加以抱怨,這個領域也沒有多少具有任何價值的作品得以發表。對此,我引入了兩個新的想法:(1)僅僅正在開始產生影響的后殖民主義應該被視為比較文學的一部分;(2)同奄奄一息的比較文學相比,正在興起的翻譯研究更加振奮人心,在潛力方面更加具有價值。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翻譯研究十分關注重寫文學史,而這一工作似乎已經遭到比較文學的拋棄。
1993年是久遠的過去,自那以后,出現了很多變化。翻譯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受人尊敬且多樣化的領域。多虧了霍恩·蘇源熙(Haun Saussy)、西奧·德漢(Theo D’Haen)、塞薩·多明戈斯(Cesar Dominguez)、哈里什·特里維迪(Harish Trivedi)、貝拉·布羅德斯基(Bella Brodzki)、愛米麗·阿普特(Emily Apter)和包括像中國學者王寧在內的全世界其他許多學者,比較文學已經重新煥發出生機。不過,在我看來,比較文學是因為受到翻譯研究和后殖民主義研究的雙重影響才得以復興的。如今,比較文學的問題是它同正在擴展的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問題,翻譯研究的影響也曾有過這樣的經歷。
然而,我相信比較文學或者翻譯研究就本身的資格而言并不是學科,它們只是走近文學的方法。試圖爭論這些龐大而松散的研究領域是否是不同尋常的學科純粹是毫無意義的時間浪費,這是因為它們非常多樣化,而且是由如語言學、文學研究、歷史、政治、電影、戲劇等其他學科組合成的一個綜合體中派生出來的。我認為這并不是問題。我們很可能要問,記憶研究——另一個龐大的領域——是否是一門學科,而我還是要回答說不是,因為記憶研究也是依靠藝術、社會科學和醫藥科學一系列既有學科而來的。至于研究領域,我喜歡這樣的觀點,那就是,研究領域不能納入學科的匣子之中。這是21世紀了,不是19世紀。
張叉:何為文化轉向?
蘇珊·巴斯奈特:文化轉向是我與安德烈·列斐伏爾(Andre Lefevere)于20世紀90年代早期共同創建的。翻譯研究本身是以小規模的方式創建起來的,而我們感到,對產生和接收翻譯的文化維度加以強調是極其重要的。我們大力主張,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文化因素上,比如編輯、出版商、贊助商、審查方等的角色之類的因素,這些文化因素在翻譯的產生之中發揮著作用,同時,也在1980年代因吉蒂昂·圖瑞(Gideon Toury)的著作而備受關注的美學規則的改變之中發揮著作用。文學轉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并得以進一步用作搭建通向后殖民主義的橋梁,它指明了后殖民翻譯研究、翻譯與性別研究的前進道路。最近以來,我們的工作已經通過被稱為翻譯研究中的“社會學轉向”(the sociological turn)而得以向前推進。我們還拓寬了研究的范圍,提出諸如編輯、編選、文藝批評與理論、評論與歷史學之類的其他方面的實踐是同翻譯并駕齊驅的,它們作為文學史上的塑造力量之一,也應該看作是具有重要性的。
文學轉向所做的事情是鞏固伊塔馬爾·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早在1978年提出的觀點。伊塔馬爾·埃文-佐哈的觀點認為,文學史研究必須要考慮翻譯所發揮的作用,我們必須要思考,為什么在它們發展的不同階段文化都多多少少地做出一些詮釋。
同樣重要的是要記住,我們最初對翻譯研究的創建是在新思潮出現于人文學科并挑戰權威觀點之際懷著極大激動的心情完成的。與翻譯研究同時興起的首先是文化研究、媒體研究,然后是女性和性別研究,接著是后殖民研究,所有這些研究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抗議而產生的,它的目的是挑戰業已建立的等級體系。
后來的翻譯研究人員,這里要特別提一提的是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邁克爾·克羅寧(Michael Cronin)、埃德溫·根茨勒(Edwin Gentzler)、謝麗·西蒙(Sherry Simon)和安東尼·皮姆(Anthony Pym)等最負盛名的五人,他們繼續挑戰業已確立的翻譯觀念。韋努蒂強調應該使翻譯變得更加有跡可循,根茨勒提出有關權力關系的重要問題,克羅寧同樣質疑多數民族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系,皮姆提出權力與倫理標準的問題,西蒙將注意力放到翻譯史中的性別偏見,且最近以來一直在構建關于多語種城市的觀點。我自豪地說,韋努蒂、根茨勒、西蒙和克羅寧的理論全部都收入我同已故學者安德烈·勒菲弗爾合著的系列叢書中出版了。
張叉:您為何不看好影響研究?
蘇珊·巴斯奈特:我的本科畢業論文是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對伊塔洛·斯維沃(Italo Svevo)的影響研究。我讀得越多,這種影響似乎就越微弱。相反,我發現斯維沃對喬伊斯有所影響,盡管喬伊斯本人對此表示否認。因此我面臨的困難是:尤其是在據認為受到了影響的作家在他與其他作家的關系問題上撒謊的時候,怎樣證明影響的存在?
我所知道的情況是,作家的聲明并不能相信,它們有時候是觀點的表達,有時候則是有意的欺騙。影響是無法證明的,剩下的是洞悉相似之處的讀者的看法了。當然,更好的做法是,不要浪費時間盡力去證明無法證明的事情,而要將關注點放到讀者的作用上,讀者在每一次重新進行的閱讀中都有效地“創造”了一個文本。
張叉:您如何回應別人對您歐洲中心主義的指責?
蘇珊·巴斯奈特:在“歐洲中心”(Eurocentric)一詞出現以前,我撰寫了本《翻譯研究》(TranslationStudies)。著作組的成員來自以色列(埃文佐哈和圖里)、比利時(勒菲弗爾和蘭伯特)、斯洛伐克(波波維奇)和荷蘭/美國(詹姆斯·霍姆斯)。霍姆斯具有印度尼西亞語言的專業知識,如若不然,我們的語言就全部屬于歐洲范疇了。當然,我們的重點在歐洲,否則,如何才能夠為它提供我們的知識庫(knowledge base)呢?歐洲中心主義是在20世紀80年代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術語用來譴責沒有充分考慮非歐洲文化的研究的,所以它成了早期后殖民主義思想中的一個關鍵的術語。然而,隨著后殖民研究和翻譯研究的擴大和發展,這個術語的力量已經失色不少了。后殖民模式無法在每一個地方都能夠得以有效的使用。比如,巴西的學者對后現代主義理論更感興趣,巴西的翻譯研究催生了食人主義理論(the cannibalistic theory),這一理論有效地推翻了歐洲中心主義。后殖民主義對經歷后共產主義的前東歐的文化也不十分管用,且對未經歷后殖民主義階段的中國、朝鮮或者日本的學者來說,它似乎也并不非常管用。
我同印度學者哈里什·特里維迪(Harish Trivedi)合著的《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與實踐》(PostcolonialTranslation:TheoryandPractice,1999)一書收錄了世界各地學者的文章,顯而易見,這些文章的研究視角有著很大的不同。當然,這也并不是說,后殖民主義不是一個極具價值的研究領域,而只是說,過去25年以來,其重點一直在變化。現在,創傷研究(Trauma studies)是一個大的領域,有大量的作品涉及歐洲的后大屠殺記憶(post-Holocaust memory)。此外,正如我所堅信的這樣,所有的社會政治事件都會帶來重大的認識論后果,這在今天已經成為歐洲學者處理歐洲問題的關鍵,比如,大規模移民的影響,這導致了一些極具吸引力的文學的出現,這些文學是由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創作的,具有隨之而來的語言學的意蘊。此外,歐洲的民族主義已經抬頭,這似乎同全球化的趨勢是相抵觸的。比如,在英國,我們已經看到1999年以來出現的蘇格蘭議會的建立和全民獨立公投以及威爾士國民議會的建立。對比較文學學者而言,這里要注意的一點是雙語教育在這兩個地區的興起及其隨之而來的對于文學的影響。可以說,北愛爾蘭也是如此,盡管這里沒有像威爾士和蘇格蘭那樣的雙語政策,但是許多作家既用英語也用愛爾蘭語進行創作。
因此,雖然我仍然堅持后殖民主義思想的理想與倫理標準,但是我同時也意識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區域需要更深入地考察其各自本土的語境。
張叉:比較文學將何去何從?
蘇珊·巴斯奈特:按以上所說,我相信,由于比較文學為在文化之間搭建橋梁提供了手段,所以它越來越重要了。它同時也給我們所有人提供了帶著不同的觀點來從事研究的機會。例如,我在最近作關于庫切(Coetzee)、布扎第(Buzzati)與卡瓦菲(Cavafy)的演講的時候,引用了王敬慧發表在一期刊物中的文章,文章在庫切在中國的接受分析方面顯示出了令人驚嘆的洞察力。發表這篇文章的這期刊物由凱拉什·巴拉爾(Kailash Baral)編輯,2008年在德里出版。王敬慧所討論的許多問題,我壓根不曾意識到。
在翻譯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印度比較文學越來越多地關注泛印度(pan-India),即討論印度多種語言與次大陸諸文學之間的相互關系。這標志著關于印度與西方關系的無休止的爭論的一個階段性的變化,這雖然還在持續,但是已經不再占主導地位了。歐洲的情況與此類似,殖民主義的遺產必須予以適當的考慮,而不管是物質上還是文化上,比較文化都需要涉及大陸正在經歷的巨大變化,這一點是重要的。
例如,我驚奇地注意到,最近蘇格蘭北部的考古發現正在改變我們對新石器時代橫跨歐洲民族的早期運動的認識,這是對我們所有業已確立的假設的挑戰。對于中國比較文學,肯定也同樣適用。一方面,中國與西方關系和中國與鄰國關系是一個極具深入調查的價值的領域,但是我們希望,中國比較文學也要涉及中國國內的多種語言與傳統。
在有關失語癥(aphasia)的論辯中,我同意中國有發展自己的文學理論之必要。我也留意到印度學者甘尼許·德維(Ganesh Devy),他在作品中已經討論了印度語境下的雙重失語癥——一是在英國文化沖擊下對印度傳統的遺忘,二是對英-印時代的嘗試與遺忘。顯然,中國已經經歷過一系列非凡的歷史變遷,我們僅僅需要思考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重要性,思考文化大革命與改革開放對西方的影響——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不過六七十年的時間內而已。不過, 中國有豐富的文論史,這可以追溯到我們西方人還處于僅略強于野蠻人狀態的時期。另外,正如我所理解的,中國對實證主義沒有我們自18世紀以來一直所保持的那種癡迷。
這正是我們必須轉而發展的以世界文學為世人所知的領域,它已經在一些理論家的手里得以轉化了,比如,在此領域提供了頗具法國特色的視角的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更多地關注于散文而非詩歌與戲劇的佛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以及大衛·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如我所見,今天正在世界文學領域發生的事情是我們關于翻譯研究發明時所設定的延伸:探尋文本如何跨越文化而運動,理解那個運動中的一些復雜的美學和社會政治意蘊,審視文本實踐如何在不同規范、不同傳統、不同時間中進行。
簡而言之,上下文之內的文本細讀同注意語言的和文化的限制和差異相結合,也需要把通過時間的運動納入考慮之中。
在我看來,任何形式的文學研究不僅必須包含對文本如何發揮作用進行考察,它差不多像一臺機器,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它也必須包含對文本創作的歷史條件進行考察,同樣至關重要的是,它還必須包含對文本的接受與文本的讀者作用進行考察。
張叉:您作為世界知名的學者,希望給比較文學學者提出什么建議?
蘇珊·巴斯奈特:在盡可能廣泛地進行閱讀方面永遠不要止步,但是要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作為比較文學學者,注定總會感到自己過于無知。我已經接受這個現實,自己永遠感到無知,因為世界上還有太多的東西我絕對還沒有閱讀過,也無法進行閱讀。
對文本保持開放態度。如果你能理解文本創作的語境,這將使你能夠接受文本的各個側面,你可能會發現這個文本讓人感覺不舒服或者甚至是判斷錯誤。
但是,僅僅因為你不喜歡文本中的某些東西,這并不意味著你就應該抗拒它。我在這里想到的是美國國內關于像《哈克貝利·費恩》(HuckleberryFinn)這類作品的討論,作品包含著我們今天看作是種族主義的,令人無法接受的語言。然而馬克·吐溫卻故意以令人厭煩的態度來同讀者進行溝通,使我們能夠對其主角的含糊性和哈克衍生的那個世界進行更為深刻的思考。
不要只讀“偉大”的作品,而要閱讀能夠閱讀到的一切東西:兒童文學、大眾傳奇、偵探小說、旅行書,等等。對西方盎格魯-撒克遜和維京傳奇興趣的復活是同電腦游戲和電視劇如《權利的游戲》(GameofThrones)聯系在一起的。冰島史詩(Icelandic sagas)出現于日本漫畫之中。在知識分子能夠抓住社會中正在發生的事情之前,大眾文化通常能觸動正在發生的事情之核心。
我的全球新聞翻譯項目為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電子媒體的力量開辟了一幅幅遠景圖。看看博客,看看互聯網社交網站吧。
總之,要無所畏懼。沒有偉大的藝術是來源于膽小怕事的人的。變化并非來自中心,變化來自邊緣。社會和藝術的革命都不是從機構內部產生的。
最后我想說,您一直慷慨地稱我為“世界知名學者”,我并不這么看我自己。我認為,正如我已經從我四個孩子和他們朋友以及我現在的孫子輩身上學到了東西一樣,我自己是一個有幸能與杰出的年輕人共事并向他們不斷學習的人。我的工作在全世界有所益處,這給我帶來莫大的滿足和驕傲,但是我一直以來所追求的是探尋文學與文化的模式,絕無遵循預定道路的想法。
我想引用兩句翻譯過來的語錄作為結束語:(1)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2)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噢,我多么希望自己可以讀懂中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