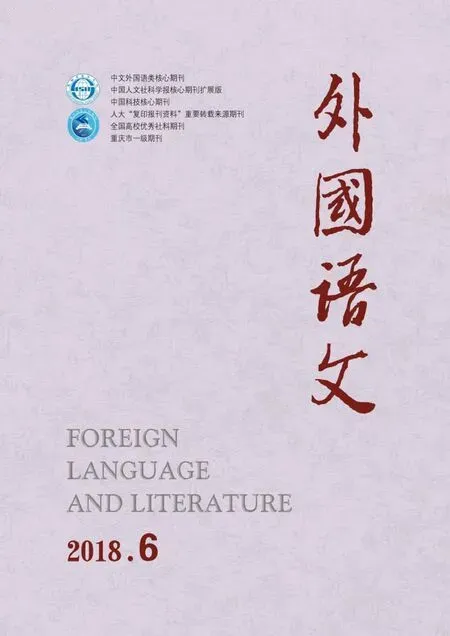意義的百科知識觀
——兼談認知語義學的原則和主張
劉 瑾
(貴州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1)
0 引言
意義問題是一個復雜而古老的問題,而語義學則是一門非常棘手的學問。對意義的研究有各種各樣的理論,如指稱論、概念論、用法論、功能論、認知論、情境論(Barwise et al., 1983)等等。這些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對意義進行了詮釋,但每種理論又有其自身的局限,難以解決意義各方面的問題。認知語義學的誕生,無疑為意義研究提供了更好的視角,拓展了意義研究的范圍,開辟了語義學的新天地。
語言學中有一個傳統觀點,認為語言知識必須與有關世界的知識區分開來,也就是說要把詞典與百科全書區別開來。但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知識尤其是詞義是離不開百科知識的,二者之間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語言表達式的意義是語言表達式向認知結構的映射,即意義是一種心理現象和認知結構,它不存在于語言系統內部的聚合與組合關系之中,而是根植于說話人的知識與信仰系統里,必須最終按心理現象來描寫和解釋。因此,語言知識與有關世界的百科知識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舉一個簡單例子,成熟的香蕉是黃色的,這是我們的常識。香蕉是一種水果,其詞義中本不含有黃色的意義。但這一常識逐漸融入詞義中,也就是說黃色變成了英語詞“banana”詞義的一部分(Taylor,2007:120 )。
有關意義的解釋,認知語言學有一個重要觀點:意義具有百科知識性。但這些百科知識性在語言中是如何體現的呢?認知語言學并沒有做出系統的回答。因此,本文將首先闡釋意義的百科知識性,并在此基礎上論述認知語義學的原則和基本主張。
1 意義的百科知識性
認知語言學把意義和意義的建構看成是語言的核心組織原則。語言是人類認知過程和認知結構的反映,而這些認知過程和認知結構是多方面的、動態的和互動的。正因為語言被認為是人類認知和認知過程的反映,因此語言的各個方面都是有意義的,包括形態和語法。語言各個方面的意義其實都是離不開百科知識的,比如句子的意義。句子的意義是檢驗語義學理論的試金石。通常,我們可以把句子分為兩大類:分析句和綜合句。例如:
(1)單身漢是未婚男子。
(2)那棵樹上有一只小鳥。
例(1)是指語法形式和詞匯意義為真的句子,也就是說,我們無須參照外部標準就可直接從意義上判斷是真或是假的句子,這種句子叫分析句。例(2)的真假必須根據事情的非語言事實,也就是要根據我們的經驗標準來判斷,這種句子叫綜合句。然而,分析句與綜合句之間的區別并非總是涇渭分明的。例如:
(3)亞里士多德是一位哲學家。
(4)2加5等于7。
(5)他的女朋友是一位男性。
(6)戰爭就是戰爭。
這四個句子都是分析句,我們根據字面義可以判斷其真假,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如果情況發生了變化,它們意義的真假值就難以判斷了。也就是說,看似為分析句,有時也要根據現實世界中實際情況的變化而定,即要根據非語言知識來判斷。這樣,分析性與綜合性的區別就不是那么清楚了。由此可見,意義的解釋和判斷是離不開百科知識的。
根據認知語義學的觀點,意義具有視角特征、動態變化特征、百科知識性和非自主性特征,基于使用和經驗的特征(Geeraerts,2006: 4-6)。認知語義學把意義等同于概念化,即意義建構的心理過程,包括人類心理經驗的各個方面,具有動態性(Langacker,2008: 30-31),涉及人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體現了人類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通過語言建構并由語言表達的意義并不是大腦中獨立存在的模塊,而是對我們所有經驗的反映,這是認知語言學的一個重要觀點,即“經驗觀”(Ungerer et al., 2006)。意義無法與其他形式的知識割裂開來,從這種意義上講,意義就具有百科知識性和非自主性特征。意義的這種經驗基礎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人是身心的統一體,既有心智的存在,更有軀體的存在,這是人類的生物屬性。人類的這種屬性直接影響自己對世界的經驗,而這些經驗必然會反映在我們的語言中。例如,我們的身體有“前后、左右、上下、里外”等方位,我們對情景進行描寫時就取決于我們自身的視角,什么東西在我們前面、后面、左右等。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把這樣的方位投射到其他物體上,從而得到這樣的語言表達式:“車前/后,車里/外”“山上/山下”,等等。
第二,人類不只是生物體,具有生物屬性,還有社會和文化身份,具有社會文化屬性。語言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產物,是文化的載體,因而人類語言可以透露人們的社會文化身份。也就是說,語言可以反映每個言語社團以及個體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經驗。我們以范疇“鳥”為例。語言的百科知識性意味著我們不得不考慮人們對鳥的實際熟悉程度:我們不僅僅要考慮“鳥”的一般定義,還有了解麻雀、燕子、企鵝、駱駝等范疇成員(Geeraerts,2006: 5)。這些經驗會因文化而異,在一種文化中典型的、為人們最熟悉的鳥,在另一種文化里未必典型、為人們最熟悉,這就會影響人們對有關范疇“鳥”的知識。Cruse(1990: 389)也認為:“在認知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范疇典型顯然受熟悉程度和經驗的影響:在南極長大的人對于鳥的典型的認識跟在亞馬遜河流域或者在撒哈拉沙漠地區長大的人就不一樣。” 再如,我國北方的人有可能視“蘋果”為“水果”的典型,而南方人則可能視“橙子”為典型;巴西人最可能會視“足球運動”為“球類運動”的典型,而中國人則可能會視“乒乓球運動”為典型。但一般而論,一個范疇總會有其典型。
第三,生態環境的影響。人類語言歸根結底是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語言雖不是自然,但自然一定包括語言,語言與自然密切相關,并會透露自然環境的一些特征。我們最熟悉的例子莫過于愛斯基摩人有關“雪”的詞匯以及阿拉伯人有關駱駝的詞語。例如,在傳統的阿拉伯語中與駱駝有關的詞就有六千多個,這些詞表達駱駝的顏色、體形、性別、年齡、行走、狀態、裝備,等等。現在這些詞匯大部分都消失了,原因在于生態環境的改變、交通工具的發達,駱駝的作用越來越小了。由此可見,把人類語言看成生態系統中一個特殊的現象來研究,可以為我們了解人類的經驗提供重要的依據。
意義的上述經驗基礎正是其百科知識性的反映。認知語義學認為,意義的理解必須依賴由背景知識結構組成的語境。這個由百科知識組成的背景知識結構就是“認知域”或“概念域”(Langacker,1987;Evans et al., 2006),大致相當于Fillmore(1982)的“框架”或Lakoff (1987) 的“理想化的認知模型”(ICM)。
概念域是我們概念系統中的知識結構,其范圍包括從簡單的概念到復雜的知識系統。概念系統包含并組織相關的觀念和經驗。例如,有關時間的概念域就可能與 “昨天”“今天”“明天”“星期一”“星期二”等時間概念相關,也可能與像“中秋節”“春節”這樣的時間事件相關。如果我們說“春節很快就要到了”,我們實際上是在用比較具體的概念域去理解比較抽象的概念域。這里的“春節”是用具體的物理“運動”域來概念化的,因為這個句子用了“到”這個表示運動的詞。很顯然,“春節”是不可能運動的。
認知心理學家認為:“詞匯的價值并非來源于其本身,而在于它們所反映的概念和關系,以及它們所反映出的有意義的知識結構。”(羅伯特 等,2008:234)因此,詞和更大的語言單位(如短語和句子)是進入無限知識網絡的入口。對一個語言表達式的意義要進行全面的解釋,通常需要考慮意象(視覺的和非視覺的)、認知識解、隱喻、轉喻、認知模型以及對世界的樸素理解等一系列百科知識。因此,一般來說,一個詞的意義靠孤立的詞典似的定義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必須依賴百科知識。一個句子的意義更是如此。
2 認知語義學的原則和主張
意義是認知語言學研究的核心。認知語義學最基本的理論成分是“概念”,即心理表征的一個基本單位。概念在認知語義學中的中心地位是認知語義學的區別特征之一,這是因為語言表達式的意義等同于概念化。就上面的論述以及認知語義學目前的發展狀況來看,我們可以用四個原則以及六個基本主張來概括認知語義學的研究內容和范圍,它們可以把認知語義學與其他意義理論區別開來。 認知語義學的四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概念的非自主性或非獨立性原則。
概念在大腦中并不是孤立的原子單位,其理解必須依賴由背景知識結構組成的語境。這個背景知識結構或語境就是“認知域”或“概念域”。例如:
(7)a.都星期六了,還在開會?
b.都星期六了,還不開會?
根據我們的常識,一周有7天,星期六是周末,應該休息,所以(7a)所傳遞的含義是:“都星期六了,應該休息,不應該開會。”(7b)所傳遞的意義則可能是:“這周都要結束了,還不開會?”這兩個句子的理解,都得依賴對概念域“一周”的理解。
第二個原則:認知的理想化原則。
Lakoff(1987:68)利用“理想化的認知模型”來描寫一些概念(如“單身漢”和“母親”)的背景知識是如何關涉理想的經驗模型,以及描寫一些來自于ICM與一個更復雜的實體之間錯配的范疇化問題。每個ICM都是一個復雜的結構整體,一種格式塔,并運用了四種建構原則:命題結構、意象圖式結構、隱喻映射和轉喻映射。因此,ICM在強調一個語義域與外部經驗之間的關系時,它與“認知域”一樣具有同樣的功能。例如,“單身漢”的定義與一個ICM 有關,那就是人類社會中有婚姻(典型是一夫一妻制)和公認的婚齡存在。該理想化認知模型并沒有提及神父、同性戀者以及被允許有四個妻子但只有三個妻子的穆斯林等情況。就這一理想化認知模型而言,單身漢僅僅指一個未婚的成年男子。但是,該模型并不完全符合現實世界,因為如果是這樣,教皇、人猿泰山等都可以稱得上是單身漢。
第三個原則:語義表征與世界的關聯原則。
該原則涉及心智中語義的表征與說話人經歷的世界之間的關系。根據該原則,心智在語義結構的創建過程中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并且以某種方式對說話人在世界中的經驗進行概念化。不同的說話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對相同的經驗進行概念化。因此,語言的眾多方面,特別是語法的屈折變化、詞語及語法結構,可以被描寫為是對不同經驗的概念化的編碼。認知語義學中的許多研究都是對概念化過程進行分析和分類的。例如,Talmy(2000)把“識解”(construal)看成是一種意象系統(imaging system); Lakoff(1987)把隱喻、轉喻以及意象圖式轉換(image schema transformations)看成是三種概念化過程;Langacker(1987,2008)則把大量的識解操作看成是“焦點調節”(focal adjustments)。不過,他們三人所討論的這些過程均是經驗表征過程的例子。
第四個原則:典型范疇化原則。
該原則體現在對范疇的結構或組織的研究方法當中。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人類認知的產物,也是為人類認知服務的工具,因此在結構和功能上很有可能反映了人類普遍的認知能力。這些認知能力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范疇化能力。研究范疇化能為揭示語言形式的意義提供重要的依據。認知語義學認為,范疇有一個內部結構,即“典型結構”(prototype structure),Lakoff稱之為“輻射范疇結構”(radial category structure),即是說,一個范疇的語義中重要的方面涉及范疇成員之間的關系。范疇延伸的關系就是一個范疇中典型成員與邊緣(非典型)成員之間的關系。例如,英語表示看的動詞“stare”“peer”“squint”“ogle”中,“stare”就比其他三個動詞更具有看的特征,也就是說更典型。
以上四個原則中的四個結構成分“概念”“認知域”“識解”以及“范疇”,代表了認知語義學中最廣泛接受的基礎。“概念”是一個心理單位,是關于物體種類的心理表征;“認知域”是表征概念的背景知識或百科知識;“識解” 是一個人在世界中的經驗被各種方法表征的過程;“范疇” 是包含于概念中的物體種類,在內部是由范疇成員之間的典型延伸關系建構的,在外部是由范疇之間的分類關系建構的。當然,除了這些共性的東西之外,認知語言學家之間還是存在較大差別的。但是,這些結構成分把意義的認知語言學研究方法聯系起來,使其有別于其他的意義研究方法,這是毫無疑問的。
認知語義學的六個基本主張(G?rdenfors,1998; Lakoff,1987):
(1)意義等同于概念化。
認知語言學認為,意義即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而不是可能世界中的真值條件;語言結構依賴于概念化,而概念化又基于我們的身體經驗。認知語義學明確承諾要把意義的身體維度、文化維度和想象維度結合起來,共同致力于研究概念化這一核心問題。一個語言表達式的意義(詞、短語、句子等)就是在說話人或聽話人的大腦里激活的概念。也就是說,意義存在于人類對世界的識解中,它具有主觀性和動態性,體現了以人類為中心的思想,反映了主導的文化內涵、具體文化的交往方式以及世界的特征。這一觀點表明,意義的描寫涉及詞與大腦的關系,而不是詞與世界之間的直接關系(文旭,2014:15)。意義的這種認知觀不同于許多哲學語義學理論。認知觀認為,語言表達式的真值條件的形式不決定意義,表達式的真值是次要的,因為真值涉及心理結構與世界之間的關系。簡言之,意義先于真值,而不是等于真值條件。
(2)概念具有典型效應。
在哲學中,概念的經典解釋就是亞里士多德的必要和充分條件理論。根據這一理論,一個概念可以用一系列的定義屬性來描述,即用充分必要的語義特征來描述,如“單身漢”的定義屬性就是“人類、男性、未婚、成年人”。這樣一來,范疇就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關系。然而,當我們把經典理論運用到自然語言中所表征的概念時,就會遇到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實際上,很多概念的邊界是模糊的。正是由于一些學者對概念的經典理論不滿意,所以在認知心理學中發展出了典型理論(prototype theory)。根據典型理論,每一個范疇都是以一個典型來代表整個范疇的。在認知語義學中,人們試圖解釋概念的典型效應。一個概念常常用一個圖式來表征,并且這樣的圖式正像概念一樣可以有變體。典型理論對認知科學具有重要的啟示,因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范疇的內部結構上,以及范疇具有“核心”和“邊緣”這一事實上。這為很多語言現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3)語義成分具有拓撲空間性。
認知語義學認為,語義成分不是建立在根據某種規則系統組成的符號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空間物體或拓撲物體基礎之上的。認知語義學里的心理結構就是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因此沒有必要進一步把概念結構轉換為心智之外的東西。此外,用來表達意義的概念圖式不是像心理語言(mentalese)那樣具有句法結構的符號系統,而經常是以空間結構為基礎的。
(4)意義制約句法結構。
意義對于句法結構非常重要,而且有可能制約著句法結構;不考慮意義,句法結構很難被描述。在認知語言學中,意義是核心內容,是基本成分,它以感知的形式在語言還未完全發展之前就存在了。語義圖式的結構對可以用來表達這些圖式的語法結構具有限制作用。這里我們以事態為例,說明意義是如何限制句法結構的。在西方文化中,時間被看成是一條線,因此,談論“過去、現在、未來”這三種基本時間是有意義的。這種現象體現在大多數語言的時態語法結構中。但是,在一些時間有循環結構的文化中,或時間沒有賦予任何空間結構的文化中,如要區別過去與未來就沒有什么意義。在具有不同時態結構的語言中,時態結構反映了不同的、潛在的時間概念結構。
(5)感知決定認知模型。
認知語義學認為,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主要是由感知決定的,而意義并不獨立于感知。由于我們大腦中的認知結構直接或間接地與我們的感知有關,因此,意義至少部分是以感知為基礎的。這明顯與語義學傳統中的唯實論相沖突,因為后者認為,既然意義是語言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映射,那么意義與感知就沒有關系。其實,我們所能談論的都是自己所能看到或聽到的東西,同時我們能創造讀到的或聽到的心理圖像或真實圖像。這就意味著我們能在表征視角形式與語言代碼之間進行轉化。認知語義學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我們把感知貯存在記憶中的方式與詞義貯存在記憶中的方式具有相同的形式。
(6)很多語義知識植根于意象圖式。
認知語義學認為,我們的很多知識并不是靜止的、命題式的和句子式的,而是植根于意象圖式或者是由意象圖式建構的。這種意象圖式是一種具身概念結構,往往通過隱喻和轉喻操作而發生改變。認知語義學中最重要的語義結構就是意象圖式的語義結構。意象圖式有一個內在的空間結構。Lakoff(1987)和Johnson(1987)認為,像“容器”“路徑”“系聯”這樣的意象圖式是最基本的意義載體。他們還認為,大多數意象圖式與運動經驗緊密相關。隱喻和轉喻在唯實論語義學理論中是很難得到解決的。在這些理論中,隱喻和轉喻被認為是語言的偏離現象,常常被忽視或通過特殊的文體規則來解釋。相反,在認知語義學中,隱喻和轉喻卻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人類認知的重要工具。
3 結語
意義是認知語言學的核心,更是認知語義學的焦點,具有視角性、動態性、百科知識性等特征。本文首先闡釋了意義的百科知識性,并在此基礎上論述了認知語義學的四個原則和六個基本主張。意義的百科知識性表明意義是非自主的,具有主觀性,體現了認知語言學的經驗觀和整體觀。認知語義學的原則和基本主張界定了認知語義學的內涵以及研究范圍,為認知語義學的確立搭建了框架,也為認知語言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