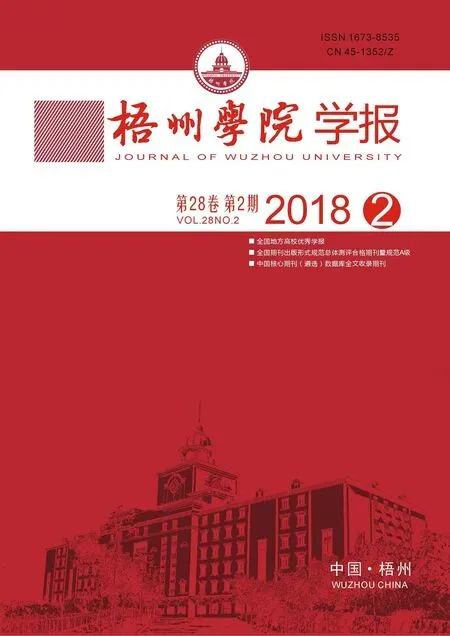黑暗中的舞者
——姚鄂梅小說創作論
田宏宇
(淮南師范學院 文學與傳播學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楚人好巫鬼”,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小說家姚鄂梅,對于神秘、幽深和黑暗的東西總是情有獨鐘。她的小說,充滿了命運的陰霾、生命的黑暗、痛苦的掙扎和晦暗的情緒。黑暗,像一道鬼影,藏身于陽光照耀的人世,在不經意間,裂開生活的縫隙,綻露出存在的深淵和本相。從《死刑》《黑色》《黑眼睛》《黑鍵白鍵》到《穿鎧甲的人》和《在人間》,黑暗始終都是逃避不開的話題。它觸摸到了生命的底處,升騰出一股陰郁和惡的力量。正如姚鄂梅所說:“我在嘈雜和喧囂中行走,內心卻在黑暗和孤獨中日益靠近文學這顆種子。”[1]陽光下的生活總是潛藏著無窮的鬼魅。黑暗,這個融化了所有顏色的極端,在靜寂、恐怖、死滅和瘋狂中,賦予了生命另類的力量。它詮釋了人性的惡與蒼涼,同時也散發了生命別樣的滄桑。這就是姚鄂梅——黑暗中的舞者,游走和舞蹈在命運晦暗的怪圈中心,以寫作為拐杖,尋覓和探索著最耀眼也是最理想的光芒。
一、生命的痛感:存在的痛苦和掙扎
王安憶說過:“藝術的創造者還是一種特別具有情感能力的人,他應該具有敏銳的感受能力,就是說他應該具有痛感。”[2]姚鄂梅的身上始終揮發著對生命和疼痛極度敏銳的感覺。她的創作史,毋寧說是女性生命的生理和情感疼痛史。她的殘忍和疼痛并行,黑暗與冷酷同在。肉體的劇痛,往往伴隨著靈魂的巨大變化。姚鄂梅在書寫現實的黑暗之時,同時也緊緊地抓住了靈魂的痛感和吶喊,揭示了人性存在中更為深邃的東西。
在姚鄂梅的“李默”系列小說中,這種痛感就貫穿始終。《黑色》中,李默在身體上遭受到繼父凌辱之后,靈魂也沾染上了黑色的冷漠。她的語言、穿著和個性,都透露著一種尖銳的、被刮傷的痕跡。
她們把小謝拉到窗前,站在八樓的窗前,順著女編輯們敲起的食指,小謝看見了街那邊李默細細黑黑的身子,一款奇大無比的黑色皮包掛在肩上,單薄的肩越發顯得脆弱不堪。從頭到腳的黑色,高舉著一張淡淡的灰白的臉。她不疾不徐的冷氣流,在早春曖昧的空氣里投下一團小小的陰影。
李默的冷漠和高傲,顯示了她內心世界的彷徨與無助。在后來又遭遇到浪蕩公子小謝的拋棄后,她那個保護自己的鎧甲丟棄了,赤裸裸地站在人群的中央,就像摔碎了的花瓶,一無是處。她開始報復,打開煤氣爐,想要毒害自己的母親,乃至于謀殺自己的情人。在這個近似瘋狂的女性身上,生命折射出了受到創傷后激烈的報復和攻擊本能。人性之惡在此顯露無疑。靈魂被逼仄到了死胡同,整體的壓抑和絕望又加深了痛感的沉重。“他人就是地獄”的詛咒久久地回旋在每個人的頭上,形成了人與人之間互相傷害和互相抹殺的過程。
如果說《黑色》側重的是身體之痛的話,那么《穿鎧甲的人》和《像天一樣高》則指的是精神之殤。在《穿鎧甲的人》中,主人公楊青春,作為一個沒落的文學青年,在沒有知音的農村,依舊堅守著自己的追求。面對村人的謾罵和不解,面對老婆的鄙視和厭棄,他依舊像孔乙己一樣嘟嘟囔囔著自己的生存哲學,抵抗著現實生存的壓力和打擊。正如《像天一樣高》中的康賽,他樂于貧窮,并且竭力在其中尋找詩意的生活和精神的向度。然而,這種對精神的追尋越純粹,其跌落和破碎,也就越加觸目驚心。這里就出現了疼痛的悖論。肉體上越安逸、越舒服和越麻痹,精神上就越痛苦、越迷惘和越空虛;相反,肉體上的貧瘠和受苦,反而增加了精神的厚度和載重。楊青春和康賽在物質的貧困和窮酸中,都保持著樂觀向上的精神。楊青春夜里偷偷寫日記的習慣和他踩著水車樂淘淘地思想的“毛病”,都顯示了精神的豐富與天真;對于康賽來說,陶樂那天天吃野菜,沒有任何營養供給的生活,反而給了他的天使——詩歌更多的靈感。然而,二者看似堅定的追求,在現實面前雖然做好了飛蛾撲火的準備,卻只是在一瞬間,轟然崩潰。楊青春因為李吉酒后失言,稱他不過是中學生水平,一下子變得目瞪口呆,精神幾近頹廢;而康賽在母親的勸說和威逼之下,終于不忍心母親的付出,從一個堅定的詩人做回了一個正兒八經的公務員。這是一種理想之殤,這種痛猶然勝于前者。原來,精神的鎧甲,竟然如此不堪一擊。何處去尋找精神信仰的棲息之地,才是在痛苦中真正值得深思的問題。
二、人生的悖論:悲劇只道是無常
悲劇是人類無力掙脫的苦難和命運。當人類以求善和圓滿為目標時,結果卻總是出乎意料。西西弗斯遵從了眾神的命令,去推山上的石塊。當他終于汗流浹背地將石塊推到山頂時,石塊又重新從山頂滾落下來。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努力與辛勞付之東流。悲劇的本質就在于此。它讓你無可奈何地面對無常的事情發生,然后又束手就擒地掉入了社會的陷阱。悲劇看起來是無緣無故的。所有的個人付出和努力,其結果歸空為零。魯迅說過,“無物之陣”[3],福克納則指出:“到處都同樣是一場不知道通往何處的越野賽跑”[4]。盡管阿Q的精神勝利法和加繆的自我意識存在其中,但畢竟是自我欺騙和自我慰藉罷了。無常統攝人心,罪孽降臨人間。何去何從?人們陷入了生存的惶惑和恐懼之中。
《在人間》就揭示了這樣一個無常的悲劇。主人公賈南(出家前名為慧真)從小生活在晨鐘暮鼓之中,偶然的機會,她碰到了浪蕩子艾津,少女懷春的情懷,使得她喜歡上了艾津,并被他引誘,犯下了孽緣。沉重的鎖鏈,產生于心獄;反抗的悖論,卻造就了辛酸和無常。賈南還俗后,立志行善積德,悔過贖身,結果卻總是遭遇無常。先是治好了隊長父親的痔瘡和高血壓,沒想到隊長父親卻利用強健的身體猥褻了五歲的小女孩。后來,她幫助許阿姨照顧她的傻女兒慧蘭,以假結婚的名義給了慧蘭安穩的生活,然而慧蘭的妹妹慧珠結婚時,卻因為沒有住房搶占了她和慧蘭的房子。傻女慧蘭一氣之下燒了他們的婚房。之后,賈南又幫助古師傅拾垃圾,被看成存心不良;收養沒人要的孤兒,卻早早地送了孤兒的性命。無常的命運總是在作祟,而善行的舉動卻又被罪惡消解,反而帶來更大的存在陰影。“何處是歸途,長亭加短亭。”賈南恐懼了,她在控訴,也在渴望。善因不得善果,那么作惡呢?人間有著人間的處事法則,這就是俗世的邏輯。于是她想到了報仇。她吃的苦、受的罪還不夠么,她要向艾津討個說法,報仇雪恨。然而,當她滿懷怒火地趕到艾津面前的時候,出乎意料地發現了一個更為不幸的人。報仇的野心頓時化為生命的空虛和無常,賈南哭了。
有著類似情節的《黑眼睛》同樣揭示了生命的無常和悖論。理發師阿昌的妻子眼疾,因為醫生的失誤,導致雙目失明。阿昌決定復仇,可是在醫生趙明終于被阿昌逼入池塘的那一刻,阿昌逼迫趙明自己做出選擇,要么摳出雙眼作為補償,要么凍死在池塘之中。趙明竟然放棄了,他甚至祈求阿昌一棒子把他打死。阿昌驚呆了。他沒有想到趙明也是一個不幸的人:老婆出軌,孩子討厭,事業全無,一輩子背著庸醫的罪名永遠地抬不起頭來。他早就不想活了。文章中描寫了趙明沉沒到水中,阿昌開始用棒子拯救他的過程:開始還試試探探、晃晃悠悠,到后來就是急躁地亂罵,當終于看到醫生沒到頭頂的時候,阿昌就用棍子往深水里亂攪,終于殺人者成為了救人者。原來,不幸的背后揭示了更大的不幸。而在《忽然中年》中,李華馬上要功成名就了,卻兵敗垂成。為了報復當年丈夫出軌的行動,李華私自和另一個男子發生了關系。可是這種復仇,并未給她帶來快樂,反而更大的罪惡籠罩其心;生命的滄桑和老態重新覆蓋了整部小說。生存意義的隕落和行為目的的消解,再次顯示了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輕帶給人的創傷和悲痛。
行善,未必救贖;以惡對惡,卻換來更大的空蕩和虛無。人的生命完全掉入了無常的掌握之中。也許“天下的許多事情都是在翻筋斗,未翻之前這么站著,既翻之后還是這么站著,然而中間畢竟有這么個筋斗。”[5]是善,還是惡?心靈的博弈從來沒有停止,黑暗與光明的交替卻頻繁閃爍。黑暗中蘊藏著不幸,光明中卻也壓抑著蓬勃生命力的掙扎與探尋。漫長的歲月打磨,無法銷跡的是那些抹不去的傷痕,卻讓晦暗更加地刻骨銘心。如果拋卻道德的憤怒和倫理的批判,人性中也蘊含著某種無辜和受難。如何理解、如何救贖,小說在無常的迷宮中設置了人性最大的難題。
“這是一種愚弄,一種靈魂的自我嘲弄,天使見了會羞慚落淚,魔鬼也會啞然失笑。悔罪的沖動到處追逼著他,將他驅趕到這里來。”[6]罪惡隱藏在人的本性之中。“但文學是寫實的,要寫善惡相生的復雜性,才能寫出人性的深度。”[7]小說借助人物在社會中的掙扎,深入到了人性背后的心靈動蕩。它在朝著原罪的觀念前進。在這個觀念的統領下,人類的處境和命運、靈魂的遭遇和掙扎迤邐展現,成就了一副苦難靈魂的人間圖像。
三、靈魂的受難:意志的淬火與強韌
對于偉大的作家來說,受難是他們的第二故鄉。沒有經歷過人生的苦難,落筆總是停留于淺薄和表面,無法深入生命的深處。黑暗,蘊藏著人性的丑陋和惡劣,飽含著社會敗類和腐朽。同時,在黑暗中,靈魂也得到從未有過的經歷淬煉和升華。尼采說過:“通往人們自己天堂的道路,總須穿過人們地獄里的肉欲。”[8]黑暗是意志淬火的地方,同時也是理念和靈魂最終升華和飛騰的地方。沒有經歷過黑暗的作家就不能洞悉人性的深邃。一個距離黑暗最近的作家,距離不幸和苦難最近的靈魂,同時也離著光明和希望最近。只有經歷了黎明前最痛苦和最無望的黑暗,人們才能守得云霧見日開,才能守護到希望的來臨。
在姚鄂梅的小說中,女性不是柔媚的、悲傷的或者追懷的,更多的則是復仇的美狄亞,是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對象。可是,她們同樣高昂著命運的頭顱,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黑暗的泥漿中舞蹈著自己的生命,蔑視著無常命運的壓迫,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跳出最為絢麗的樂章。
在《白話霧落》中,麻姑家的三代人就是這樣一種形象。《白話霧落》敘述了三代女人在黑暗中對愛情堅定的信仰和瘋狂的追尋。姚鄂梅有很多涉及愛情的作品,不是欲望占有,就是丑惡欺騙。這篇也不例外,然而卻多了一樣東西,那就是蓬勃、堅韌、超強的生命力量。麻姑在很早之前就做了童養媳,受盡了婆婆和丈夫的虐待。婆婆死后,她終于做了大,然而生活并不平坦。丈夫不久就死了。丈夫去世后,她的愛情就像遲到的花朵,悄然而固執地綻放了。在此,她的忠貞和熱情一覽無余。她為丈夫請了三年的飯,這幾乎是在孤獨和痛苦中的三年牢獄般的堅持。每頓飯,她都像宗教儀式一樣的隆重。麻姑的癡迷和執著,有著一股瘋狂的堅貞和愛情的意蘊。它蘊藏在辛酸的苦寂和孤獨之中,卻迸發出生命別樣的光彩。麻姑的這種堅持,藏在骨子里,同時也一點不剩地傳給了她的下一代阿山和阿水。
阿山由于夢的暗示,遇到了她所認定的命中王子——高工。可是高工另有家室的隱衷,使得他離開了阿山,剩下了阿山苦等了他大半輩子。高工走后,阿山的精神已經崩潰了,神經也出了問題。她吃飯睡覺啥事都想著高工,即使女兒小魚的出世人間,也不能絲毫減緩她對他的思念。這種癡迷近乎到了神經質的地步。后來她終于不提了。然而麻姑看得出來,她只不過把高工從口頭轉到了心上,并且刻骨不忘。
與此相對的是阿水。她是霧落有名的美女子。表面看起來浮浪,實際上卻有著對愛情獨特的看法。經歷過兩次離婚的挫折后,她一度頹廢。然而在這時她遇到了和她第一次相親卻沒有見到的男人——秦自清。重新相遇的他們,飛快地陷入了愛情的汪洋大海。他們不顧倫理,忘記家庭,甚至到了不知廉恥的地步。任何的謾罵威脅,乃至于秦自清老婆的以死相逼,都沒有動搖二人對愛情的堅持。姚鄂梅在寫這一點時,確實有著獨特的一招。每個人的愛情都有著特別的光彩。麻姑的愛情,就像老年人追憶似的癡迷和沉醉;阿山的愛情是在苦楚中的一廂情愿的枯守;至于阿水的愛情,則是在苦難中迸發著的熱烈火焰,幾欲把整個霧落村弄得地動山搖。先是秦自清老婆扔磚頭報復,后是秦自清的老婆拿刀相逼,再就是阿水為了躲避四處逃難,到最后乃至于二人在經營“陽光工程”時相繼落難。秦自清被陽光灼瞎了眼睛,而阿水則被陽光強勁的光芒燒毀了面容。然而,二者的愛情,卻像守著前世的承諾一樣,不為所動。他們甚至在陽光工程的玻璃后面挖好了墳墓,準備一起葬在那里。這使得我不禁想起了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亞。他們就像無所畏懼的英勇戰士,在苦難中水乳交融,相濡以沫,高亢而激情澎湃地走在最前列。他們的愛情,在罪愆和夢魘的追逐下,也綻放出最為壯觀也最為轟轟烈烈的光芒。
殘缺中蘊藏著圓滿,不幸中暗示著追尋。姚鄂梅的寫作,以深遠的悲劇意味和苦難性質,賦予了文學以感染力和生命力。她在用苦難寫作。尼采說過:“一切文字,我只愛以血書寫者。”[9]沒有生命的劇烈創痛,沒有面臨絕望和苦難的黑暗和罪惡,生命力就會消弭而變得軟弱。姚鄂梅的語言冷靜中透露著蒼勁,抑郁中也有著堅持,那是蘊藏在生命深處對光明的渴望和追尋。也正是它,在最艱難處逼仄出了光亮,在最黑暗的地方為人們指引了前進的方向。
姚鄂梅在《在寫作中覺悟》中說過,“我以我的寫作為杖,執著于向人性深處的東西靠攏……但人的內心不一樣,修行過的眼光就不一樣。但是肯定會有。這是一個勇敢的修行者的囈語,也是一盞虛弱的燈光,閃閃爍爍地出現在又深又長的隧道里。”[10]從生命的痛感到人生的悖論,再到靈魂的受難,姚鄂梅的小說始終直面于人性深處的慘烈陰郁,并著力挖掘靈魂的深層內涵。它是一場心靈解構和拯救的過程。黑和冷是永恒的色調;掙扎和抗爭,也構成了無路可走時的艱難的救贖。然而,救贖在哪里,同樣也成了姚鄂梅創作的瓶頸。她在小說中很少揭示。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創作者思想的圈囿和局限:《在人間》中賈南無望的救贖,《穿鎧甲的人》中楊青春的自暴自棄,《大約在冬季》中李默的無言哭泣等,都暗示了姚鄂梅并未尋找到真正的解脫之道。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認為文學“其精神存于解脫”[11]。然而,光明在哪里呢?在“虛弱的燈光”和“閃閃爍爍的隧道里”,這個黑暗的舞者終究落于迷茫和無助的狀態,不能不說是創作中的一個不足之處。
[1] 陳競.姚鄂梅:“十年坐冷凳”的修煉[N].文學報,2007-10-11.
[2] 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論稿[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357.
[3] 魯迅.魯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104.
[4] 威廉·福克納.我彌留之際[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12.
[5] 梁遇春.春醪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183.
[6] 張心嘉.美國早期文學中上帝形象的變化[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3).
[7] 孫婧.尋找失落的精神——裘山山小說的日常生活書寫與當代的文學理論價值建構[J].當代文壇,2011(4).
[8] 尼采.快樂的科學[M],轉引自米勒.福柯的生死愛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8.
[9] 李建軍.穿越人性黑暗的文學遠征——讀章詒和小說《劉氏女》[J].小說評論,2011(4).
[10] 姚鄂梅.在寫作中覺悟[J].青年文學,2006(23).
[11] 王國維,蔡元培,魯迅.王國維、蔡元培、魯迅講紅樓[M].北京:長征出版社,20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