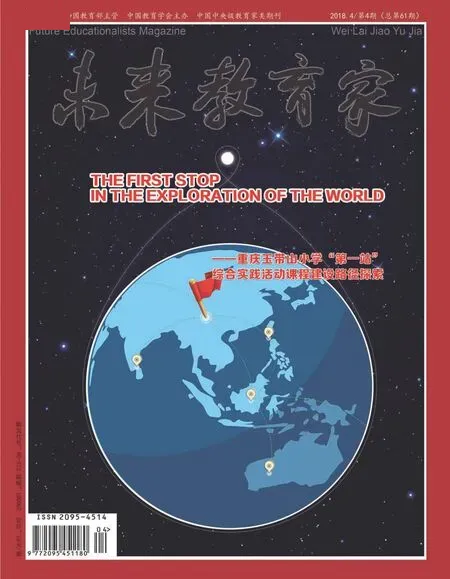教師的表情是一所學校的名片
表情
一位教師朋友和我聊天時說,她被她的女兒尊稱為“戲精”——前一刻正在和顏悅色地對她班里的學生說話,轉過身來對女兒卻是“劈頭蓋臉”,比川劇的變臉還厲害。那時候她的女兒在她任教的小學上學,經常享受這種待遇。
這位朋友其實是非常優秀的班主任,她從來沒有對學生發過火,帶的班是出了名的好。她只是輕度“選擇性瞬時脾氣不良癥”患者(此處有“大笑”表情)。我們在學校經常看到的一幕恰恰相反,前一刻還在跟同事正常說事兒,轉身就能“惡狠狠”地對學生說:“xxx,你在干嘛呢!”
不少人都說過,看一所學校好不好,一堂課好不好,就看學生的表情。這話一度感動了很多人。但我們也知道,孩子的臉說變就變,其實很難捉摸,要從孩子的表情中讀懂孩子的內心,并非易事。單從孩子的表情來進行判斷,恐怕也有失客觀。對孩子的很多誤解,很多“我以為他/她沒事了”,“我以為他/她理解了”……,都是從錯誤解讀孩子的表情開始的。
而解讀一所學校或課堂還有一個重要的“信息源”,那就是教師及每個教職員工的表情。或許成年人更會“裝”,但成年人的“裝”(或“不裝”)成年人都懂,不像兒童的表情,即便沒裝也不一定懂。
所以,或許更具有“指示劑”作用的,是教師的表情。一所學校好不好,寫在孩子們的臉上,也寫在教師的臉上。是焦慮緊張多一些,壓力大一些,還是更舒心一些,更有干勁一些,是能夠從教師的面部表情看出來的。教師的表情或許更是一所學校的名片。
反饋
很多學校都有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讓學生對教師進行反饋,并以此作為評價教師的重要依據。問卷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多有參考價值的信息,但一所學校如果過度依賴問卷,恐怕會出大問題。
我們都說要把學校建設成為一個“家”,還要讓教師“以校為家”。什么是“家”?家就是“有話就可以說”的地方,溝通交流的成本降到最低。問卷無非是獲取信息的一種方式。家里的溝通為什么不需要問卷?沒錯,因為人少。但人少不一定就有溝通。還因為家里的人天天在一起,相互都了解、理解,可以及時溝通。
如果我們過度依賴于問卷調查的結果,而不是日常的互動溝通,那問卷提供的信息即便準確,那也已經晚了。
我們不是要辦一所大家都相互理解,溝通順暢,形成合力的學校嗎?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重點放在加強和支持教師和學生的順暢溝通,教師和領導干部的順暢溝通上呢?
是教師通過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某個學生原來這么長時間對他的課有意見好呢?還是我們建立起有效的機制,讓學生(及家長)能夠信任教師,通過日常途徑及時向教師有效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意見,并和教師一起尋求問題的解決方式好呢?
是我們的領導干部每學期在電腦前查看冷冰冰的統計數據,發現某老師“出了問題”好呢?還是干部們平時就跟老師們摸爬滾打在一起,有問題及時發現,共同面對,合力解決好呢?
不是說調查問卷就不做了,而是有必要在一個更大的框架下重新定位學生對教師的調查問卷。這個框架就是基于充分信任與問題解決的,一套支持性而非評價性的信息反饋系統。我們要思考,在一個更大的信息源系統及互動-反饋-改進系統中,哪些信息最需要,且最合適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來提供?
合適
“一個教育系統的質量,好不過其教師的質量”,這最早來自麥肯錫11年前對全世界教育質量最高的教育系統進行研究后得出的結論。
麥肯錫2007年9月的報告《世界上最高質量的學校系統是如何脫穎而出的》得出的另外兩條重要結論:1.提高教育質量的唯一路徑是改進教學;2.實現教育普遍的高質量,必須要有機制確保學校向每個孩子提供高質量的教學。報告還總結出了在OECD(經合組織)的PISA測試中表現最好的教育系統最重要的三條經驗:1.讓合適的人成為教師;2.把他們培養成有效的教學者;3.確保教育系統能夠為每一個孩子提供盡可能好的教學。
麥肯錫的研究還顯示,在招募具有優異學業背景的年輕人做教師方面,美國遠遠落后于像芬蘭、新加坡、韓國這樣的高成就國家。這些國家的教師百分之百是從學業成績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學生中進行招募。而在美國,不到四分之一的新教師來自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學生。
在教育成就最高的國家,新教師的標準認定是一件國家大事。除了學歷要求之外,哪些是做教師“合適的人”也是各國在探索的一道難題。在人工智能迅猛發展,大有取代任何職業從業者的背景下,對什么樣的人“適合”做教師的思考,必須帶有一種不可回避的前瞻性。
2017年BBC基于劍橋大學研究者 Michael Osborne 和 Carl Frey 的數據體系分析了365種職業在未來的“被淘汰概率”,其中教師行業幸運地屬于被淘汰率最低之列。報告指出,如果你的工作包含以下三類技能要求,那么,你被機器人取代的可能性非常小:1.社交能力、協商能力,以及人情練達的藝術;2.同情心,以及對他人真心實意的扶助和關切;3.創意和審美。
這或許暗示出了未來教師最重要的特征——恰恰不是掌握最先進的技術,因為這個能力是最容易獲得的,尤其對于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