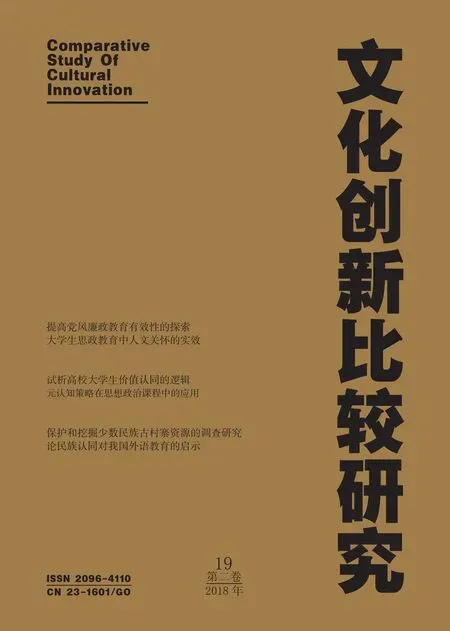論北魏太武帝前后麥積山石窟修造活動低谷的非滅法因素
阮海峰
(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甘肅蘭州 730070)
麥積山石窟的開創年代問題,是學術界迄今仍在討論的問題,很多中外學者都發關表了很有見地的意見。主流觀點認為是開創于后秦(西秦),該觀點認為:麥積山的早期窟龕以74、78、90、165窟為代表,創建于十六國后秦王朝,或西秦[1]。據此觀點,麥積山石窟自后秦(西秦)開創以來,現存有一百九十四個窟龕,后秦和西秦修造有74、78、90、165等窟龕,北魏中后期修造有八十余個窟龕,這中間數十余年的時間里幾乎不見修造的痕跡。學界普遍認為這種現象與太武滅佛有直接原因,但單一的論斷顯然不利于對麥積山石窟的研究,也就是說麥積山石窟在五世紀前期的修造活動的低谷有著更深刻的原因。
1 頻繁的戰亂與人口的大量流失
1.1 頻繁的戰亂
秦州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多兵災人禍。十六國時期,秦州先后為多個少數民族政權所占據。圍繞著秦州,前趙、后趙、前涼、前秦、西秦、后秦、仇池、赫連夏、北魏等諸多政權在一百多年里先后對其進行了爭奪,尤其是五世紀前期的爭奪異常激烈。
五世紀前期,西秦、赫連夏、仇池、北魏紛紛在秦州角力,后秦弘始十四年(412年),西秦攻上邽,后秦守將姚艾戰敗,西秦徙秦州五千戶于枹罕。后秦弘始十四年(416年),仇池楊盛陷秦州祁山,進攻秦州,守將姚嵩戰死。同年,夏主赫連勃勃奔襲上邽,破城后殺死后秦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后秦將士五千人,并毀城而去。赫連定撤離秦州后,楊難當于始光三年(426年)派兵占領上邽,七月在魏軍威脅下又撤出上邽,北魏自此正式占領上邽。太延五年(439年),楊難當發兵上邽,但為北魏擊敗。終太武帝一世,北魏并未解決仇池問題,秦州作為北魏攻打仇池的前沿也經常處于緊張的態勢。
太武帝武力占領秦州后,在其他民族內心尚未歸附北魏的情況下,太武帝的統治十分嚴酷,尤其是對其他少數民族的態度更為強硬。在嚴酷的壓迫之下,秦州的武裝反抗風起云涌,太平真君七年(446年),金城邊冏、天水梁會率領秦益二州雜人萬余戶起義,并得到休官、屠各等民族的響應和路那羅的回應,略陽王元達也趁機發動起義。不久,上邽的呂豐和王飛廉率休官屠各等族八千余家,也發動了起義。太武帝時期,秦州頻繁起義使得北魏對秦州的統治并不穩定,這對剛剛占領秦州的北魏來說是個重大打擊。
1.2 人口的大量流失
十六國時期,秦州地域不只被爭奪,關于人口的爭奪也屢屢見于史料。《晉書·劉曜載記》載:“(劉曜)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余戶于長安。”平陳安后“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余戶于長安。”后秦弘始十四年(412年),西秦攻上邽,徙秦州五千戶于枹罕。譚其驤統計:自永嘉之亂至劉宋的170年間,今陜、甘兩省流徙到今四川省的有5萬人,流徙到河南省的有3萬人,今甘、川兩省流徙到陜西的有10萬人[2]。徙民作為一種統治措施,在秦州區域內被不同政權施行多次,唯不見熱衷徙民的北魏對隴上徙民的記載,劉光華認為:對此只能用此時隴右隴東人口已很稀少進行解釋[3]。
佛教建筑的建設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和較雄厚的人口基礎,而頻繁的戰亂破壞了社會的穩定性,致使大量人口流亡和死傷。而對秦州人口的爭奪,使秦州的人口數量急劇減少,同時也削弱了秦州綜合實力。總之,頻繁的戰亂和人口的流失嚴重阻礙了秦州的發展,導致佛教建筑的建設遭遇到嚴重挫折,麥積山石窟作為秦州首屈一指的佛教建筑,自然不會例外。
2 北魏太武帝時期嚴酷的統治
北魏在占領秦州之后,為鞏固統治,削弱敵國,實行了一系列嚴酷的統治措施,這些統治措施阻礙了麥積山石窟的建設。
2.1 軍鎮制度的嚴厲管控
軍鎮制度萌芽于十六國前期,到十六國后期,軍鎮制度已成為一級地方行政單位。北魏在入主中原的過程中也實行了軍鎮制度,北魏軍鎮的鎮將名義上是國家派戍地方的軍事長官,并未明確規定其對于一地民政的權力,但是實際上鎮將已經成為一地最高的行政官員。不只如此,太武帝為了加強統治,賦予了鎮將更大的權力,《魏書·世祖紀》載:“其百工技巧,駐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在北魏政權相對穩定后,鎮將的職官性質愈向民政過渡。軍鎮的人事權不受中央的控制,其府僚可以由自己招募、征辟,軍鎮通過以品開府,鎮將對其下屬有絕對的任命權[4]。
北魏占領秦州之后,在秦州境內設上邽鎮和清水鎮,尤其上邽為秦州治所所在地,其盛衰影響到整個秦州。太武帝在上邽建立軍鎮,毫無疑問是把秦州作為征服與鎮壓的對象。在軍鎮管理之下,生活在秦州境內的人民無時無刻不在受到嚴厲的管理與監視,人們往往戰戰兢兢,用盡全力保全自身生命和財產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雖不會斷絕佛教信仰,但從事佛教建筑難免要承擔很大的風險。
2.2 班賞制度與賦稅制度的殘酷剝削
北魏早期無制度性俸祿,實行班賞制度,甚至在入主中原后這種制度依然持續到了孝文帝之前。北魏前期征伐較多,每攻克一地,必然掠奪當地財富以充軍資并犒賞將士,正所謂“以大眾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5]。班賞規模十分宏大,在太武帝時期達到了頂峰。班賞內容包括牲畜、人口、金銀錢財等。北魏在初步統一北方后,因戰事減少,班賞制度已很難實行,促使北魏初期的貪腐行為十分猖獗。《魏書·舊本魏書目錄序》載:“(官吏)爵而無祿,故吏多貪墨刑法峻急”。同時,太武帝還實行了九品混通制,此制以戶為單位收稅,規定每戶“調帛二匹,帛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6]。除此之外還頻頻加稅,《魏書·世祖紀》載:“(太武帝)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
太武帝時期,在全國實行的班賞制度和繁重的賦稅,以及官吏的殘暴貪腐行為,對于剛占領,并且時不時爆發戰亂的秦州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北魏鎮西將軍王斤就因橫征暴斂,使秦州和雍州等地數千家百姓難以承受,而南逃漢川。在殘酷的剝削之下,人們必然無心思也無力去支持麥積山石窟的修造,這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3 結語
從十六國早期到太武帝占領秦州,秦州處于諸多政權的爭奪和此起彼伏的起義之中,失去了安定的社會環境,經濟也遭受重大打擊。同時,頻繁的戰亂、徙民政策和北魏嚴酷的統治導致秦州人口大量流失,幸存的人們生存環境也很惡劣。也就是說,佛教建筑建設所需要的穩定的社會環境,長期的經濟支持,大量的具體勞動者和雄厚的人口基礎,在此時已然喪失。最終導致麥積山石窟在北魏太武帝前后進入了修造活動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