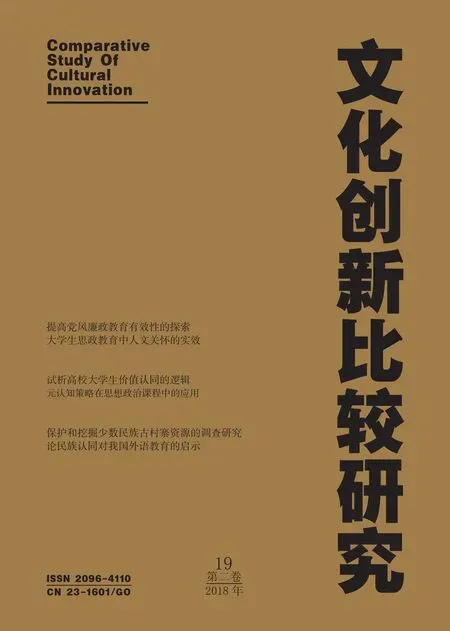“洞房”一詞詞義演變探究
王覓
(山東大學文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
1 “洞房”來源的傳說
關于“洞房”一詞的來源有兩種不同的神話傳說。一種是:遠古時期,陶唐氏堯稱王不久,因緣際遇與鹿仙女一見鐘情。他們在姑射仙洞完婚,傍晚結鸞之時,一簇神火突然出現在洞頂,耀眼奪目,光彩照人。從此,世間也就有了把新婚的房子稱作洞房,把新婚之夜稱作洞房花燭夜的習俗了。 另一種則是黃帝打敗蚩尤,建立部落聯盟,為制止群婚而發明一夫一妻制,在拜天地等活動之后,將夫妻二人送進事前準備好的洞穴(房)里,周圍壘起高墻,出入只留一個門,吃飯喝水由男女雙方家里親人送,長則三月,短則四十天,讓他們在洞里建立夫妻感情。此之為“洞房”。
2 “洞房”詞義演變
“洞房”一詞最早有文獻記載是在先秦時代。《楚辭·招魂》中即已提到了“洞房”二字——“姱容修態,絙洞房些[1]。”這里的“洞”之意與《洛陽伽藍記》中“崇門豐室,洞戶連房”的“洞”同,都是“深”的意思。因而,這里“洞房”是指幽深的內室,多指臥房、閨房。這也是“洞房”二字的最初意義,即本意。從造詞的角度,“洞房”是古人積累了一定的詞匯基礎上造的詞,是“洞”與“房”的結合,從造詞法上講,是用說明法造詞,為了說明“房”的“幽深”的性質特征。在實際使用中,幽深的內室也就多指臥房和閨房了。這樣的解釋在司馬相如的《長門賦》中得到印證:“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意思是說,明月高掛,孤獨地照著自己,我在洞房中消磨如此良夜。如其序所言,《長門賦》是陳皇后“別在長門宮”后,聞司馬相如之文才,所托“因于解悲愁之辭”。而且從這句話中,我們能感受到的是陳皇后被棄后的境遇和苦悶抑郁的心情。更何況是在“日黃昏而絕望兮,悵孤托于空堂”的等待之后。如此之凄涼,可見并不是新婚的場景。因此,無論從時間上還是情感上,這里的“洞房”二字都不是指“新人完婚的新房”,而應該是深邃的內室。實際上,在漢代,“洞房”這一含義僅用來指王宮貴族的富貴奢華住處,不用來指平民的房屋。
那么“洞房”一詞的現代所廣泛使用的意義——新婚夫婦的臥室——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呢?
魏晉南北朝時期,陸云的《登臺賦》中也出現了“洞房”一詞:“蒙紫庭之芳塵兮,駭洞房之回飚。”然而,在這里,“洞房”的意思是連接相通的房間。《梁書?徐勉傳》:“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事?”中也是此意。而在可能為魏晉時期成書的《黃庭內景經》中,“洞房”則是道教養生之道中所指的人體中的一個穴位,“洞房紫極靈門戶。”梁丘子注引《大洞經》:“兩眉直上……卻二寸為洞房。”雖然北周庾信《三和詠舞詩》曰:“洞房花燭明,舞馀雙燕輕”[2],有了花燭相襯,但此時的“洞房”仍然不具有現在所使用的詞匯意義。
“洞房”多種意義的產生是在唐代。在社會相對穩定,國力強盛,民風開放的情況下,艷情詩重新興起,“洞房”在艷情詩中常常用來指代男歡女愛場所,借以描寫閨情。例如“莫吹羌笛驚鄰里,不用琵琶喧洞房。”(喬知之《倡女行》);唐代佛教興盛,產生了很多與佛教有關的新詞匯,“洞房”也有了“僧人的山房”的意義,例如 “洞房隱深竹,清夜聞遙泉”(王維 《投道一師蘭若宿》)。直到“洞房”被用在中唐詩人朱慶馀的《近試上張籍水部》中:“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新房紅燭點著,通夜不滅,新婦一早起床,在紅燭光照中妝扮,等待天亮,好去堂前行禮。朱慶馀巧妙地用新婚之時的緊張期盼的心態隱晦代指面臨主考官應試的忐忑心情,指科舉考試對考生來說是像女孩兒出嫁一樣的終身大事。所以這里的“洞房”才是“新人完婚的臥室”,是從原意引申而來。
此后,“洞房”被更廣泛地使用,幾乎專指“新婚夫婦的臥室”了。宋人洪邁的《容齋隨筆》中的“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一句更是流傳后世。近代,洪深在《少奶奶的扇子》的第二幕中用的也是這個義項:“二十年以前,男女總要在入洞房以后,才說到愛情。”
雖然“新婚夫婦的臥室”義項在唐代產生,并被廣泛使用,但“幽深的內室”的意義,其生存空間并沒有消失。例如唐代沈亞之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急諫策》:“市言唯恐田園陂地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直到宋代,它的最初意義仍在被使用:“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晝夜樂?洞房記得初相遇》,柳永)。在柳永的詞中“洞房”一詞以閨房、臥房的意義被運用的現象屢見不鮮。并且這一詞義還出現在清代的《老殘游記》一書中:“搬來搬去,也很費事,不如竟到你洞房里去彈罷。”這也證明了詞義的演變更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也并非是新詞義代替舊詞義的簡單覆蓋與更迭,而是隨著歷史的發展一點一點滲透。詞語意義的選擇與使用仍然與日常生活的使用要求密切相關。
在名詞義“新婚夫婦的臥室”的基礎上,洞房產生了動詞詞義——完婚。《玉嬌梨》第十七回中“雖別有人家肯與我,卻又不中我意,自分今生斷無洞房日”即為例證。從造詞上講,是屬于引申法造詞,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有這一用法, 例如 “圍脖”、“知己”、“領袖”、“買賣”。詞匯的使用是靈活的,人們總是依據最方便的原則使用詞匯,這也是詞匯意義不斷變化的原因之一。
語言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的,在近代,為了描述的便捷,“洞房”又有了“窯洞”的意思。朱德曾經在《游南泥灣》中寫:“今辟新市場,洞房滿山腰”,描繪山下新開辟了市坊,山上建起了一排排嶄新的窯洞的景象,熱情謳歌延安大生產運動。然而這種詞義雖然產生的年代近晚,其用途卻并不廣泛,因而被接受程度也不高。“洞房”的主流意義仍然是“新婚夫婦的臥室”,多被人們運用在“鬧洞房”“洞房花燭夜”等詞句里。
3 結語
“洞房”一詞詞義從“幽深的內室”到“新婚夫婦的臥室”產生了詞義縮小的變化,其共同義素并沒有發生變化而是區別性義素發生了變化,仍然擁有“內室”這一含義。并且這種變化是在不斷交替的使用中經過了千年的緩慢演變,它的今義最終取代了原義。不僅僅是“洞房”一詞,無以計數的詞匯在歷經幾百年的滄海桑田之后詞義或是擴大,或是縮小,或是轉移,失去其原意保留下來。然而這也正是漢語的魅力:時代不斷發展演變,其語言文字永遠最富有生機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