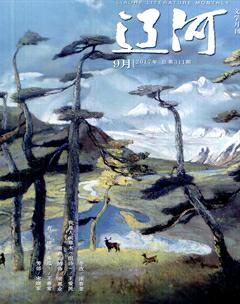鳥鳴與春風里的詩行
于成大
我與王愛民的相識要追溯到孩童時代。那時我們在同一所學校的同一個班級,同窗共讀。多年以后我一直在想:若當初我們的性別稍稍變動一下,會不會引出諸如同窗共讀后十八相送之類的橋段。
那時我們太小,縱使踮起腳尖,依然望不到詩歌,走進詩歌并為此歌哭憂歡,那是后來的事兒。
走出校園后,我們各奔東西、地北天南!愛民教書育人、采訪編報,我則踏上了流浪的旅途,飄忽不定、輾轉他鄉……所幸我們一直都沒有遠離詩歌,一直都在她的視野范圍內。我們時常以詩歌的方式遙相呼應、牽掛惦念。
愛民化筆為刀,以最完美的姿勢切入鄉土,他的詩歌除了那種來自土地的淡淡的土腥味兒外,更能感受到他的深沉、博大、厚重、質樸,愛民用筆筑一條泥土路,讓我們見識他的家園:推門,門檻開花/鈴鐺草搖小鈴鐺/像蟲鳴聲/滿眼綠……這就是他的“由蟲鳴和春風說了算”的“萬里山河”,樸素、親切、瑣碎得如母親的嘮叨、如父親的沉默。
愛民的鄉土詩,既非學院派那種對著一粒大米想象稻田的隔空打鳥式,又非鄉村遺老土坷垃一樣硬邦邦的化不開的理性,而是以小見大、言之有物。他熟悉并牢記那片土地上的一切,頂著高粱花在都市漂泊,于鋼鐵水泥瀝青的城市回望鄉間,依然心動于“天空下走著變舊的新人/還飄著花香的氣息”,“樹杈上冬眠的巢/一天天孵出個紅皮的太陽”……
他總是深入挖掘那片土地上的美好以及一種叫根的東西,不褪色的故園揮不去的鄉愁一次次凸顯了他對那片土地的深情及歸屬感……作為詩人的王愛民,就是“云朵里回來的一畝薄田”,他認真地栽種著他的懷念、牽掛、本真、熱愛,栽種著他青青黃黃、圓圓缺缺、歲歲年年的鄉村夢,聽憑某一刻“鞭炮在身體的某處關節回響”“身子里有一塊塊鐵鳴叫”,并跪拜——山是一座碑……
他用現代的犁鏵耕耘世襲的土地,相信語言,但不依賴語言,語言只是道具,而非劇情。我和愛民有些類似,都來自那片土地,那里有我們的根。進城許多年了,偶爾抖落一下衣衫,肯定還會掉落曾經的土粒,我們攜帶著故鄉漂泊,我們拒絕空中樓閣、拒絕“語言轟炸”,只醉心于地面上的寫作、低姿態為詩。我們習慣了土地上的一切,喜歡腳踏實地向前走。
從他的詩里,能讀出溫度和痛感,讀出對生與死、命運弄人的不斷追問與反思,繚繞著一縷縷叫做鄉愁的人間煙火的味道。
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個寫詩的人,就有多少種對詩歌的定義。無所謂誰高誰低、誰對誰錯,適合自己、得心應手就好。一首真正的好詩,與風格無關,與題材無關,與流派無關,與傳統亦或現代無關……愛民的詩,讓你見識了樸素的力量,讓你感受到鄉土的厚重!
黑土一樣本色的王愛民,露水一樣純凈的王愛民,溪流一樣明澈的王愛民,月亮一樣真摯的王愛民,他筆下的那方山水,讓人心動、向往、著迷、恍惚、心疼……
對于詩歌來說,王愛民本質上更接近鄉村,而非現代都市。這或許是愛民之幸——廣闊的鄉村,肥沃的土地,讓他的詩歌獲得了勃勃生機和無限遠景。
秋天的背影漸行漸遠,愛民身后的背景,依然是那片青翠欲滴、博大深沉的土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