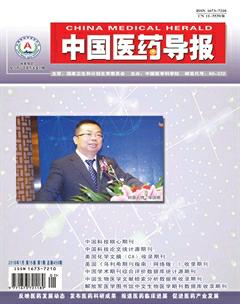不同中醫證型原發性肝癌患者中血小板參數的變化及意義
歐陽博慧+謝晴晴+唐健
[摘要] 目的 研究不同中醫證型原發性肝癌患者中血小板分布寬度(PDW)、血小板平均體積(MPV)水平的變化及意義。 方法 采用回顧性研究方法分析2013年1月~2016年12月廣西柳州市中醫醫院收治的155例原發性肝癌患者,根據中醫證型將其分為肝氣郁結、氣滯血瘀、濕熱聚毒、肝郁脾虛四組,比較各組PDW、MPV的差異。 結果 原發性肝癌各中醫證型組中肝氣郁結組PDW較其余組明顯升高(P < 0.01),MPV較其余組明顯降低(P < 0.01)。肝郁脾虛組PDW較氣滯血瘀組、濕熱聚毒組升高(P < 0.01),MPV較其余三組均增高(P < 0.01)。 結論 PDW和MPV可作為原發性肝癌肝氣郁結和肝郁脾虛證型的重要參考指標。
[關鍵詞] 原發性肝癌;中醫證型;血小板分布寬度;血小板平均體積
[中圖分類號] R25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8)01(a)-0102-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the changes and significances of 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PDW)and mean platelet volume (MPV)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yndrome classifi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data of 155 HCC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6 in Liu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ll patients was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ccording to TCM syndrome: stagnation of liver-Qi, qi-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 dampness and heat accumulation, stagnation of liver-Qi with deficiency of the spleen.The differences of PDW and MPV among different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level of PDW in stagnation of liver-Qi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groups (P < 0.01), however, the level of MPV in stagnation of liver-Qi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groups (P < 0.01). Compared with qi-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 and dampness and heat accumulation group, the level of PDW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stagnation of liver-Qi with deficiency of the spleen group(P < 0.01), and the level of MPV in the stagnation of liver-Qi with deficiency of the spleen group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hree groups (P < 0.01). Conclusion The PDW and MPV can be used as important reference indexes for HCC patients with stagnation of liver-Qi and syndrome of stagnation of liver-Qi with deficiency of the spleen in primary
[Key words] 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yndrome types;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Mean platelet volume
肝癌是一種常見的惡性腫瘤,每年我國新發肝癌人數約占全球新發人數的一半[1],已成為常見惡性腫瘤第4位及腫瘤致死病因第3位[2]。中醫沒有肝癌病名,其發生病機則是本虛標實,正氣不足,臟腑功能失調,氣滯血瘀、痰凝毒聚[3]。“證候”即證的外候,是指特定證所表現的、具有內在聯系的癥狀、體征等全部證據,是辨證論治的依據[4]。中西醫結合治療方法以辨證論治為核心,在控制癌瘤發展和轉移、縮小癌瘤體積及減毒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治療效果,成為原發性肝癌綜合治療的重要手段之一[5]。然而,原發性肝癌的中醫辨證分型尚無明確的統一標準,臨床各醫家對此存在爭議。近年來血小板分布寬度(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PDW)、血小板體積(mean platelet volume,MPV)等血小板參數檢測指標已引起重視。PDW是反映血液內血小板容積變異的參數,以測得的血小板體積大小的變異系數表示。MPV用于判斷骨髓造血功能變化、血小板活化及某些疾病的診斷治療。有研究表明,肝癌患者血小板參數變化明顯,且與腫瘤大小及分期有關[6]。因此,本研究對肝癌中醫證候類型與PDW、MPV水平的變化進行研究,以期將中醫證侯與西醫客觀指標相結合,為原發性肝癌的辯證論治提供依據。endprint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2013年1月~2016年12月于廣西柳州市中醫醫院就診的住院患者155例,其中男139例,女16例;年齡21~88歲,平均(63.10±4.80)歲;發病高峰期為55~72歲;既往有乙肝病史者137例,占88.38%;根據我國肝癌分期標準[7],Ⅰ、Ⅱ期共31例,占20.0%,Ⅲ、Ⅳ期共124例,占80.00%;在Ⅰ、Ⅱ期原發性肝癌患者中,肝氣郁結證28例(18.06%),氣滯血瘀證1例(0.65%),肝郁脾虛證2例(1.29%),Ⅲ、Ⅳ期患者中肝郁脾虛證47例(30.32%),濕熱聚毒證41例(26.45%),氣滯血瘀證32例(20.65%),肝氣郁結證4例(2.58%)。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 西醫診斷標準根據《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7年版)》[2]及2004年版《原發性肝癌的臨床診斷與分期標準》[7]。
1.2.2 中醫證候診斷標準 本研究的中醫證候診斷參照《中醫內科學》[8]肝癌的證候分型及《原發性肝癌辨證分型與免疫指標相關性的研究》[9],將常見的肝癌證型分為四組,即:肝氣郁結組、氣滯血瘀組、濕熱聚毒組、肝郁脾虛組。
1.3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符合原發性肝癌的診斷標準,且在住院期間進行血常規檢測且結果可測出,入組前1個月未進行放化療及介入治療的患者。排除標準:妊娠、生殖系胚胎源性腫瘤、活動性肝病及轉移性肝癌,合并有其他腫瘤;有明顯的兼夾證者。
1.4 儀器及檢測方法
選取患者入院后第一次檢測的相關指標,所有患者采集清晨空腹靜脈血2 mL,將其置于EDTA-2K抗凝管內,進行抗凝之后,使用日本Sysmex公司的XE-2100全自動血液分析儀對血液進行檢驗,采用的溶血素、稀釋液、質控液以及清洗液等,均為該血液分析儀原裝配套的試劑。
1.5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采用SPSS19.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統計檢驗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S-N-K(Student Newman Keuls)法。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經方差分析,四組PDW、MPV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組間兩兩比較結果顯示,氣滯血瘀組、濕熱聚毒組、肝郁脾虛組PDW水平明顯低于肝氣郁結組(P < 0.05),MPV水平明顯高于肝氣郁結組(P < 0.05);且氣滯血瘀組、濕熱聚毒組PDW、MPV水平均明顯低于肝郁脾虛組(P < 0.05)。見表1。
3 討論
對于肝癌的病因、病機及治療方法,亦有大量古書記載。清代著名醫家黃元御在《四圣心源》中提出五臟六腑之病緣起發生莫不與肝臟有關,所以在其書中直接將肝冠以“五臟之賊”“百病之長”[10]。中醫認為肝能生血,受藏于肝之血復行于周身,“肝生血氣”之說始見于《內經》。肝臟具有藏血功能,“肝藏之血”時血氣化生的物質基礎,若肝藏血功能失常,營養物質不能合成儲存,并根具需要交換至血液后及時輸送至全身,則可出現肝血虛證。而脾是人體氣血生化之源,脾為后天之本;而病理情況下,任何影響脾胃功能的因素均可導致脾失運化,進而導致其他臟腑功能障礙。肝主疏泄和脾主運化功能之間的相互促進,以及肝藏血與脾統血之間的相互配合,共同在人體的消化吸收、氣血運行及水液代謝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11]。故后天之本脾胃虛弱,失于健運,胃失和降,濕邪內聚,氣滯血瘀,濕邪瘀毒結于肝臟而發為肝癌;再者憂思傷脾,所想所愿不得志,經絡不通,則痰瘀積聚成塊而發肝癌[3]。肝脾相關理論作為五臟相關學說的子系統,強調肝脾雖有各自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特點,但兩者在生理上相互為用、制中有生,在病理上相互傳變,這種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功能協調,即被稱為肝脾調和,若肝脾任何一臟的偏盛偏衰,出現木乘土,土侮木等各種乘侮表現,統稱為肝脾失調[12]。
肝癌的形成受多種因素影響,單一的治療往往獲效甚微或者難于持續,綜合治療已成為共識,目前針對肝癌本身所采用的一些化療、放療療效大多差強人意,即使可手術根治的肝癌術后往往伴有腫瘤復發與轉移的危險,現今肝癌患者絕大多數都接受中醫藥治療,或在姑息性治療中配合中醫藥治療,中醫藥逐漸成為了肝癌的重要治療手段之一[3]。經過長期的臨床觀察,本院就診原發性肝癌患者以肝氣郁結、氣滯血瘀、濕熱聚毒、肝郁脾虛共四個證型多見,與《中醫內科學》所述較為一致,故以此四個證型進行研究。MPV是檢測骨髓中巨核細胞增生代謝和血小板生成的指標,與血小板的超微結構、酶活性和功能狀態相關,一般體積較大的 PLT 代謝更活躍、酶活性更強。PDW是反應血小板均一性差異的參數,可反映血小板的年齡與結構[13]。PDW、MPV是臨床上患者入院必查的血常規中的項目,該項目簡單快捷,收費低廉,如果其與中醫證型存在某種關系,利用這種關系輔助中醫辨證,將大大提高辨證的準確性。
本研究結果表明,四種證型的原發性肝癌患者PDW、MPV水平分布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其中肝氣郁結證型組、肝郁脾虛組的PDW、MPV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1)。且肝氣郁結組PDW明顯高于其余各組,MPV明顯低于各組;肝郁脾虛組較氣滯血瘀組及濕熱聚毒組的PDW、MPV同時增高。可見,PDW、MPV對肝氣郁結和肝郁脾虛的辨證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可提高其臨床中醫辨證的準確率。
肝氣郁結組的現象從西醫客觀指標分析,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第一,原發性肝癌患者肝細胞受損,血小板生成素TPO合成不足,血小板減低。而TPO幾乎是由肝細胞專供,是調節血小板生成的關鍵生長因子,可調節骨髓巨核細胞系統的分化成熟,刺激巨核細胞產生血小板,是刺激巨核細胞血小板生成的主要因素[14]。第二,乙肝病毒具有的泛嗜性,肝炎病毒可抑制骨髓:研究發現肝炎病毒可以直接作用于骨髓造血干細胞,或通過病毒介導的免疫異常抑制骨髓造血干細胞的產生,通過抑制激素的活性從而達到殺傷骨髓造血干細胞的功能侵犯骨髓造血功能[15],引起單核-巨噬細胞系統功能減弱,抑制巨核細胞增殖,新生血小板減少[16]。第三,患者呈現出肝功能受損的情況后,會使得自身內毒素清除能力呈現出一定程度降低,在內毒素誘導作用下,使得血小板出現了激活以及凝集等情況,進而使得血小板表現出破壞的情況[17],當血小板不斷的被激活,體內的活性物質被完全釋放,使得致密顆粒衰竭,造成患者的血小板體積發生縮小,儲備的功能也逐漸下降[18]。第四,血小板凋亡會使細胞膜形成囊泡,釋放出血小板微顆粒。微顆粒釋放使血小板皺縮、體積變小是血小板凋亡形態學上的表現[19]。因此,肝癌初期新生血小板減少,陳舊血小板的逐漸凋亡(皺縮),在外周血象的表現即為:少量新生血小板(體積較大)、部分成熟血小板及多量陳舊、凋亡血小板(體積較成熟血小板更小)同時存在,使得MPV明顯減低,PDW增高。endprint
隨著疾病發展,脾大、脾亢、脾臟滯留對血小板產生了進一步的影響,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被阻滯的血小板生成時間降低,導致血小板被吞噬和破壞增加,與此同時脾臟可產生血小板病理性抗體[13],患者循環中的免疫復合物水平及血小板綁定的免疫球蛋白水平升高,促使被吸附了免疫復合物的血小板在脾臟內被單核巨噬細胞破壞[20]。其次,肝癌患者蛋白生成減少,出現低蛋白血癥,當伴脾功能亢進時,網狀內皮系統血小板破壞增加,出現代償反應,骨髓巨核細胞增生,形成“應激反應性大血小板”[15]。因而,在脾功能亢進及全身免疫狀態改變和脾臟的滯留破壞等多種因素的共同參與下,機體內血小板的破壞加速、壽命縮短刺激了巨核細胞增值分化,骨髓代償性的釋放年青血小板,血小板更新增加[21]。年青血小板體積較大,細胞器成分豐富,因此血小板的更新增加繼而使MPV增高;體積增大的大量血小板導致其均一性下降,從而又使 PDW 增高,但增高幅度小于血小板降低幅度[22]。另一方面,在原發性肝癌患者的疾病進程中,對于血小板活化標志物水平的研究,有資料顯示,臨床分期、轉移與否是肝癌患者外周血、血小板活化標志物水平的影響因素,中、晚期患者外周血血小板活化標志物水平明顯高于早期[23],活化后的血小板體積增大,MPV增大。綜上所述,臨床上即出現肝癌晚期即肝郁脾虛證型組較氣滯血瘀組、濕熱聚毒組的MPV、PDW均增大的現象。本研究結果基本符合王榕平等[9]研究發現的,肝癌從肝氣郁結——肝郁脾虛——死亡是一個逐漸進展的過程。
通過此次對血小板參數水平的變化與原發性肝癌中醫證型的研究發現,血小板參數(PDW、MPV)的水平變化與中醫證型中的肝氣郁結證及肝郁脾虛證,具有較高的吻合度,因此PDW明顯增高及MPV的明顯降低,可作為原發性肝癌肝氣郁結證的重要參考指標,PDW、MPV同時增高對肝郁脾虛證型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參考文獻]
[1] 陳建國.中國肝癌發病趨勢和一級預防[J].臨床肝膽病雜志,2012,28(4):256-260.
[2]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醫政醫管局.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7年版)[J].中華消化外科雜志,2017,16(7):635-647.
[3] 張詩軍,陳燕,孫保國,等.肝癌的脾虛內環境本質研究[J].中華中醫藥學刊,2017,35(1):7-9.
[4] 占義平,凌昌全.原發性肝癌中醫證候研究概述[J].中醫雜志,2017,58(2):167-170.
[5] 宋慧嫻,喬飛,邵銘.中醫藥治療原發性肝癌的研究進展[J].臨床肝膽病雜志,2016,32(1):174-177.
[6] 丁勝楠,楊偉民,牛俊奇.肝癌合并肝硬化患者血小板參數的變化及影響因素[J].臨床肝膽病雜志, 2014,30(6):556-559.
[7] 楊秉輝,夏景林.原發性肝癌的臨床診斷與分期標準[J].中華肝臟病雜志,2001,9(6):324.
[8] 吳勉華,王新月.中醫內科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2:96-105.
[9] 王榕平,吳丹紅,金源,等.原發性肝癌辨證分型與免疫指標相關性的研究[J].福建中醫藥,2001(2):4-5.
[10] 潘立文,王曉明.“肝為五臟之賊”的臨床應用探析[J].中醫藥導報,2017,(12):118-123.
[11] 陳啟亮,唐東昕,龍奉璽.“見肝之病,知肝傳脾”在肝癌防治中的運用[J].中醫學報,2016,23(12):1833-1835.
[12] 彭學錢,王三虎.從“肝脾相關”論治肝癌并發低血糖[J].中醫學報,2016,31(12):1826-1829.
[13] 秦啟燕.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血小板參數檢測的臨床分析[J].現代實用醫學,2014,26(3):290-291.
[14] 趙西平.慢性肝病患者血小板減少發生機制及治療[J].臨床血液學雜志,2016,29(1):11-15.
[15] 王國有,梁小利,拓紅曉,等.凝血功能及血小板相關參數檢測對肝病診治的臨床價值[J].中國醫學工程,2016, 24(6):40-42.
[16] 葉潤清.HBV感染血小板行為特征與肝臟病變的相關性研究[D]:廣州:廣州醫學院,2012.
[17] 周敏,潘寧.血小板參數聯合D-二聚體檢測在肝硬化患者中的效果分析[J].中西醫結合心血管病電子雜志,2017,5(5):23.
[18] 潘增福.肝硬化患者凝血指標與血小板參數檢測的臨床價值[J].中國醫藥指南,2017,15(7):144-145.
[19] 趙麗麗,阮長耿,戴克勝.血小板凋亡的最新研究進展[J].中華血液學雜志,2012,33(8):687-689.
[20] 張紅勝,張敏.血清RBP、凝血四項和血小板指標檢測在重癥肝病輔助診斷中的應用[J].國際檢驗醫學雜志,2016,37(17):2413-2415.
[21] 彭碧,陳勇.巨核細胞與血小板參數在血小板減少性疾病中的應用[J].臨床和實驗醫學雜志,2012,11(12):910-911,913.
[22] 侯會香.肝硬化患者凝血酶原時間與血小板檢驗的臨床價值[J].臨床合理用藥雜志,2015,8(26):86-87
[23] 陳艷,王熙才,伍治平,等.肝癌患者外周血血小板活化標志物檢測及臨床意義[J].中華腫瘤防治雜志, 2006, 13(18):1412-1415.
(收稿日期:2017-09-23 本文編輯:李雅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