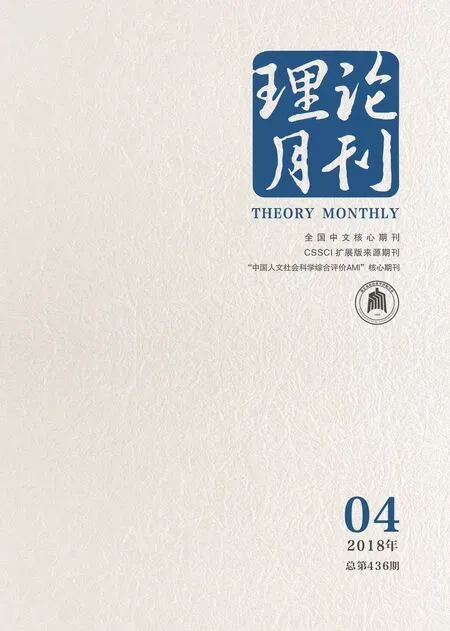文藝學反本質主義的限度與出路
——兼論文學本質的存在方式
□劉連杰
(云南師范大學 美術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近十多年來,反本質主義成為國內文藝學研究的前沿話語,本質主義受到普遍質疑。所謂本質主義,原是西方后現代主義者對傳統(tǒng)形而上學認知方式的追加命名,指所有的本質論。引入中國后,這一概念的內涵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它不反對所有的本質論,而是反對特定的本質論,即“僵化的、非歷史的、形而上的理解文學本質的理論和方法”[1](p12-23)。因此,“本質主義”可以說是中國文藝學界的理論創(chuàng)新,但這一理論創(chuàng)新也使本質主義的認定成了問題。什么樣的本質論才是本質主義?中國當前文藝學研究中存不存在本質主義?本質主義是不是一定不好?學者們莫衷一是,引發(fā)了諸多論爭,其中也不乏錯位與混亂。有鑒于此,在反本質主義文藝學的話語邏輯中理清“本質主義”的內涵,遠比含糊地進入論爭要有意義得多。
一、反本質主義的限度
當前,文藝學界對本質主義論爭的諸多混亂,實源于陶東風教授的一個邏輯錯位:將僵化的思維方式等同于實體本質論,將實體本質論等同于普遍本質論。首先,他將本質主義界定為“一種僵化、封閉、獨斷的思維方式與知識生產模式”[2](p97-105)。這種明顯貶義的情緒化表述自然使本質主義成為眾矢之的,也為反本質主義贏得了最大限度地學術認可空間。但回過頭來,很多學者也發(fā)現,這種本質主義只不過是一個虛構的理論前提,在現實中難以找到對應的理論。就在陶東風教授大張旗鼓地反本質主義之時,童慶炳教授卻認為“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的戰(zhàn)爭其實早就已經結束”。如果更進一步,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本質主義從來就沒有存在過,因為即使是眾多學者公認的本質主義肇始者柏拉圖,也不能和“僵化、封閉、獨斷的思維方式”直接畫等號。因此,這一設定是沒有意義的,也不可能形成論爭。其次,陶東風教授所謂的本質主義也表示實體本質論,它相信文學本質就像地下的石頭一樣客觀存在著,否認本質是社會歷史的建構。這種本質論盡管在歷史上確實存在過,但也早已被歷史所否定,正如童慶炳教授所說,“我不認為今天的思想界仍然抱著本質主義的思維方法,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的戰(zhàn)爭其實早就已經結束,已經沒有了懸念。”[3](p6-11)然而,奇怪的是,既然如此,為什么很多學者還要對反本質主義保持警惕呢?原來,陶東風教授對本質主義還有第三個界定,即普遍本質論,它相信文學本質應該具有普遍性,不甘于文學本質只是“歷史化和地方化的言語建構”[1](p12-23)。對于此種本質主義,很多學者的態(tài)度是矛盾的,他們一方面看到了文學本質言說受到歷史語境影響的事實,另一方面又覺得一旦消解文學本質的普遍性,就難以進行理論的建構,因此,他們一方面堅持反本質主義,另一方面又認為“反本質主義不能走向極端”[3](p6-11)。這固然不失為一種辯證的看法,但問題在于,反本質主義的限度究竟應該如何確定呢?
對此,我們應該將文學存不存在普遍本質與文學需不需要普遍本質區(qū)分開來,文學不存在普遍本質不等于文學不需要普遍本質,文學不存在作為實體性構成要素的普遍本質不等于文學不需要功能性的普遍本質,正如上帝不存在不等于我們不需要上帝。盡管任何文學本質論最終都難逃被歷史化的命運,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要求普遍性的權利。基于這一認識,我們有必要改變提問的方式,不應該問: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文學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質,某一歷史時期對文學本質的界定是否能夠得到其他歷史時期的完全認同,而應該問:一種文學本質論的建構是否應該考慮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文學,并具有解釋和應對它們的能力。反本質主義認為,所有文學本質論都是歷史化與地方化的建構,是在特定歷史語境中形成的對文學的理解,即使作為文藝學研究對象的“文學”本身也是一種建構,是處于特定歷史語境中的人根據自身的文學標準從一大堆文獻中圈出來的。如果從歷史事實出發(fā),這大體上是不錯的。然而,問題在于,不同歷史時期對文學的認定有延續(xù)性嗎?如果每個歷史時期的學者只是完全根據自己的標準來認定文學,那豈不是每個歷史時期都只有自己稱為文學的東西,我們又如何保證自己同其他歷史時期的學者是在探討同一話題呢?它們會不會只是同名卻完全不同的東西呢?換一個角度來說,如果每一歷史時期的文學本質論只滿足于歷史化與地方化的建構,不認為自身能比歷史上的其他文學本質論更合理,或者暫時用本質主義的表述,更接近“文學本身”,不追求自身的普遍性,把自己完全封閉于自身的歷史語境中,我們又如何保證自己是在延續(xù)其他歷史時期的學者所探討的文學本質論話題呢?我們又如何有資格去評判其他歷史時期文學本質論的意義特別是局限呢?可見,完全否定“文學的共性”是行不通的。
其實,反本質主義存在著兩個錯誤的預設,一是認為任何建構都不能也不想克服自身的歷史局限,即使有其他歷史語境中的建構存在,也只會強化我對歷史性和語境性的信念,而不會影響我在當下歷史語境中的建構。二是認為“文學的共性”只能是非建構物,任何處于特定歷史語境中的人都不可能建構出所有歷史語境的人都可能認同的“文學的共性”。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陶東風教授曾表示,伽達默爾“視野融合”的觀點非常值得我們借鑒,認為“我們的這個立場、前理解和信念并不是拒絕交往和對話的,也不是不可能在交往對話中修正的。”[1](p12-23但遺憾的是,他卻沒有能夠將這一觀點貫徹到底。怎么樣才能產生對話,怎么樣才能視野融合?埋頭于當下歷史語境的建構,而不顧其他歷史語境的建構,滿足于各有各的合理性,各有各的局限性,能夠產生真正的對話嗎?所謂視野融合,當然是讓當下的歷史語境融合其他的歷史語境,盡量克服自身的歷史局限,以便獲得更大的合理性。以文學本身來說,盡管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同名異指的現象,但我們相信自己的文學觀比古人更加合理,因為我們相信我們了解古人的歷史語境,我們了解古人如此界定文學的原因與局限,這種了解不僅僅是知識,它也為我們當下對文學的界定提供了經驗與教訓。我們對文學的界定不只是符合當下的歷史語境,而且也深入到了古人的歷史語境中,如果古人了解我們如此界定文學的理由,相信他也一定會認同。也許我們永遠不能達到真理,但我們永遠走在真理的途中,可能我們會犯錯,可能我們的文學觀并不比古人的更加合理,但一旦我們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會重建我們的文學觀,直到我們認為它比古人的更加合理為止,因為即使我們不擁有真理,至少也擁有糾正錯誤,走向真理的能力。也許后現代主義者會認為這是真理的宏大敘事,但如果不堅信這一點,我們還能繼續(xù)走向未來嗎?如果我們不相信了解的知識越多,同等條件下,我們對文學的界定就能更加合理,我們還能有借鑒歷史的理由嗎?
反本質主義強調知識生產的歷史語境性,但其實,人們越是處于歷史語境中,就越是意識不到歷史語境本身,過于強調歷史語境,將之主題化,反而是處于歷史語境之外了。這是歷史語境的悖論。我覺得,陶東風教授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正是陷入了這一悖論之中。它致力于“用知識社會學的方法揭示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社會歷史條件”[4](p12),認為“教材的使命是盡可能客觀地介紹、梳理知識共同體所公認(或者大致公認)的歷史上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學觀,而不必要提供自己的文學觀。”[1](p12-23)這種“盡可能客觀”的努力實際上就是對自身所處歷史語境的遺忘,如果文學理論知識生產是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進行的,那么對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歷史語境的“揭示”行為也必然要處于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它不可能“客觀”,必然會帶有自身歷史語境的色彩,并用“自己的文學觀”進行評價。一部完全客觀的文學理論教材只能是資料匯編,難以獲得應有的價值。
反本質主義的問題還在于,它認為如果我們不處于歷史語境之外,就只能局限于自身的歷史語境之中。但伽達默爾視野融合的理論正是在告訴我們,其他歷史語境的存在可以盡可能地克服我們自身歷史語境的缺陷,視野融合之后,我們既不處于其他歷史語境之中,也不再完全處于自身的歷史語境之中,而是處于一個融合兩者的更大視野之中。歷史發(fā)展的各個不同時期不是完全孤立的并列,而是視野的不斷擴大,正是它保證了我們可以獲得比前人更多的合理性,盡管后人還會獲得比我們更大的合理性。因此,盡管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觀確實處于自身的歷史語境之中,但這些歷史語境之間是有延續(xù)性的,正是這種延續(xù)性,才不至于使這些文學觀僅僅成為歷史語境的附庸,它在不斷揭示著以前文學觀的局限,并使后人有權利評價以前的文學觀,而不只是“盡可能客觀地介紹”。
反本質主義強調歷史語境,其意義不在于使我們成為歷史語境的附庸,而在于提醒我們自身歷史語境的局限,并盡可能地通過對過去歷史語境的融合來克服這一局限。因此,反本質主義只能是反思性的本質主義,不應該將兩者對立起來。本質主義也不是“僵化、封閉、獨斷的思維方式與知識生產模式”,而是不斷克服自身的歷史局限,試圖在更大視野中對文學本質進行更合理界定的思維方式與知識生產模式。
二、建構主義和關系主義的意義與局限
當前的中國文藝學界,完全反對文學本質論的學者還不多,反本質主義論爭各方的共識在于,文學不是不可以具有本質,關鍵是如何理解“本質”概念。對此,很多學者給出了極具創(chuàng)造性的意見,有代表性、且爭議比較大的當屬陶東風教授的建構主義和南帆教授的關系主義。實際上,任何一種理論的出場,都不能只是被簡單地肯定,或者否定,它們都為思考文學本質觀提供了新的視野,這些新的視野應該被更新的研究所接納,使更新的研究在更寬廣的視野中獲得更大的合理性。更新的研究不只是強化新的歷史語境或個人語境,也不只是在眾多理論中添加一種只能與它們并列的理論,而是應該融合它們,在自圓其說的同時發(fā)展它們,使它們所具有的局部真理在更大的真理中得到定位,這是研究得以延續(xù)、具有歷史的前提。
建構主義認為,任何文學本質論都是歷史化與地方化的建構,文學本質不可能被一勞永逸地獲得,它必然要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而不斷重建。從歷史事實來看,這一觀點有其合理性。但新的建構的歷史語境不只是特定歷史階段的歷史語境,而且也包括過去的所有歷史語境,因為新的建構不能無視過去的歷史,過去的歷史同樣在新的建構的視野之中。對此,德國哲學家胡塞爾對時間問題的研究值得我們重視。他認為,時間并不是由各個孤立的時間點構成,“現在”通過“持存”和“預存”的方式將“過去”和“未來”包含在自身中,“現在”不是單純的瞬間,而是整個時間的縮影,是包含“過去”與“未來”的永恒。同樣,文學本質建構的歷史語境,也不只是“現在”的歷史語境,而是包含“過去”與“未來”的歷史語境,也就是說,文學本質的建構不能只是迎合當前的時代需要和文學實踐,它也要回應過去的各種本質論,并準備好應對將來可能會有的挑戰(zhàn)。只有這樣,它才能從過去和未來汲取力量,克服自身的歷史局限性,引領當下的文學實踐。反過來說,如果一種文學本質論僅僅停留于自身,不想或不能回應過去和未來,那它就還不成熟。因此,成熟的文學本質論不可能只滿足于“符合使用者的價值訴求、利益以及愿望”,甘于“自己選擇的一套理論詞匯本身是有缺憾的,它并不比別人選擇的理論、術語和詞匯更接近某個文學的‘實體’”,它必然會要求成為普遍和永恒,“聲稱自己是唯一正確、合法的本質言說”,甚至“絕對真理”,我們不能說“這種言說本質的程序就是非正義的”[1](p12-23)。固然,某一文學本質論可能會在未來或現在就遭到質疑,但這一質疑不能一意孤行地僅僅以歷史語境的不同為由,而應該以它能夠接受的方式進行,并準備好應對可能來自它的回應。
新的文學本質論建構必須承認歷史語境對文學本質論的影響,承認文學本質論是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而不斷重建的,但它不能把自身封閉于當下的歷史語境之中,必須強調自身向過去和未來歷史語境的開放。歷史語境也不能粗暴地直接干預文學本質論建構,而只能間接地通過文學研究內部規(guī)律起作用,只講外部語境而不講內部規(guī)律就不會有發(fā)展,而只能有難以預料的變化,最終必將導致不可知論。當然,文學本質論發(fā)展的內部規(guī)律并非是因果性的,當下的文學本質論不能決定未來的文學本質論,但未來的文學本質論應該在當下的文學本質論的預料之中。正如今天的我不能決定明天的我會是什么樣子,但明天的我必然能夠在今天的我中找到解釋,因為明天的我畢竟還是我,而不可能是與今天的我毫無關系的另一個人。建構主義切斷了不同歷史語境之間的聯(lián)系,而我們正是要恢復這一聯(lián)系。
與建構主義只是提供一種文學本質論建構的理論設想相比,南帆教授關系主義文學本質論的可操作性則要強得多。他認為:“一個事物的特征不是取決于自身,而是取決于它與另一個事物的比較,取決于‘他者’。”文學本質“與其說來自本質的概括,不如說來自相互的衡量和比較——形象來自文學與哲學的相互衡量和比較,人物性格來自文學與歷史學的相互衡量和比較,虛構來自文學與自然科學的相互衡量和比較,生動的情節(jié)來自文學與社會學的相互衡量和比較,特殊的語言來自文學與新聞的相互衡量和比較,如此等等。我們論證什么是文學的時候,事實上包含了諸多潛臺詞的展開:文學不是新聞,不是歷史學,不是哲學,不是自然科學……”[5](4-13)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未必不是文學在各種紛繁復雜的事物中自我確認的一種方式,它能夠便捷地將文學從其他事物中區(qū)分出來,回歸自身。但這種否定性的排除法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方法,只是在文學研究進入迷茫狀態(tài)時的一種臨時性策略。如果將之常規(guī)化,如果過分強調文學與其他文化現象的區(qū)分,那么,隨著文學周圍文化相對物的不斷增多,文學在越來越精確的同時,也會走進一條越來越窄的死胡同。實際上,文學在以一種方式排除其他文化現象時,也在以另一種方式整合其他文化現象。也就是說,盡管文學在某種意義上不是新聞、不是歷史、不是哲學、不是自然科學,但它同時也在另一種意義上將新聞、歷史、哲學、自然科學整合進自身之中。其他文化現象不僅是文學自我定位的參照系,而且也是文學自我豐富的現實資源,隨著文學周圍文化相對物的不斷增多,文學不是越來越狹窄,而是越來越豐富。很多時候,文學的發(fā)展恰恰源于從那些文化相對物中獲得的靈感,例如,清末民初新聞的出現,并未讓文學急于與之撇清關系,反而借助它來進行文學創(chuàng)新,發(fā)展出新聞體小說、報章體小說,強調文學的當下關切、宣傳作用與閱讀效率。因此,新聞的出現對于文學的意義不只是“文學”概念內涵的增加和外延的縮小,而且也為文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從此文學可以在一個更加寬廣的視野中進行了,不管是嚴詞拒絕,還是欣然接受,這一新視野都已經成為文學無法回避的一個維度。鑒于此,文學研究不應只關注文學與其他文化現象的區(qū)分,而更應關注文學整合其他文化現象的方式,即文學何以能夠整合其他文化現象但卻沒有成為其他文化現象,我們正是將此稱為文學的本質。
總體上講,南帆教授的關系主義是反本質論的,盡管他的表述比較謹慎,語氣也比較平和,認為關系主義只是“在本質主義收割過的田地里再次耕耘”,并表示:“即使冒著被奚落為‘保守分子’的危險,我仍然必須有限度地承認‘本質主義’的合理性。”[5](p4-13)當然,這里所說的本質主義與陶東風教授不同,指所有的本質論。盡管如此,他卻沒有能夠說明,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處理本質主義與關系主義之間的關系,在具體表述中,他甚至還將本質主義與關系主義對立起來,認為本質主義“所謂的文學公式如果不是一個幻覺,也將是某種大而無當的空話。”[5](p4-13)我覺得,南帆教授之所以會對文學本質有如此看法,是由于他對“本質”的誤解,或者說,是由于他錯誤的本質觀。在他看來,所謂文學本質,就是所有文學現象所共有的因素,是“從原始神話至后現代小說之間的公約數”[5](p4-13)。正如他所說,文學尚未完結,我們尚不知未來還會出現什么樣的文學,怎么可能找到它們的公約數呢?就算在現有的文學中找到了一個公約數,它又怎么能夠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文學負責呢?我們還可以再補充一點,就算在現有的文學中找到了一個公約數,我們又怎么能保證它就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本質呢?鑒于此,我們必須重新回答“什么是本質”這一問題,重建人們的本質觀。文學本質不是所有文學的公約數,而是后來的文學必須回應先前的文學,從先前的文學中找到發(fā)展出后來的文學的新維度,以保證所有稱為文學的東西之間的延續(xù)性,使文學能夠具有一個不斷發(fā)展的歷史。或者說,本質不是一個建構型的概念,而是一個范導型的概念,本質不是具體文學作品的實際組成部分,我們不應該到具體的文學作品中去尋找文學本質,更不應該將本質視為所有文學作品的公約數,它只是所有稱為文學作品的東西得以被組織起來的方式。
三、文學本質的存在方式
鑒于當前文藝學反本質主義論爭的錯位和自說自話,學界更為需要的不是建構出一套具體的文學本質論,而是弄清“什么是本質”這一問題,即文學本質的存在方式,重建人們的文學本質觀。我們無意回避建構主義和關系主義所提出的問題,而是將它們作為文學本質觀重建的視野加以接受,并力求以它們能夠接受的方式做出回應。我們承認建構主義認為文學本質論建構具有歷史語境的觀點,但不同意這一歷史語境僅僅封閉于當下,而是向著過去和未來開放的。雖然我們處于某個具體的歷史語境中,但我們看到的仍然是從某個維度組織起來的文學整體,而不會是處于各不相同的歷史階段并具有各不相同的本質的文學碎片。不同歷史語境的實際存在,不會強化我們對當下歷史語境的依附,而只會使我們意識到當下歷史語境的局限,并盡可能通過對不同歷史語境的融合來克服這一局限,重建文學整體。文學整體盡管不可能最終獲得普遍永恒的本質,但它卻始終要求并堅定地走在通向普遍永恒的本質的途中。我們也承認關系主義所說的文化相對物對文學本質論的影響,但不把它們僅僅作為自我定位的參照系,而是作為文學必須對之做出回應的視野,文化相對物的增多不會使文學之路越來越狹窄,而是越來越寬廣。總之,建構主義與關系主義以及各種其他文學本質觀的提出,并不會讓我們的文學本質論越來越準確,追求準確的文學本質觀是一條不歸路,它使文學不斷純化,也不斷貧瘠化,而是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更多可以回應的視野,它們可以幫助我們不斷克服自身視野的局限性,并獲得更大的合理性。
總的來講,文學本質觀的重建必須強調文學發(fā)展的延續(xù)性,并在這一延續(xù)中不斷吸收不同歷史語境的合理成分和文化相對物中的異質因素,來豐富自身、擴展自身。文學,從它作為“文獻”出現的那一天起,就已經具有了可以無限發(fā)揮的延續(xù)維度,成了一切后來文學都不能回避的源頭,后來文學只有通過它才能被認定為文學,只能通過將它放入一個更大的視野中來發(fā)展文學。沒有任何作家能夠無視文學傳統(tǒng)而進行創(chuàng)作,也沒有任何文學能夠無須文學傳統(tǒng)就被認定為文學。文學的發(fā)展不是對過去文學的隨意變化,也不是在文學史中添加一些無法確定其與過去文學是否有關系的異質因素,而是在過去文學中發(fā)現人們未曾發(fā)現的意義或維度,并把它開展出來,否則我們就沒有理由將這些各不相同的東西歸入一個可以共同稱為“文學”的東西中。換句話說,對于“什么是文學”,不是一個人完全封閉于自己當下的歷史語境或個人語境就能思考的問題,他必須考慮先前的文學傳統(tǒng)。如果世界上第一個人寫出了稱為文學的東西,哪怕這種稱為文學的東西只能表示文獻的意思,后來的人在創(chuàng)作文學時,也不能無視這一表示文獻的文學傳統(tǒng),他必須接受這一傳統(tǒng),接受這一傳統(tǒng)得以產生的歷史語境,并利用這一歷史語境,通過揭示這一歷史語境的局限來更新稱為文學的東西。因此,后來稱為文學的東西并非與先前稱為文學的東西無關,它通過揭示先前稱為文學的東西的局限來獲得自身的合法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世界上第一部稱為文學的東西已經開創(chuàng)出了后來所有能夠稱為文學的東西,正如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在談到繪畫時所說:“在某種意義上,第一幅畫就一直通達到了未來的深處。”[6](p92)后來的文學可以不同意先前關于文學的理解,但它必須回應先前關于文學的理解,否則就不能說明自己也可以稱為文學,正是這一回應使文學能夠一直保持為文學而不至于變成其他東西。例如,一直以來,我們認為詩歌“飽含著豐富的想象和感情”“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語言精練而形象、有鮮明的節(jié)奏和韻律”,而于堅的詩歌卻故意打破這些清規(guī)戒律,語言非常散文化、日常生活化,節(jié)奏也散漫拉沓。然而,我們不能說,于堅的詩歌完全是在先前詩歌之外的另一種東西,它必須回應“這也叫詩歌?”這一問題,如果它也能夠被稱為詩歌的話,就必須要到先前被稱為的詩歌的東西中尋找資源來說明自身作為詩歌的合法性。
所有對“什么是文學”這一問題的重新回答,都不是源于奇思妙想,也不能僅僅源于當下的歷史語境和文化相對物,一個人之所以能夠重新回答這一問題,必然是因為他借助當下的歷史語境和文化相對物在先前稱為文學的東西中看出了什么,他看到了先前的文學其實不僅僅是人們通常看到的那個樣子,而且還可以是其他的樣子。但他所看到的其他樣子必須是先前文學可能具有的樣子,而不是脫離先前文學創(chuàng)造出來的樣子。正如在繆勒—萊爾錯覺中,兩條相等的線段其實可以是不相等的,或者說,相等是有條件的,只有當這兩條線段處于同一個存在領域中時,它們才是相等的,如果不把它們看作是同一個存在領域中的兩條線段時,它們就可以是不相等的。同樣,我們之所以將過去的文學看作某種樣子,是因為我們處于某種歷史語境和文化相對物中,一旦歷史語境和文化相對物變了,我們就會看到過去文學的另一個樣子,后來的文學只是通過變形的方式將文學的另一個樣子開展出來而已,正如繆勒—萊爾錯覺通過添加輔助線的方式將兩條相等的線段可以不相等的意義開展出來。同樣以詩歌為例,由于某種歷史語境和文化相對物的限制,我們先前在稱為詩歌的東西中只看到了“飽含著豐富的想象和感情”“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語言精練而形象、有鮮明的節(jié)奏和韻律”等特征,但這些只是先前稱為詩歌的東西所具有的無數特征中的一部分,我們?yōu)槭裁磧H僅把這些特征規(guī)定為詩歌之所以為詩歌的原因呢?難道只有滿足這些特征,才能被稱為詩歌嗎?詩歌真的就如此狹窄嗎?而于堅詩歌的意義在于,它通過變形告訴我們,其實不滿足這些特征也可以稱為詩歌,先前的詩歌之所以被稱為詩歌,并不在于它們滿足這些特征,而是另一些更為重要的東西使它們成了詩歌。因此,于堅詩歌不是對先前詩歌的背叛,而是對先前詩歌的更深入理解,這一更深入理解的意義在于,“飽含著豐富的想象和感情”“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語言精練而形象、有鮮明的節(jié)奏和韻律”等特征并非詩歌的本質,而是詩歌在自身中能夠融合的東西,詩歌不僅可以融合這些東西,而且也可以融合語言的散文化、日常生活化,節(jié)奏的散漫拉沓等特征,甚至在以后還可以融合更多的東西。這樣,詩歌就不是越來越純化、越來越貧瘠化,而是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有張力。因此,對“什么是文學”這一問題的重新回答,不是為了刻意創(chuàng)新,也不是對傳統(tǒng)的拋棄,而是就在傳統(tǒng)之中,通過變化歷史語境和文化相對物,發(fā)掘傳統(tǒng)所具有的張力,使之在不偏離自身傳統(tǒng)的同時能夠整合更加豐富的資源。
撮要而言,文學本質既非文學整體固有的實體性構成要素,也非脫離文學整體陷入歷史語境和文化相對物中的隨波逐流,而是吸收新的歷史語境和文化相對物的中的營養(yǎng)并依據自身的內部規(guī)律在不斷生長,它總能夠通過變化視角在先前的文學中尋找到新的生長點,將所有文學按照新的維度重新組織起來,敞開先前文學被遮蔽的面貌,并以這種方式推動文學的不斷創(chuàng)新。總之,文學本質的存在方式是動態(tài)的、生成的、有活力的、充滿創(chuàng)造力的,只有這樣的文學本質才具有張力,在保持自身的同時盡可能地整合各種資源,也只有這樣的文學本質才具有高度,在回應歷史的同時引領當下的文學實踐。
參考文獻:
[1]陶東風.文學理論:建構主義還是本質主義:兼答支宇、吳炫、張旭春先生[J].文藝爭鳴,2009(7).
[2]陶東風.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J].文學評論,2001(5).
[3]童慶炳.反本質主義與當代文學理論建設[J].文藝爭鳴,2009(7).
[4]陶東風.文學理論基本問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5]南帆.文學研究:本質主義,抑或關系主義?[J].文藝研究,2007(8).
[6][法]梅洛-龐蒂.眼與心[M].楊大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