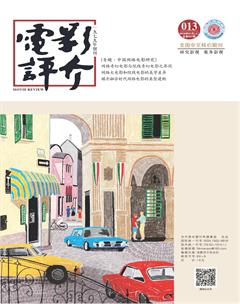媒介融合時代網絡電影的類型建構
路春艷 張志秀
自2010年微電影《老男孩》正式拉開了網絡電影創作的大幕以來,隨著互聯網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網絡電影的創作數量迅猛增長,其傳播范圍也一路拓展,儼然成為當前最重要的線上文化產品之一,得到了業界和學界持久的關注和熱議。然而,在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語境中,同諸多互聯網文化形態一樣,為了博人眼球,大量網絡電影在張揚個性的同時也不斷刺激著大眾的獵奇心理,利用軟色情、低俗的片名和離奇、暴力的情節來吸引觀眾,不僅加劇了行業內的惡性競爭,更不利于整個互聯網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隨著國家監管政策的不斷出臺,這種靠“打擦邊球”來博取點擊量和刺激觀看欲的策略難以為繼,2018年3月,愛奇藝、騰訊、優酷土豆等流媒體平臺大量下架網絡電影進行自查,為網絡大電影的生產帶來了嚴峻考驗。處在風口浪尖上的網絡電影,固然面臨著亟需正視的創作困境,然而,從某種程度上講,國家管控和行業自律也孕育著類型升級的契機。從當下網絡大電影的生產機制出發,在媒介融合的語境中思考網絡電影的類型建構,無疑是助推其走上產業良性發展道路的關鍵環節。
一、 從投機到自覺:熱門題材的類型化表達
與院線電影相比,在互聯網平臺上進行傳播的網絡電影具有“成本相對較低,技術相對輕量,制作周期相對較短”[1]等特點,梳理2014年以降在線發行的網絡大電影,不難發現,愛情片、喜劇片連年拔得頭籌,以絕對優勢成為最受網絡青睞的電影類型,驚悚片和懸疑片緊追其后,不時出現引人注目的“爆款”。近年來,網絡大電影的整體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其投資門檻較低,無序競爭嚴峻的情況卻沒有發生質的改觀。無論是愛情片、喜劇片還是驚悚片、懸疑片,這些中小成本創作依舊立足于現實語境,從社會熱點事件中尋找素材。現實題材類影片在當下的網絡電影生產和傳播體系中占據著重要比重,這一現狀雖然符合其基本定位,但目前而言,尚未走出成熟且值得推廣的發展模式。換言之,網絡電影在現實題材的創作上仍然處于原始粗放階段,所謂的“愛情”“驚悚”等“類型標簽”更多地等同于“題材”,而這些題材的選擇具有明顯的投機性,大量作品以“搭便車”的形式,試圖通過攀附院線熱門電影的片名或抄襲故事主體來復制其在院線市場的成功:《人再囧途之泰囧》(2012)、《心花路放》(2014)在院線市場的大獲成功極大地刺激了網絡大電影的創作,《山炮進城》(2015)系列、《澳囧》(2015)、《韓囧》(2015)等喜劇片爭相上線;《失戀三十三天》(2011)、《杜拉拉升職記》(2010)等都市情感片的火爆令女性觀眾成為線上線下均大力爭奪的市場資源,“小妞”題材的《總裁在上》(2017)系列、《霸道總裁藍百萬》(2017)扎堆上映,樂此不疲地用陳舊膚淺、耽于幻想的橋段勾勒遠離真實生活的“愛情”;《孤島驚魂》(2011)的過億票房點燃了國產恐怖片的創作熱情,當粗制濫造的《筆仙驚魂》(2012)等影片難逃“院線一日游”的命運時,《七月半》(2015)等網絡大電影卻借助鋪天蓋地的線上宣傳坐享可觀的“長尾”流量,獲得不錯的分賬收益。
年輕人是互聯網的主流用戶,青春和職場的話題經久不衰,在院線電影市場尚未迎來青春片創作熱潮的2010年,《老男孩》成功地將懷舊的校園記憶、理想與現實的激烈碰撞帶入觀眾的視野,點燃了微電影的創作熱潮。《老男孩》獲得的好評離不開其對青春記憶的深切懷念和對現實生活的深刻觀照,在喧鬧、戲謔、自嘲背后深藏著對理想的堅定追求,正是這種彌足珍貴的執著產生了令人動容的感染力,喚起了屏幕內外的情感共鳴和交流互動。反觀各大互聯網公司爭相布局“網絡大電影”的當下,網絡電影的生產數量和在線播放量都實現了成倍增長,但屏幕內的世界卻離我們的真實生活越來越遠。2017年上線的《哀樂女子天團》(2017)巧妙地將沉郁的殯葬業與明媚少女的音樂夢結合在一起,給人帶來耳目一新之感,然而,這樣的案例鳳毛麟角。目前網絡上常見的以青春之名或職場女性來吸引注意力的電影,無論是男性受眾廣泛的《校園風騷史之舞動青春》(2016)還是致力于吸引女性觀眾的《24小時脫單宅女》(2017),均跟風模仿院線青春片的敘事套路,深陷題材雷同、情節撞車的困局。2018年上線的《熱血跨男》宣稱自己“以青春校園競技為題材,融合愛情、友情、逆襲等多元素……”在70余分鐘的時長里雜糅了親情、友情、愛情、師生情等多種情感,試圖以愛情為動機建構一個男生的成長歷程,但影片的人物塑造和情節設置都難以令人滿意,依靠MV煽情場景串聯起來的故事存在明顯的邏輯混亂、敘事斷裂等硬傷,雖然制作較為精良,卻難掩其平庸本色。
在信息爆炸的當下,互聯網上既有眾聲喧嘩,也不乏理性思考,既有起哄的造謠者,也有冷靜的辟謠人,值得關注和思考的現實議題很多,但經由類型化的視聽語言,以敘事完整的故事片形式呈現在大眾面前的網絡電影卻很少。網絡上的年輕人對熱點新聞保持著高度敏感,對社會百態的討論不絕如縷,然而這些備受大眾關注的社會話題,雖然為網絡電影提供了創作素材,但這些電影的敘事重點并非對真實生活的寫照,也無意于對畸形病態的社會現象作出反思。《網紅是怎樣倒下的》(2017)以時下關注度一路攀升的“網紅”現象為切入點,講述了一個女孩兒追求名利、博取關注的經歷,整個故事雖然具有現實基礎,但創作者既疏于對典型個案的深度呈現,又缺乏對社會氣象的整體把握,影片津津樂道于對都市欲望濃墨重彩的渲染,僅僅將“網紅”作為噱頭,在內容和形式上都缺乏藝術感染力,雖屬于現實題材創作,卻鮮有值得肯定的現實意義。
在當前日益激烈的同質化創作環境中,急功近利的網絡電影亟需培養類型敘事的自覺,只有將噱頭轉化為真誠的講述,充分依托互聯網的便捷性和普及度讓更多的觀眾介入現實,網絡電影才能凸顯其優勢,在對用戶產生持續吸引力的同時,也實現其社會價值。
二、 差異化與精品化:類型的拓展與升級
隨著智能終端的大規模推廣,中國迎來了移動互聯時代,年輕群體日益習慣碎片化、邊走邊看、非沉浸式的觀看模式,小屏幕漸漸成為大銀幕的有力競爭對手。2014年,各大流媒體平臺試水網絡大電影之初,面對流動性極高且難以固定的受眾,均心照不宣地將點擊率作為分賬指標,為實現利益最大化,制片方致力于“先聲奪人”,依靠極具噱頭的片名、色情暴力的海報和極具感官刺激的開場六分鐘來吸引受眾。2016年以降,隨著監管措施的日趨完善,網絡電影野蠻生長、泥沙俱下的發展態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近年來,網絡大電影試圖通過不斷加大投資,依靠華麗的視聽奇觀來爭奪受眾,《斗戰勝佛》(2017)邀請明星演員和知名導演加盟,《再見美人魚》(2016)、《深宮遺夢》(2016)等影片的投資高達300萬元,然而,特效技術既不是票房靈藥,也不是口碑保證,在當下的網絡視頻生態系統中,網絡大電影的整體口碑、受關注程度和影響力都遠遠落后于網絡劇和網絡綜藝節目,其未來的走勢仍然難言樂觀。
調研報告顯示,當前年產量幾千部的網絡大電影以批量制作為主,導演和演員以及其執導或參演的前作對觀眾的影響力非常微弱①,而網絡劇和網絡綜藝節目見證了固定用戶帶來的流量和市場效益:2017年備受好評的網絡劇《白夜追兇》和《無證之罪》均憑借精心打磨的故事攬獲了口耳相傳的贊譽,許多觀眾為了第一時間觀看更新劇集而充值成為會員,說明優質的付費資源開拓了視頻網站的盈利模式,而觀眾們對《白夜追兇》第二部的翹首以待更說明高品質的作品對用戶粘性和忠誠度的培養至關重要。國產網劇在創作上漸入佳境,一路走向海外市場,為網絡電影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路徑:盲目跟風的粗獷模式必須向深耕細作的方向轉變,形式多變的營銷手段首先應該以精致的內容支撐為依托。
在類型敘事自覺的基礎上,網絡大電影可以通過類型的差異化來爭取受眾。著力打造院線市場上鮮有的國產科幻片,是一條值得探索的道路:2017年中影投資的《孤島終結》作為一部成本僅7萬元的低成本創作,與《機器男友》(2017)等隨意穿插“科幻”元素的喜劇片明顯不同,盡管在敘事上存在明顯的瑕疵,這部影片在故事結構和內容上均力求接近真正的科幻,做了一次值得肯定的類型嘗試;《海帶》(2017)同樣是一部科幻題材影片,影片從一位精神病人的視角出發,通過講述一個“海帶星人入侵地球”的荒誕故事來審視邊緣人的生存困境,離奇的情節和黑色幽默的基調下不乏對現實的思考,鏡頭語言的運用和配樂都比較精致。
《孤島終結》和《海帶》兩部科幻片,令人欣喜地看到網絡電影在類型拓展上的進步,然而,相比于院線電影的多元類型探索,網絡電影還需作出更大的突破,差異化競爭之外,更應該以內容的精品化來積聚優良口碑,這樣才有可能同網絡劇和網絡綜藝節目一樣,逐步培養起忠實的受眾。2010年以來,院線電影市場的繁榮不僅表現為喜劇片、愛情片、青春片屢創票房新高,更重要的是其見證了類型電影的迅速成長和漸趨成熟。中小成本佳作如警匪片《烈日灼心》(2015)、犯罪片《白日焰火》(2014)、《暴裂無聲》(2018)等不僅以精致的視聽和圓融的敘事為觀眾帶來了高品質的觀影體驗,更在類型敘事的框架下置入創作者對當下中國現實困境和社會癥結的深切關注和思考,具有強烈的、發人深省的現實意義,而這些影片的創作者均是年輕的電影人,他們在各類青年電影展和青年導演扶持計劃中嶄露頭角,漸漸成長為中國電影創作的中堅力量。對網絡大電影而言,鼓勵青年導演原創是其類型升級和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
2014年,國內流媒體平臺愛奇藝影業率先提出“網絡大電影”概念,其負責人在網絡發行計劃推出之際便指出,“……(網絡大電影的)核心是故事……以前微電影和網絡影片的導演大多是草根出身,現在90%的導演和作者都是院系里面出來的……這一類相對成本很低的片子理論上沒有任何機會進入院線,但是我們在互聯網的平臺給它提供了非常好的展示機會”[2],說明流媒體平臺不僅是網絡電影的發行平臺,還應該充分發揮其優長,成為鼓勵創意的投融資平臺和青年導演的成長平臺。然而,盡管“互聯網+”的覆蓋面越來越廣,愛奇藝、優酷土豆、騰訊相繼啟動了各類創意計劃,積極吸納青年電影人進入電影工業體系,但目前上線的網絡大電影還鮮有藝術品質特別突出的作品。比之于流媒體平臺對熱門題材緊鑼密鼓的宣傳,其對青年導演的扶持仍待產生真正的影響力。
網絡電影不同于用戶上傳的自制短視頻,與時長更加靈活的微電影也多有不同。作為面向廣大網絡觀影群體的文化產品,網絡電影應該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鮮明的價值立場,在此基礎上作出藝術突破則有利于其品質的提升。成長在新世紀的年輕觀眾,比其父輩擁有更便捷的文化資源,積累了一定的觀片基礎,隨著其審美要求的提升,帶有實驗氣質的藝術佳品對追求個性的年輕人有著越來越大的潛在吸引力。不得不提的是,帶有“實驗氣質”的故事片不能與“實驗片”混為一談,前者的藝術性建立于扎實的敘事之上,后者則更強調形式感。事實證明,接受過系統化專業訓練的青年導演有著類型創作的自覺,在足夠的資金支持下,能夠以類型化的影像語言觀照歷史與現實。近年來先后得到FIRST青年電影展肯定的《心迷宮》(2014)和《中邪》(2016)有諸多值得網絡大電影借鑒之處:《心迷宮》以獨具匠心的迷宮敘事,抽絲剝繭般揭開了封閉村莊的重重隱情,離奇的案情和黑色幽默的手法背后是導演對人心的洞察和人性的拷問;《中邪》中的偽紀錄片手法,從某種程度上講,與當下網絡上熱衷于奇聞逸事、社會奇譚的“直播”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但影片對鏡頭語言的運用值得稱贊,粗糲的畫面和一路升級的恐怖氣氛令人毛骨悚然,是值得肯定的藝術嘗試。
值得深思的是,近十年來,從各類青年影展和青年導演扶持計劃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們,如忻鈺坤、畢贛、馬凱、李睿珺等人,在《心迷宮》《路邊野餐》《中邪》《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等一眾影片中,不約而同地將鏡頭對準了在城市化進程中日漸荒蕪、凋敝、被遺忘的偏遠鄉村,關注游離于主流話語之外的邊緣社會,記錄現實社會的另一種生活,具有人文精神和社會價值。《心迷宮》等佳作同大多數網絡大電影一樣,是低成本的作品,但這些事業剛剛起步的電影創作者們利用有限的資金和資源,以較為成熟的視聽語言和巧妙的敘事結構實現了獨具特色的藝術表達,在不疾不徐的節奏中保持著敘事內容和敘事形式上的微妙平衡,盡管影片的成色有些粗糙,卻彰顯出青年導演的創作銳氣,令觀眾對其下一部創作充滿了期待。許多青年導演的首部中長片創作依靠口碑傳播而逐漸走向公眾視野,而一度集中涌現的網絡大電影制片公司則盲目追逐市場熱點,熱衷于撿拾院線電影的“邊角料”,以“炒冷飯”的方式實現“低成本,高產出”的經濟效益。隨著國人版權意識的增強和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這種寄生式、山寨化的生產與營銷模式必然會被市場淘汰,通過類型的拓展和升級來實現差異化競爭,創作出類型色彩鮮明又不失藝術氣質的作品,是網絡電影轉型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三、 迷群文化的深耕:跨媒介敘事與類型融合
新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中國的視覺文化產業發展迅速。依托于日益精進的特效技術,國產電影不僅對《西游記》《聊齋》《白蛇傳》等傳統文學故事改編為魔幻大片,還不遺余力地發掘《盜墓筆記》《鬼吹燈》等網絡文學的市場潛力。主流網絡視頻平臺上,倡導原創理念的“微電影”在產業整合中走向了看重“IP資源”的“網絡大電影”,然而,自2014年“網絡大電影”概念的提出到2016年國家對網生內容實行管控前夕的兩年間,“網絡大電影”的創作數量、播放量和分賬收益均一路高歌猛進,并非緣于過硬的品質,而是以蹭“IP”的山寨投機之舉來博取關注,這一現象集中凸顯在古裝、奇幻等非現實題材的創作中。《道士出山》(2015)以不足30萬的投入獲得了高達2000多萬元的收入,不僅掀起了玄幻仙俠、僵尸鬼怪題材的創作熱潮,更令“寄生營銷”成為網絡電影盈利的不二法寶,一時之間,各大網絡平臺上群魔亂舞,僵尸橫行。《道士出山》《捉妖濟》(2015)等山寨作品風靡一時,既得益于混淆視聽的宣發策略,又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下網絡上狂歡情緒的盛行。經歷了幾番下架、整改、審查風波,網絡電影的浮躁之氣有所消散,但轉型之路卻步履維艱。就2018年第一季度上線的網絡電影而言,除了《靈魂擺渡·黃泉》(2018)集合了系列網絡劇《靈魂擺渡》的原創人馬,在原有口碑之作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突破,獲得了較高的評價這一個案之外,網絡大電影的“IP精品化”轉型之路依然道阻且長。
受到業界和學界高度關注且持續引發激烈討論的“IP”話題,作為融媒體時代令人矚目的文化現象,與時下風生水起的青年文化有著極其密切且復雜的關聯。近年來各類文化產業報告的調研數據顯示,90后日漸成為文創市場的消費主力,而00后的崛起亦不可忽視。在院線電影觀眾發生結構性轉變的同時,互聯網新增用戶的低齡化趨勢也日益明顯,藝恩咨詢發布的《2016年中國網絡大電影行業研究》顯示,網絡大電影的受眾中,19歲以下的觀眾占比30.1%,20—29歲的觀眾占比32.3%,而在文化水平與學歷結構分布上,初中學歷的觀眾占比21.8%,高中學歷觀眾占比41.5%,兩者占比超過60%。①恰如社會學家米爾斯所言,在變化速度越來越快的社會中,應該格外注意時代中的人的類型的問題[3],出生或成長于新世紀的年輕一代是信息網絡時代的原住民,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在一個相對寬松、開放和自由的社會環境中,他們始終對紛至沓來的外來文化保持著強烈的好奇心和強大的吸收能力,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動漫、網游架構的虛擬世界和現實生活之間,因對某種流行文化異常著迷而自發地形成新型社群,樂此不疲地進行著新的文本生產,由此而形成了蔚為可觀的迷群文化①,成為一種自覺的跨媒介敘事實踐。
《盜墓筆記》《鬼吹燈》等網絡文學IP的開發獲得了不俗的市場收益,《道士出山》(2015)、《二龍湖浩哥之江湖學院》(2017)等則是對港片IP的再次消費。然而,無論是“盜墓”“捉鬼”還是“混社會”,這些80后的集體記憶在網絡上的影響力漸漸走弱,已然不敵炙手可熱的漫畫、網游和同人小說。活躍于網絡世界的新興觀影群體圍繞著動畫(Animation)、漫畫(Comic)、游戲(Game)、輕小說(Novel)(根據其英文單詞的縮寫,下文簡稱為ACGN),形成了獨特的二次元審美,他們消解權威,挑戰傳統,以彈幕、表情包、短視頻狂歡的方式宣告與成人世界的不同,充分利用互聯網突破時空阻隔的技術優勢,建構起代迭明顯的圈層文化,創造出形形色色的流行符號。作為純網生一代,年輕觀眾以天馬行空的想象實踐著“動作+奇幻”“古裝+科幻”“魔幻+科幻”等跨類型敘事,用自己的方式解讀社會萬象,解構現實生活,并不在意是否被主流社會認可,而是在小圈子樂此不疲的另類話題和文化密碼中尋求身份認同。大數據時代,定制產品和精準營銷成為市場的新寵,毋庸置疑,作為網絡電影主力受眾的網生一代,他們的審美趣味正深刻影響著網絡電影的創作方向,迷群文化由此而成為一座亟需深度開掘的資源寶庫。
網絡上層出不窮的流行語和曾經小眾的二次元文化在當下儼然發展為泛青年文化,借助移動互聯平臺滲透到成人世界,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這一趨勢顯然受到愛奇藝、騰訊等流媒體平臺的密切關注,以蹭IP、山寨惡搞等手段來吸引受眾的低成本網絡電影逐漸被市場淘汰,倚重動漫元素、特效包裝來吸引青年受眾的作品集中涌現。然而,雖然播放量可觀的《魔游紀》(2017)系列電影借“西游元素”構建起全新的異域時空,《絕命循環》(2017)以網絡游戲的邏輯和匪夷所思的情節顛覆了民國諜戰劇的敘事傳統,《異次元少女失蹤事件》(2016)不遺余力地營造日本推理動漫的氛圍,《獵靈師:鎮魂石》(2016)以高規格的特效強化二次元元素,但網絡電影對ACGN資源的開掘卻并不成熟,許多網絡上風靡一時的文學和漫畫作品被改編為電影后,靜態文字或圖畫并沒有轉變為精致的動態影像,其內容和形式均難以實現真正的類型融合,更多地停留在拼貼、雜糅階段,不僅沒有吸引新觀眾,還不時陷入被原著粉絲集體聲討和抵制的尷尬境遇。
在整個社會泛娛樂化色彩越來越明顯的同時,國家對網絡文化的重視程度也空前提高。2016年至今曾被勒令下架或整改的網絡電影中,充斥著鬼怪靈異情節的“奇幻/魔幻”類影片成為首當其沖的“重災區”。媒介融合時代如何將網生代觀眾迷戀的IP資源有效地轉化為既有受眾基礎,又契合主流價值理念的作品,在迷群文化、商業訴求和審查風險之間尋求平衡,這不僅是當下網絡電影人集體面對的創作難題,與此同時也亟需整個文化工業體系的協同探索。
參考文獻:
[1]張燕,盧科巖.中國微電影發展現狀與未來展望[M]//金德龍,楊才旺,王暉.中國微電影2016.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7:2.
[2]潘樺.電影新生態:從微電影到網絡大電影[M].北京: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18:104-105.
[3](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M].李康,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