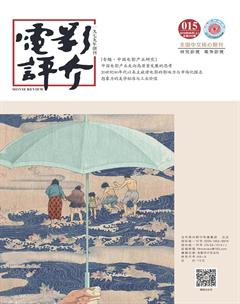《出山記》的紀實風格與當下關照
彭美玉
在2018年第八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一部記錄貴州遵義大山里脫貧攻堅故事的電影——《出山記》,以“黑馬”姿態斬獲紀錄單元評委會最佳作品獎。不少觀眾看過之后表示,“主旋律能引人入勝并不容易,但這部作品用真情打動了我”。
本文主要從敘事技巧、人物構建、心靈鏡語三個方面來分析《出山記》的紀實風格。此外,透過電影所傳遞出來的脫貧攻堅進程中的一個時代、一個群體和一種關懷也賦予了電影更多的現實關照。
一、《出山記》的紀實風格
(一)敘事技巧:多情節中的主題統一
《出山記》的故事發生地——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大漆村,一個美得沁人心脾但又窮得讓人觸目驚心的地方。全村985戶4119人中貧困戶有435戶1803人。
影片圍繞脫貧攻堅這個主題,以脫貧攻堅中的易地扶貧搬遷、大通道建設、特色產業發展為主線,講述當地群眾脫貧致富、走出大山的故事。
大齡青年申周一心想借政府易地扶貧搬遷的政策離開貧困的山村,到城里開始新生活。但和莊稼、牛羊打了一輩子交道的父母卻不愿意離開大山,觀念的不可調和一度引發了家庭矛盾。
常年在外打工的申學科是個孝子,父親的病重讓他回到了家鄉。為了帶父親看病,他背著父親在尺把寬的懸崖山路上艱難地步行一個多小時,他最大的心愿是通組路能夠早日修好。
申修軍,大漆村黨總支書記,肩負脫貧攻堅重任的他白天走村串戶做群眾思想工作,晚上還要熬更守夜整理脫貧材料,然而他的付出并沒有獲得群眾的理解,甚至招來謾罵和毆打。
三條主線、三個人物,在相對獨立完整的故事鏈條中,又有機地統一在脫貧攻堅這個主題下。不管是申周對城里新生活的憧憬,還是申學科對通組路的渴望,乃至申修軍在工作中的無奈,《出山記》猶如一面鏡子,生動地照出了脫貧攻堅進程中的人和事。
(二)人物構建:平視下的性格塑造
平視又被稱作平民視角和平民化視角。平視的理念,就是要超越國家意識、階級意識、民族意識、階層意識,超越意識形態去考察人類社會最為本真的東西,探討人類共同存在的問題。[1]在《出山記》中,平視是影片一以貫之的態度。
《出山記》的平民視角首先體現在人物的準確選擇上。申修軍的形象與主旋律電影中高大全的好干部形象有很大不同,他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農村一線干部,每天身處各種繁瑣的工作和糾纏中,既要貫徹國家扶貧政策,又要做好群眾工作。在影片中,不僅看到了他履行基層干部職責的兢兢業業和擔當、也看到他無暇顧及家庭的無奈,甚至看到他做不通群眾工作時的無助和潑辣,他是豐滿的,更是鮮活的、真實的。正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基層干部,拉近了主人公和觀影人的距離,也讓生活的酸楚和簡單的幸福在影片和現實之間產生了共鳴。
《出山記》的平民視角還體現在矛盾沖突中的性格塑造。申周在搬遷問題上幾次和父母發生矛盾,甚至還和父親動起了手,就在觀眾紛紛譴責這個“大逆不道”的“不孝子”時,他卻在父母同意搬遷并拿出所有積蓄準備支付搬遷款時以“冷關心”的方式回應父親:“你留一些錢在身上。不夠的我來想辦法。”在申周身上,仿佛看到了中國千萬家庭的親子相處方式,愛而不愿言,愛而不善言。
(三)心靈鏡語:旁觀下的真情流露
創作者只有跟拍攝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全面了解拍攝對象,才不至于像盲人摸象一樣把事物分解為一個個不相關聯的局部,這是紀實主義提倡的一種觀察方法,把“客觀距離”放在第一位,保持清醒的態度,努力再現客觀事物(生活)的原貌。[2]《出山記》在拍攝過程中,不論是村民對申修軍的謾罵,還是村民房屋被拆遷后的不舍,或是村民申學王一家進城后的好奇,鏡頭都客觀、真實地進行了呈現,沒有一個刻意而為的場景。在這種客觀的距離下,人物的真情實感自然流露。如影片開場不久,為了拓寬公路,60多棟房屋面臨拆遷。在轟鳴的挖掘機將一堵堵墻推倒的過程中,一個鏡頭震撼人心——一個女村民靜坐在廢墟上,倔強而又不舍的眼神凝視遠方,而身后則是自家即將被推倒的房屋,委屈、不舍、隱忍頓時侵入觀眾內心。
“在一般紀實類的紀錄片中,如果第三人稱的旁白表現出了某種情緒,馬上會被認為是煽情,是誘導,是議程設置,是宣傳等等,因此大部分紀實類的紀錄片都盡量規避第三人稱的旁白的使用,代以劇中人物的敘述”。[3]不同于以往政論紀錄片對解說詞的大量使用和聲畫對位,以及人文歷史紀錄片恢弘場景、優美配樂等藝術表現手法的使用,《出山記》自始至終沒有一句解說詞和旁白,不作任何主觀性的解釋和表達,既沒有說脫貧攻堅政策是多么偉大正確,也沒有說村民們基于自身利益抵觸相關政策是多么錯誤,而只是把一個完整的故事擺在觀眾眼前,讓觀眾慢慢體悟、細細思考。
二、《出山記》的當下關照
一個時代。在第八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評委會對《出山記》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出山記》為我們展示了遵義貧困大山里脫貧攻堅波瀾壯闊的時代畫面,為我們講述了貧困山民翻越腳下大山的曲折動人故事。”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黨的十九大把脫貧攻堅戰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贏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脫貧攻堅這場具有時代意義的戰役注定會被銘記。
《出山記》將鏡頭對準貴州這個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以小見大、以點帶面地展示出廣大干部群眾在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的良好精神風貌,是一種現實生活的反映,更是一個時代的記錄,為這一歷史進程留下了具有文獻價值的影像資料。
一個群體。在脫貧攻堅這場戰役中,最大的主力軍是成千上萬的農村基層干部,而申修軍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他代表了我國一大批當下的基層干部形象,他們扎根鄉土,深諳民情,兢兢業業地執行國家政策,用自己的情感和付出投入到一個個微小但重要的工作中。大多數時候,他們的工作既非令人矚目的壯舉,也不具有一錘定音的歷史地位。但是,在積極面對新時代主要矛盾的過程中,在中國社會管理的現代化需求逐漸提高的今天,正是這些基層干部的日以繼夜的平凡工作,理解和消化了發展過程中的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鼓勵不同群體之間的溝通、理解和認同,從而凝聚了脫貧和發展這個最大的公約數。[4]
一種關懷。任何成功的作品都是有情懷的,它透露著創作者對社會、人文、良知的情感,對社會的責任和使命。紀錄片存在的意義就在于它的靈魂和責任,在于對人們生存狀況的關懷、對人們尊嚴的關懷、對人類社會責任和使命的鞭策。[5]
《出山記》之所以感人,除了其記錄的是真人、真事、真情之外,更多地在于其透過影片傳遞出來的對脫貧攻堅歷史進程中各類群體生活狀態的關注、關心、關懷,以及對扶貧就要扶志、扶智的思考。生存的大山容易翻過,然而生活的大山和思想的大山能否輕易翻過卻是需要時間印證。
參考文獻:
[1]何蘇六.中國電視紀律片史論[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
[2]歐陽宏生.紀錄片概論[M].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
[3]聶欣如.紀錄片概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4]梁君健.《出山記》精準扶貧的影響記錄[J].光明日報,2018(5).
[5]朱榮清,張志巍.紀錄片中的“多元”人文關懷[J].今傳媒,2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