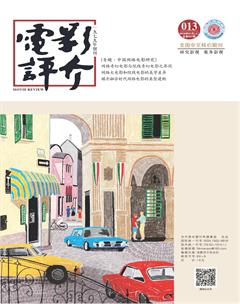從民族性到現(xiàn)代性: 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①現(xiàn)實(shí)主義思潮概貌
王丹丹 張蕓
中國(guó)電影發(fā)展100余年的歷史長(zhǎng)河中,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思潮貫穿始終。從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視角切入,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內(nèi)涵與表征在不同的時(shí)代語境下不盡相同,形成了獨(dú)有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手法,林立于中國(guó)電影的多元化發(fā)展之中。在中國(guó)電影快速發(fā)展的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更是占據(jù)了中國(guó)電影市場(chǎng)的重要地位,同樣,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也有令人驚艷的表現(xiàn),如《告別》《八月》《爆裂無聲》都是基于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電影作品。從中國(guó)電影大語境下甄別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地整體建構(gòu),從早期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重心是民族歷史敘事的呈現(xiàn)到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現(xiàn)代文明沖擊之下民族生存的憂患思索再到新世紀(jì)青年導(dǎo)演崛起,對(duì)潛藏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切實(shí)的民族生存、人性復(fù)雜以及民生問題進(jìn)行的闡釋,都呈現(xiàn)出基于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思潮的主體脈絡(luò),成為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發(fā)展至今的主流創(chuàng)作趨勢(shì)。綜觀這一發(fā)展脈絡(luò):歷經(jīng)了1942年—1966年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傳承發(fā)展時(shí)期、1977年—2000年來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剝離轉(zhuǎn)型期、2000年—2015年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民族性回歸以及2015年直至現(xiàn)今,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
一、 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傳承發(fā)展(1942—1966)
從1942年的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塞上風(fēng)云》伊始,到1949年新中國(guó)成立為止,作為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發(fā)展的開端,飽含了藝術(shù)家對(duì)國(guó)家命運(yùn)與民族命運(yùn)的憂患和希冀,承載著強(qiáng)烈的國(guó)家意識(shí)、民族意識(shí)進(jìn)行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一定程度上傳承了20世紀(jì)30年代中國(guó)早期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形式,諸如《漁光曲》《十字街頭》《桃李劫》等能夠反映現(xiàn)實(shí),更能夠預(yù)示未來的影片。同樣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的發(fā)展不是孤立的,尤其在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形式上,它與中國(guó)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電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手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在中國(guó)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映照之下傳承發(fā)展,基于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力度逐漸深化,成為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創(chuàng)作的必然趨勢(shì)。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第一部?jī)?nèi)蒙古影片《內(nèi)蒙人民的勝利》,迎合了時(shí)代背景和民族政策,以宣揚(yáng)民族解放和革命事業(yè)為影片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基調(diào),在中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演進(jìn)中表達(dá)政治立場(chǎng)和意識(shí)形態(tài)訴求的同時(shí),描繪著中國(guó)社會(huì)主體的價(jià)值取向。影片沿襲了早期中國(guó)電影,如《中華兒女》《光榮人家》等立足于革命歷史與戰(zhàn)爭(zhēng)題材下的影片。影片《草原上的人們》《牧人之子》等通過對(duì)草原人民的勞動(dòng)和斗爭(zhēng)的書寫,來闡釋本民族保護(hù)和堅(jiān)守勝利的果實(shí)的日常生活常態(tài),在穩(wěn)定的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環(huán)境中,電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進(jìn)入民族文化體系,反映解放后的新中國(guó)、新草原和人民新生活、新景象的電影創(chuàng)作使影片更具有現(xiàn)實(shí)性且還原了電影本體性價(jià)值。
毋庸置疑,在1942年—1966年電影創(chuàng)作的風(fēng)起云涌中,中國(guó)電影史上涌現(xiàn)出大批優(yōu)秀的影片,這一時(shí)期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也迎來佳作迭出的黃金年代。無論1942年的《塞上風(fēng)云》還是1949年—1966年期間的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在以現(xiàn)實(shí)主義為主的創(chuàng)作形式上,通過對(duì)內(nèi)蒙古歷史、現(xiàn)實(shí)、生活、生產(chǎn)的影像表達(dá),讓黨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區(qū)落地生根,達(dá)到對(duì)新中國(guó)的國(guó)家認(rèn)同,傳承著中國(guó)傳統(tǒng)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的創(chuàng)作熱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20世紀(jì)80年代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的發(fā)展趨向。
二、 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剝離轉(zhuǎn)型(1978—2000)
1976年“文革”結(jié)束后,進(jìn)入80年代,長(zhǎng)期以來的文化封閉現(xiàn)象被打破,文化思想領(lǐng)域的大解放,改革開放的政策使各種創(chuàng)作形式涌入了電影創(chuàng)作當(dāng)中,但是盡管如此,從電影的整體創(chuàng)作上仍然可以看出,20世紀(jì)80年代的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創(chuàng)作仍舊是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歸趨,題材上因循守舊,仍然是對(duì)草原生活圖景的闡釋和民族風(fēng)俗的直觀描摹,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自此而產(chǎn)生出剝離的態(tài)勢(shì)。90年代初延續(xù)到2000年,強(qiáng)烈的商業(yè)訴求在電影中占據(jù)了上風(fēng),影片的基調(diào)多是呈現(xiàn)以商業(yè)化傾向的類型片形式表現(xiàn)民族題材的內(nèi)容。[1]由此,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進(jìn)入了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型時(shí)期。
80年代初期的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創(chuàng)作仍然延續(xù)了中國(guó)三四十年代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影片《獵場(chǎng)札撒》采用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方式,表現(xiàn)蒙古族人民的真實(shí)生活、樸素醇厚的蒙古族習(xí)俗,進(jìn)而傳達(dá)出天、地、人之間的理想境界和審美感受。80年代初期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創(chuàng)作與同期的全國(guó)電影創(chuàng)作緊密聯(lián)系,受時(shí)代的影響,不少導(dǎo)演沖破傳統(tǒng)的藝術(shù)觀念,從政治立場(chǎng)轉(zhuǎn)向美學(xué)立場(chǎng),開始關(guān)注影片的真實(shí)性和電影中蘊(yùn)藏的人情、人性。如影片《人生》《巴山夜雨》基于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下對(duì)電影藝術(shù)的真實(shí)追求、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折射出的問題進(jìn)行反思和拷問,從對(duì)于歷史和現(xiàn)實(shí)問題的思考,引向國(guó)家和民族文化的深層內(nèi)涵,奠定了80年代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的現(xiàn)實(shí)品格。
20世紀(jì)90年代初延續(xù)到2000年,全球化進(jìn)一步深入,中國(guó)從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轉(zhuǎn)向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面對(duì)經(jīng)濟(jì)化與市場(chǎng)化的雙重考量,以塞夫、麥麗絲為主要代表的蒙古族導(dǎo)演,為了兼顧藝術(shù)與娛樂相融合,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型模式進(jìn)行市場(chǎng)化探索,創(chuàng)作了這一時(shí)期多元化、類型化的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的扛鼎之作。影片《騎士風(fēng)云》《東歸英雄傳》《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通過耳目一新的影像造型和獨(dú)特的藝術(shù)內(nèi)涵,把民族、文化、歷史以及人類生存現(xiàn)狀通過宏大的民族敘事方式融入到電影創(chuàng)作中,這一系列民族史詩電影與當(dāng)代主流類型電影整合、建構(gòu),使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從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中轉(zhuǎn)型,不再是還原和再現(xiàn)歷史,而是將歷史化入神話加以敘述,通過虛構(gòu)、想象和敘述的形式進(jìn)行電影創(chuàng)作,不再是依托于特定民族地區(qū)的表現(xiàn)形式,而是雜糅在娛樂化與商業(yè)化中發(fā)展。
三、 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民族性回歸(2000—2015)
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熱潮沖擊和裹挾之下,2000年以來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創(chuàng)作題材更加豐富,內(nèi)容更加多元。與早期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描繪民族生活、刻畫民族性格的民族性內(nèi)涵不同,2000年以來轉(zhuǎn)向書寫民族精神與追尋民族文化之根為主的民族性內(nèi)涵。民族性的回歸與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格呈現(xiàn)出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創(chuàng)作的新面貌,關(guān)注農(nóng)耕文明、游牧文明在市場(chǎng)化、工業(yè)化的時(shí)代撕裂性變遷及社會(huì)轉(zhuǎn)型中所帶來個(gè)體經(jīng)歷的陣痛,由此引發(fā)的懷舊和傷感情緒真實(shí)的表達(dá)在電影創(chuàng)作中,通過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審視當(dāng)下蒙古族所面臨的生活困境與生存危機(jī),表達(dá)出對(duì)本民族歷史、現(xiàn)實(shí)與未來的深思。
以《季風(fēng)中的馬》《藍(lán)色騎士》《長(zhǎng)調(diào)》為代表的影片,是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下日益失落的傳統(tǒng)文明、民族身份及草原精神狀態(tài)的表達(dá),是對(duì)民族自豪感的日漸喪失和民族生存困惑感不斷深化的闡釋,通過個(gè)體的生存狀態(tài)進(jìn)而展示草原人們?cè)诂F(xiàn)代化進(jìn)程中遭受的艱難境遇,都呈現(xiàn)出一種以現(xiàn)實(shí)主義為主要風(fēng)格的創(chuàng)作形式。影片從傳統(tǒng)民族風(fēng)情的表達(dá)過渡到對(duì)于人性的探索,逐步走出對(duì)歷史情節(jié)的眷戀,把目光投射到了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來挖掘民族文化和人文精神,使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的民族性創(chuàng)作回歸現(xiàn)實(shí)理性。從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創(chuàng)作的趨勢(shì)上可以充分體現(xiàn)出一種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照,傳達(dá)出人們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精神狀態(tài)和人類普遍情感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表達(dá)。無論是在主題的選擇還是電影的創(chuàng)作水準(zhǔn),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創(chuàng)作表達(dá)的發(fā)展路徑與存在空間中的文化象征意義和民族主義價(jià)值,都是在創(chuàng)新中得到了發(fā)展。
這一時(shí)期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的創(chuàng)作,以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焦點(diǎn)來關(guān)注人類普通的情感經(jīng)驗(yàn)與人文精神表達(dá),個(gè)體的記憶在時(shí)代的延續(xù)中充滿了陣痛感和無措感,草原文化的遺存與民族文化的轉(zhuǎn)型,從民族生存歷史選題的本體論探尋到民族意識(shí)的覺醒,通過對(duì)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展示,構(gòu)成對(duì)歷史維度和民族生存的反思,這些都將標(biāo)志著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之下歷史反思與民族性回歸,開始逐步的走向文化與歷史的深度和廣度中。
四、 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現(xiàn)代性反思(2015至今)
通過FIRST青年電影展發(fā)掘出一批新銳的蒙古族青年導(dǎo)演,從德格娜到忻鈺坤再到張大磊以及今年備受矚目的周子陽。電影《告別》《心迷宮》《爆裂無聲》從普通人的精神狀態(tài)出發(fā),深入挖掘人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狀態(tài)以及人的生存現(xiàn)狀進(jìn)行現(xiàn)實(shí)主義描摹;從理想情感主義的精神出發(fā),緊密的聯(lián)系人生,從民族性回歸走向現(xiàn)代性反思,以自我去展示宏觀,以自我來反觀世界,將本民族與社會(huì)大眾所共有的特性融入到當(dāng)前中國(guó)電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大語境下進(jìn)行電影創(chuàng)作和藝術(shù)提煉。
2015年以來,這些導(dǎo)演在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藝術(shù)呈現(xiàn)中更加注重對(duì)于大環(huán)境下群體生存狀態(tài)本質(zhì)的真實(shí)關(guān)注,從而著力反映社會(huì)歷史文化語境下作為大眾群體的生存狀態(tài)。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發(fā)展正在經(jīng)歷著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將傳統(tǒng)生活與社會(huì)變革相結(jié)合,有充分的社會(huì)認(rèn)知意義,呈現(xiàn)出當(dāng)代社會(huì)的本質(zhì)。電影《告別》《八月》《爆裂無聲》等都是在中國(guó)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社會(huì)歷史背景下,匯集在統(tǒng)一空間語境下而達(dá)成的在變幻莫測(cè)的時(shí)代中,不僅僅是闡釋生活的表象問題,更不是生活流,這些影片記錄了大時(shí)代下人們內(nèi)心的精神,小人物間情感的真實(shí)流露與生活乖舛更加賦予觀眾從影片走向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生活本真,在真實(shí)再現(xiàn)了時(shí)代氛圍的基礎(chǔ)上,呈現(xiàn)了內(nèi)蒙古地區(qū)普通群眾的心靈世界。
2015年以來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的發(fā)展不再局限于民族題材在個(gè)人記憶中的表達(dá),更多的則是將內(nèi)蒙古置于整個(gè)現(xiàn)代社會(huì)轉(zhuǎn)型中,討論其引發(fā)的現(xiàn)代性標(biāo)準(zhǔn)語境下所帶來的社會(huì)共有陣痛與焦慮。將民族化、本土化的多種元素轉(zhuǎn)化到電影創(chuàng)作中,使影片在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過程中做出創(chuàng)新性改變,關(guān)注人類社會(huì)整體的價(jià)值體系、精神世界與物質(zhì)世界,在現(xiàn)實(shí)代替情感、理性代替感性的現(xiàn)代狀態(tài)的深化與思考。
結(jié)語
在中國(guó)電影高速發(fā)展的當(dāng)下,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機(jī)遇也面臨著新挑戰(zhàn)。面對(duì)今天國(guó)家“一帶一路”建設(shè)、“走出去”戰(zhàn)略所體現(xiàn)出完整的意識(shí)形態(tài),中國(guó)電影中所體現(xiàn)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主流價(jià)值以及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創(chuàng)作手法,都印證了中國(guó)正在以一個(gè)大國(guó)的姿態(tài)崛起。隨著《戰(zhàn)狼》《紅海行動(dòng)》的主流元素與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形式相結(jié)合的主旋律電影的問世,無疑為中國(guó)電影現(xiàn)實(shí)主義題材的發(fā)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開拓了多種發(fā)展可能性。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與主流電影相結(jié)合,準(zhǔn)確、深入的把握了中國(guó)的發(fā)展?fàn)顟B(tài)、現(xiàn)實(shí)的社會(huì)生活以及本民族的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用鮮活的影像表達(dá)中國(guó)社會(huì)主義價(jià)值觀,挖掘潛在的現(xiàn)實(shí)價(jià)值,創(chuàng)造具有中國(guó)特色的電影,為當(dāng)今中國(guó)電影的興盛締造出別樣的影視熱潮。
作為中國(guó)電影的重要組成,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的價(jià)值在于建構(gòu)國(guó)家文化意義上的多樣性,是一種可以對(duì)主流文化和他者文化產(chǎn)生實(shí)際傳播影響的存在。在民族發(fā)展和民族勃興中,基于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電影是反映民族發(fā)展的藝術(shù)形式,對(duì)世界的吸引力和對(duì)后世的影響是最具變革性和廣泛性的意義,正是由于電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表達(dá),才能夠讓國(guó)家、民族采取這一特殊的藝術(shù)形式和話語形式,來反映現(xiàn)實(shí)的人生精神。中國(guó)電影創(chuàng)作應(yīng)該繼承自己的傳統(tǒng)藝術(shù),建構(gòu)屬于自己的民族特色與文化氣質(zhì)的藝術(shù)理論表達(dá)體系,這就要著力倡導(dǎo)以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為核心的中國(guó)電影,不僅是電影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dòng)力,更是一個(gè)國(guó)家、人民發(fā)展進(jìn)步的迫切需求,并成為電影中最廣闊和深遠(yuǎn)的組成。進(jìn)入新世紀(jì),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在努力融入中國(guó)電影大語境的同時(shí),必不能忽略的一點(diǎn)——現(xiàn)實(shí)主義成為電影作品中的重要?jiǎng)?chuàng)作方式之一,再現(xiàn)內(nèi)蒙古輝煌歷史進(jìn)程中鮮明的創(chuàng)作方式,這是內(nèi)蒙古民族電影最獨(dú)特的印記。[2]
參考文獻(xiàn):
[1]饒曙光.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電影史[M].北京:中國(guó)電影出版社,2011:240.
[2]張蕓.內(nèi)蒙古電影六十年“蒙古人”形象掃描[J].內(nèi)蒙古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0(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