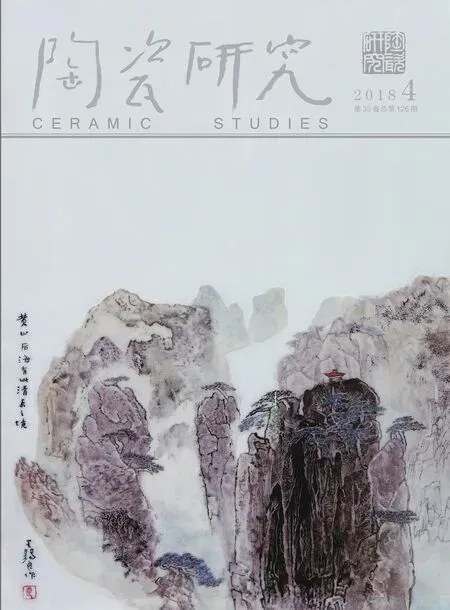瓷器上圖像的信息解讀方法
——以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康熙五彩瓷人物故事圖盤為例
劉樂君
(景德鎮陶瓷大學 景德鎮市 333403)
1 問題的提出
自古至今,浩瀚的中國傳統文化在瓷器上以圖像的方式呈現歷時千年,種類繁多。由于對讀圖者的故事文化背景的了解程度和綜合判斷能力的要求較高,敘事性人物故事圖的解讀是最為復雜和具有難度的。在缺乏對瓷器上敘事性故事圖中必要的歷史文化背景知識的認知的情況下和未能合理掌握圖像信息解讀方法的前提下,人們習慣根據瓷器上呈現的表淺圖像信息或單憑個人的生活經驗來對故事情節加以判斷,這就很容易產生錯誤的判斷。如何才能做到對圖像的正確認識和判斷?以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的清康熙五彩人物故事圖盤為例,由于沒有合理地運用圖像的信息解讀途徑,使得本應該是“洗桐圖”的故事圖像被誤解為“采桑圖”故事圖像的錯誤結論。

圖1 清康熙1700-1720 五彩人物故事圖盤 口徑27cm景德鎮窯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
2 圖像的信息解讀方式
2.1 關于圖像中“自然的、基本的意義”的認定

圖2 清康熙 焦秉貞繪圖、朱圭和梅裕鳳鐫刻《康熙御制耕織詩圖》中“織”圖之第七圖 “采桑”

圖3 左圖:清康熙 五彩人物故事圖盤(局部)荷蘭藏 右圖:清康熙 焦秉貞繪圖《康熙御制耕織詩圖》之 “采桑”(局部)
美國德裔猶太學者潘諾夫斯基把圖像大致詮釋為三步,第一步是為“前圖像志描述”,即對圖像“自然意義”的認定①。圖像的“自然的、基本的意義”也就是指畫面中的物體、人物、事件的具體形象以及人物的穿著打扮、神情舉止和細節環境的描寫等這些基本的、顯而易見地呈現的圖像信息。通過第一步驟“前圖像志描述”,可以打開故事解讀的第一扇門,以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清康熙1700-1720年景德鎮窯五彩人物故事盤(圖1)為例,書中一開始以常規的方法敘述瓷器中呈現的圖像信息:這件五彩瓷裝飾瓷上,有一個帶欄桿的花園,右側有一塊碩大的玲瓏石,兩棵樹旁站著一位男子和一個男童,樹下放著一個大水缸和舀水勺。而樹上還有一個脫了鞋的男童把他的鞋子和掃帚一起留在了地上。樹下的男孩正通過一條繩線拉著掛在樹枝上的紅色木桶。②”這段話里較為客觀地敘述了瓷器中呈現的“自然的、基本的信息”,并較完整地還原了人物、人物動態、景物、環境等。

圖4 清康熙 五彩人物故事圖盤(局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

圖5 明代 崔子忠《云林洗桐圖》(局部)絹本設色 縱160公分,橫53公分
2.2 對圖像傳統意義的認定

圖6 倪云林的形象比較 左圖:明代 崔子忠《云林洗桐圖》(局部)絹本設色 右圖:清康熙1700-1720 五彩人物故事圖盤(局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

圖7 盛器的比較 左圖:明代 崔子忠《云林洗桐圖》(局部)絹本設色 右圖:清康熙 五彩人物故事圖盤(局部)
之后,《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國明清瓷器》書中繼而又根據以上信息的描述,得出以下的判斷:這幅精心繪制的場景很可能描繪了采桑圖,即用所采桑葉來喂養蠶。③”同樣,齊魯書社出版的《中國陶瓷史》下卷中也有對這件五彩瓷的解釋為“清康熙五彩采桑圖盤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 ”④。而這個判斷的獲得應該是在潘諾夫斯基圖像學闡述的第二個步驟即“圖像志分析”之后形成的,也就是“對圖像傳統意義的認定。⑤”整個圖像學釋讀的過程中這個步驟至關重要,而由于對第一個步驟中存在信息理解是否準確、關鍵標志物的把握正確與否、圖像細節的觀察是否有遺漏、個人經驗、理解能力和知識背景來源的差異等眾多客觀因素,不同的觀圖者都可能產生不同讀圖結論。

圖8 掃把的比較 左圖:清康熙 五彩人物故事圖盤(局部) 右圖:明代 崔子忠《云林洗桐圖》(局部)

圖9 樹桿的比較 左圖:清康熙 五彩人物故事圖盤(局部)右圖:清康熙 五彩鳳凰梧桐圖盤(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的清康熙五彩人物故事圖盤的解說正是在這個環節中對意義的認定中出現了偏差,從而導致“這幅精心繪制的場景很可能描繪了采桑圖,即用所采桑葉來喂養蠶”這樣錯誤地判斷。這一點可以拿來歷代采桑圖的范本進行對比,由清康熙焦秉貞繪圖、朱圭和梅裕鳳鐫刻的版畫《康熙御制耕織詩圖》中“織”圖中的第七圖為“采桑”(圖2),這幅御制耕織詩圖是以上文(詩)下圖的形式呈現的,它與當時較為流行的版畫形式是相契合的。上面的康熙的御制詩文寫道:桑田雨足葉蕃滋,恰是春蠶大起時。負筥攜筐紛笑語,戴鵀飛上最高枝⑥。下方的版畫插圖中既有表現整個采桑的忙碌情景,又在圖畫的中心位置保留了南宋樓璹的“采桑”詩詞:吳兒歌采桑,桑下青春深。鄰里講歡好,過畔無欺侵。深籃各自攜,層梯高倍尋。黃鸝飽紫葚,啞咤鳴綠陰⑦。
2.3 圖像細節的比較:五彩瓷盤與版畫《耕織圖》中的“采桑圖”
版畫耕織圖中的采桑圖的確與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五彩瓷盤中的圖像有一定相似性,如:枝葉繁密的書、攀爬在高處的男童、樹下有接應的伙伴,樹上掛有或手中提著盛裝東西的容器。但仔細觀察卻不難發現,這件瓷盤中更有不少與采桑并不相干的圖像信息:首先,主體人物形象的區別。瓷盤中的主體人物是一位身著長袍衫,留有長須有著道古風范的文人雅士,這種著裝打扮與采桑葉、干農活的人物形象不相匹稱;其次,人物動作的差異。乍一眼看,瓷器中樹上的短衫、長褲打扮的男童在樹上攀爬,好似在摘采桑葉(圖3-左圖),然而,再對比《康熙御制耕織詩圖》中的“采桑”圖,不難發現,動態完全不同:“采桑”圖中樹上的男童在確保把自己穩固在樹杈之間的同時,一手提竹籃,一手有明顯將桑葉往樹下拋灑的動作,畫面中呈現了桑葉正在空中灑落的連續性動態(圖3-右圖)。而瓷器中卻沒有出現這個摘采和拋灑桑葉的特征性動作。
再次,細節標志物的差異。瓷器中,樹上懸掛了一只色彩亮麗的紅色木桶,而不是采桑用的籃子,這與《康熙御制耕織詩圖》中的詩文“負筥攜筐紛笑語”和“深籃各自攜”兩句詩文中的表述明顯是不符的。樹上的男童并沒有像采桑圖中摘采的是桑葉,而是在他的右手中正拿著一塊長條抹布,由于畫面中它與樹干的色彩十分接近,這個重要的圖像細節信息很容易被忽略了,缺失了這個重要細節信息就很容易造成對瓷器圖像的誤讀。
再進一步觀察疑點更甚:樹下為何放置大水缸和掃把(圖4)這與采桑圖似乎沒有直接關聯,詩文中的“負筥攜筐”的筥和筐才是盛裝桑葉的必要器物,而水缸的出現確實與圖像原境不匹配;最后,樹與樹葉圖像的差異。瓷器中兩顆樹上繁茂的樹葉與版畫耕織圖中的桑葉形象確實有所差異,瓷器圖像中是三或四辨的大片樹葉,而采桑圖中是散點式的小片桑葉,兩者的樹葉形象有著鮮明的區別。

圖10 梧桐葉的比較 左圖:清康熙 五彩人物故事圖盤(局部) 中圖:明代 崔子忠《云林洗桐圖》(局部)右圖:張深之正本《西廂記》木刻版畫插圖“緘愁”(局部)
2.4 圖像細節的比較:五彩瓷盤與絹本“洗桐圖”
正因為在進一步讀圖中呈現出越來越多的謎團,所以繼而轉向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更顯得迫切,再來比較一幅明代崔子忠的絹本“洗桐圖”(如圖5)與荷蘭藏的這件清康熙五彩人物故事圖盤:第一,倪云林的形象。絹本設色中的倪云林一副葛巾褒衣、長須飄飄、悠然自得的儒雅氣質與瓷器中的主體人物形象和氣質都具有極高的相似度(如圖6);第二,裝盛液體的容器。絹本“洗桐圖”中家仆用的是青銅盛器,瓷盤中為一件陶制水缸,雖然材質不同,但同為裝盛液體的容器(如圖7),即裝清洗梧桐樹的清水,這樣的圖像處理是合情合理的;第三,不可或缺的掃把。兩幅圖都出現了掃把這一圖像,為的是強調“洗”這個動作和力度。絹本中一位家仆正揮舞著掃把用力替梧桐樹清除污垢的動態十分明顯,而瓷盤中的掃把已經與脫下的鞋子一起置于樹下放著(如圖8),平躺著的掃把圖像似乎暗示著已經清掃完畢,掃把從樹上高空扔下,接著是用抹布再擦拭干凈,比起絹本的“洗桐圖”,瓷器中的抹布擦洗梧桐樹的動作更有韻味和遐想的空間。第四,樹桿與樹葉。不僅絹本的“云林洗桐圖”與這件瓷器中的樹桿具有相似的圖像處理方式,而且上海博物館藏景德鎮窯出品的清康熙五彩鳳凰梧桐圖盤中的梧桐樹的畫法和姿態也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高大粗壯的樹干、主桿上的樹瘤與錯落有致地橫線排列的樹干紋理的處理(如圖9)、以及畫面中與枝干相互掩映著滿密重疊、層次厚重的梧桐葉,都顯示了梧桐樹的特征。再對比梧桐樹葉,它們之間也具有極高的相似度,圖10中分別將清康熙五彩人物故事圖盤、明代崔子忠絹本設色的《云林洗桐圖》與張深之正本《西廂記》木刻版畫插圖“緘愁”一幕的局部進行對比,三幅圖中的樹葉都具備了鮮明的梧桐樹葉的特征,即三或四辨組成的大片梧桐樹葉,繪畫的手法相似,排列錯落有序疏密得當,這與采桑圖中是散點式的小片桑葉的畫法有著顯著的差異。
2.5 “圖像學闡釋”
倪亦斌先生在《從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理論看中國古代敘事畫釋讀的方法論問題》中:“解讀故事畫的第三步驟稱為’圖像學闡釋’,其目的是揭示圖像所體現的社會觀念,包括藝術家的心靈和當時社會環境有意無意留在畫面上的痕跡⑧。”根據以上圖像細節的分析,可以得出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即“洗桐圖”。歷史上這個圖像傳統并不鮮見,以明代畫家崔子忠的“云林洗桐圖”最負盛名。相傳元代著名山水畫家倪云林(又名倪瓚)愛潔成癖。平日里,不僅書房的文房四寶專門有兩個傭人負責經營和隨時擦洗,就連他院子里的梧桐樹,也要命人每日早晚挑水擦洗干凈。根據《石渠寶籍編》的記載:崔子忠所繪的《云林洗桐圖》絹本設色立軸畫表現的是葛巾褒衣、佇立假山前的倪云林,其中一位仕女佇立其后,手中端捧盥器。在梧桐樹前,一位家仆正注于盆,另一位仆人在揮手擦洗梧桐樹。并在畫中題詩為:“古之人潔身及物,不受飛塵,奚及草木,今人何獨不然?”。并稱贊倪瓚為:“吾謂倪之潔,依稀一斑,自好不染,世是人被其清風”。在這里,崔子忠用他的畫筆,借用倪云林“洗桐”這一表象事實,表達的是對倪云林潔身自愛的品性和其遠離塵垢高尚情操的贊賞。
因此,將這件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的清康熙五彩人物故事盤定義為“洗桐圖”更具有顯而易見的合理性。但由于《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中國明清瓷器》書中做了可能是“采桑圖”的猜想,這個“可能性的猜想”進而影響了作者做出這樣的發揮:這是一個描述農業和手工業活動的場景,它被廣泛地運用在卷軸和成套的中國木刻版畫插圖中,這個圖像不僅在中國國內很受歡迎,還經常出現在西方人的紀念品當中,……這個圖像場景的描述來源于木刻版畫插圖,這件瓷盤可能屬于《耕織圖》中“織圖”中的一個生產環節。⑨”潘諾夫斯基圖像學中闡釋的第三個步驟是指:探究圖像背后的歷史文化,即通過藝術史和文獻知識來辨認藝術品所表現的圖像,并通過文化背景中研究圖像來闡發圖像中所折射的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⑩。正是由于在第二個環節 “圖像分析”中認識的不嚴謹或不全面,書中對荷蘭藏康熙五彩瓷盤的“圖像傳統意義的認定”出現了嚴重偏差,而這個至關重要的環節又導致了第三個步驟“探究圖像背后的歷史文化”中最終會有錯誤的判斷,并且繼而為這個錯誤的判斷尋找了“順理成章”的理由。因此,圖像闡述的第二個步驟“圖像志分析”顯得至關重要,正因為分析得當、圖像細節比對合理,才能夠做出接近符合故事真實原境的正確判斷。
3 結語
綜上所述,從用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三個步驟理論來分析瓷器上敘事性故事圖像是具有非同凡響的意義。它在對圖像中“自然的、基本的意義”的認定、對圖像傳統意義的確認、對圖像信息的細節合理分析以及對圖像背后的歷史文化所折射的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認定的方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每個環節緊緊相扣,是促使圖像得以形成正確判斷的關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荷蘭國家博物館藏這件康熙五彩瓷盤找不到可以完全臨摹和借鑒的繪畫或版畫粉本,它更多體現地是景德鎮瓷畫藝人對“洗桐圖”傳統圖像的再創作和再設計。它的微妙之處在于既借鑒了版畫“織圖-采桑圖”中的人物在樹上的構圖形式,但又有將木桶掛于樹上、抹布擦洗動態等使之更加符合生活常理、體現藝術家細心觀察和體現的創新處理;另外,有別于崔子忠絹本繪畫中“有人在掃樹和有人用盆在倒水”的分散動態處理,而是更集中強調圖像的主題即“洗”的動作,人物更加簡練、圖像視覺更加集中、敘事主題更加鮮明,這些獨具匠心的圖像細節的創新處理無不體現了景德鎮窯瓷畫藝人對在圖像被充分解讀的基礎上高超的圖像駕馭能力。
注釋
① 倪亦斌《從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理論看中國古代敘事畫釋讀的方法論問題》一文載自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編《形象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5上半年 第4頁
② “Decorated in famile verte enamels with a fenced garden, a large garden rock, two trees a man and a boy besides a large jar with a ladle. Another boy has climbed into the tree, leaving his shoes and a broom on the ground.Over a branch hangs a bucket on a cord held by the boy on the ground”. 選自:Christian J A Jorg《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Amsterdam——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中國明清瓷器)》1997 Philip publishers Limited 第 P158 頁
③ “This nicely and carefully painted scene probably depicts the gathering of mulberry leaves for feeding silkworm同上 第P158頁
④ 方李莉《中國陶瓷史-下卷》濟南,齊魯書社,2013.12 第 925 頁
⑤ 倪亦斌《看圖說瓷》中華書局 北京2008.1第26頁
⑥ 【清】焦秉貞繪 張立華注釋《康熙御制耕織詩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12 第72頁
⑦ 【清】焦秉貞繪 張立華注釋《康熙御制耕織詩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12 第72頁
⑧倪亦斌《從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理論看中國古代敘事畫釋讀的方法論問題》一文載自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編《形象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5上半年 第4頁
⑨ “Scenes of 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extensively illustrated on scrolls and in sets of Chinese woodblock prints, were very popular in China and were also bought as souvenirs by Westerners……The scene depicted here will also have been based on a woodblock print and this saucer probably belonged to a set which included other stages in silk production. 選自:Christian J A Jorg《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中國明清瓷器)》1997 Philip publishers Limited 第P158頁
⑩ 倪亦斌《看圖說瓷》中華書局 北京2008.1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