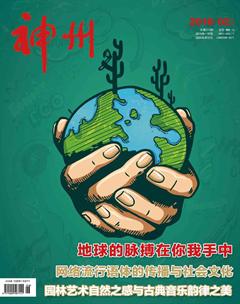《隆中對》戰略決策SWOT分析得失談
朱禹霏
摘要:《隆中對》無論在正史還是小說中,都是諸葛亮一生中的精彩手筆。歷來為世人所稱道,但其終未助劉備成就霸業,匡扶漢室。可見,其也存在局限性。本文用SWOT分析法就《隆中對》存在的不足進行分析,從而對諸葛亮進行更加客觀的歷史評價。
關鍵詞:隆中對;諸葛亮;SWOT分析法
《隆中對》作為戰略分析和戰略決策的一篇軍事論文,不論在軍事史上還是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它都是精彩一頁。欲成就霸業屢遭失敗的劉備,三顧茅廬拜訪年僅27歲自詡臥龍的諸葛亮,為他分析天下形勢和制定稱霸的戰略規劃,劉備如醍醐灌頂,豁然敞亮,如遇救世主一般,把諸葛亮拜為軍師,言聽計從。聯吳抗曹,獲得了赤壁之戰的勝利,取得了戰略要地荊州作為根據地;其后又挺進川蜀之地,奪取益州;步步為營,終于與曹操、孫權三足鼎立,做了蜀漢皇帝。劉備從一個織席賣鞋的小商販,當上了至高無上的昭烈皇帝,真是“一對足千秋”[1]!
諸葛亮的才華智慧,在中國歷史上有口皆碑,輔佐劉備從如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到割據一方,與曹吳割據形成鼎足的三分天下態勢,奠定了北伐曹魏的基礎。按照《隆中對》的決策,劉備白帝托孤先諸葛亮遺恨而早逝,諸葛亮鞠躬盡瘁病逝北伐,復興漢室沒能實現!誠如諸葛亮所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嗎?
SWOT分析法,就是態勢分析的方法,基本做法是把所關注的對象按照優勢、劣勢和外部的機會和威脅等基本要素,通過現場取樣逐一列舉歸并,作出矩陣形式的排列分析,然后從整體入手,把各種要素對應比較,從中找出有效利用機遇化解風險的可能,實現目標的達成。運用這種方法,結合《隆中對》進行思考,也許對其得失會得到一些新的啟迪。
《隆中對》前半部分是高瞻遠矚的形勢分析。在分析中優勢、劣勢、機遇的分析邏輯演進,無懈可擊。當時的勢力范圍是“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2]。劉備本身是“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而荊州和益州是戰略地位十分突出,劉表、劉璋不可能長期固守,利用他們的暗弱取而代之,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和戰略后方。《隆中對》后半部分是戰略策。軍事方面巧取荊州作為根據地,然后謀取益州作為戰略后方,然后等“天下有變”,兩路出擊,北伐中原,一路以劉備帶主力為主攻方向“出于秦川”,另一路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構成正奇相輔的格局,深合大戰布局,如果形成這樣的局面,的確有成功的可能。內政方面“內修政理”,逐步增強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外交方面“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
反復讀來,《隆中對》“高瞻”到位,“遠矚”不足。應用SWOT分析法就是威脅、危機認識不到位,致使決策和實施多有敗筆。
首先,沒有認識到劉備不是帝王之才,空有匡扶漢室的雄心大志,缺少一統天下的雄才大略。因為關羽之死,他忠言不聽,揮師伐吳,致使夷陵之戰大敗成為蜀國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夷陵之戰是三國歷史上吳蜀政權為爭奪戰略要地荊州南部五郡(南郡、長沙、零陵、桂陽、武陵)而進行的一場戰爭,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守為攻的積極防御戰例。該戰役是東漢末年三國歷史上三大戰役之一,也是三大戰役的最后一場。關羽丟失荊州,敗走麥城,斬首丟命,使劉備地人兩亡,損失重大。從常理講,大丈夫能屈能伸,應該忍辱負重,痛定思痛找出失敗的原因,聽人良言吸取教訓,厲兵秣馬進行反擊才是。他卻匆忙稱帝,開始調兵遣將,御駕伐吳。出征前為集中兵力,命駐守閬中的張飛趕去江州與他會合,可張飛還沒來得及出發,在酩酊大醉中就被部下生殺了,并將腦袋送到東吳請功。這一系列的失敗源于狹隘的桃園結義的兄弟情誼,導致損兵折將,從此再也沒有收復戰略要地荊州的人才和機會。
其次,沒有認識到駕馭悍將艱難性,執行力極低,不能有效達成戰略目標。比如關羽本身就是個心高氣傲的人。赤壁之戰后巧取荊州為家,把諸葛亮費經心思謀得的唯一一塊根據地交給他鎮守。劉備帶兵西進攻奪西川開辟戰略后方,戰將立功,他心里極其妒忌,丟下重要的戰略基地,私自去攻打樊城。曹操按照司馬懿的計策,雙管齊下,正面五萬精兵馳援樊城,迎戰關羽;暗面修好聯結吳國,孫權神不知、鬼不覺決計攻襲荊州。雖然關羽留下重兵防范,結果被吳將呂蒙辭職,使驕兵關羽麻痹丟失荊州,只得狼狽逃往麥城,成為吳軍的階下囚并慘死。再如街亭之戰,這是諸葛亮的北伐第一戰,親自委任參軍馬謖統領諸軍,在軍事咽喉重地街亭攔截曹魏將領張郃。他根本不聽諸葛亮叮囑,丟掉懶于生存的重要水資源,登上南山據守,主觀臆想,居高臨下,勢如破竹,轉守為攻,一舉大敗張郃,建立奇功。結果水源被張郃切斷,圍而緩戰。無水的千軍萬馬不戰自亂,張郃把握戰機,乘亂攻山,使易守難攻的攻山之變得易如反掌。街亭易主,諸葛亮進退沒有根據地,前不能進,后無保障,只得半途而廢,退往漢中。
再次,沒有認識到根據地荊州的選擇與戰略后方益州的天塹逾越之難,犯了“風水”大忌。《隆中對》有一段話,意思是說,“跨有荊益”,聯合孫權對付曹操,等待機會,“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3],如此兩路齊出,“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4]。然而毛澤東在讀到這里時,卻一針見血地指出:“劉備其始誤于《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5]。荊、益兩州東西相隔上千里,中間有九轉肥腸式的大巴山蜀道阻隔,當時的通訊技術和交通水平,不可能有效協調和指揮;大兵未動,糧草先行,跨天險長途作戰,后勤保障很難有效供給,獲勝系數不高。當年司馬懿就曾說:“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6]。
最后,沒有認識到“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是一廂情愿的畫餅充饑,沒有穩定的戰略后方。“南撫”變成了南征,“七擒七縱”的佳話僅是小說的精巧構思而已。“西和”變成了平西。西北少數民族以游牧為主要的生存方式,與農耕為主的中原王朝沖突長達兩千多年,是世界全球范圍內最長的文明沖突。他們生存條件單薄,畜牧業的經濟結構,絲毫不穩定,風調雨順,基本實現畜牧和人口發展的供需平衡。當異常氣候出現,尤其是干旱年景,糧食草料及其短缺,就東征或南下搶奪農業民族,幾乎是游牧民族度過危機求得生存的有效良方,蜀國政權也不可能幸免。諸葛亮的西征雖然收獲了猛將馬超,但得遠大于失。可以說割據西部的蜀國政權四面受敵,由盛而衰最終滅亡只是時間問題。
由于《隆中對》對危機、威脅、地緣和人力資源的認識不足,到其結尾樂觀的說到“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7]由于危機、威脅的認識不足,過于樂觀,作出兵分兩路的決策必然削弱自身優勢;由于地緣認識的不全面,只能以武打求統,武打求和,武打求穩,嚴重削弱綜合實力,延誤北征時機;由于人力資源的認識不足,忘卻桃園結義一統天下的宏圖,為“兄弟”復仇傾巢東征,元氣大傷;不能知人善任,失掉戰略根據地,一出祁山,無功而返士氣大損,雖然屢戰屢敗共六度出祁山,百折不撓,也只是盡力而為之舉。
但是,《隆中對》的不足,并不有損于諸葛亮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諸葛亮的人品是極其偉大的。杜甫發自內心贊頌“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這種贊揚,是對諸葛亮知恩知遇感恩情懷的贊揚;是對諸葛亮知恩圖報,鞠躬精粹、死而后已偉大人格的謳歌與緬懷。用諸葛亮自己的話講,便是“鞠躬盡力,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8]。我敬仰、崇拜諸葛亮勇于擔當責任的人格。
參考文獻:
[1]“兩表酬三顧(上聯),一對足千秋(下聯)”,是明代文人游俊題在"三顧堂"正門的對聯;(成都武侯祠三顧堂聯)。
[2]原文引自《三國志·諸葛亮傳》。
[3]《隆中對》
[4]《隆中對》
[5]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06頁;(《人民網.文史》)
[6]網絡《司馬懿名言》
[7]《隆中對》的戰略“誤區”黃樸民,《文史天地》 2015
[8]諸葛亮《隆中對》試析 楊榮新,《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 ;(諸葛亮《后出師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