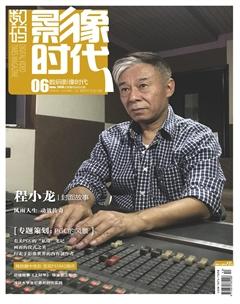淺談大學生紀錄片創作實踐
郭振元



在電視紀錄片的創作領域中,大學生是一個十分活躍的創作群體。近年來,國內綜合類高等院校里自覺參加紀錄片創作實踐的大學生群體,B經由新聞傳播學科、戲劇與影視學科等相關專業的學生逐步拓展到其他學科。他們在創作實踐中追蹤時代步伐,以鮮明的紀實美學為基礎,能動地表達著對現實的關注和理解,作品表達充滿入文關照。
一,大學生紀錄片崛起的背景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紀錄片經過快速發展,表現的題材范圍日益廣泛,類型多樣,制作上,形成多部集、大型系列化的紀錄片形態。從傳統媒體到全媒體的復合傳播結構中, 大批優秀的紀錄片以其獨特的品質影響著社會審美思潮的變化,從深度到廣度,為大眾構建起種認知紀錄片的審美觀念。縱使個不懂專業知識的普通觀眾、 個沒有專業背景的大學生,他們有可能說不清紀錄片是什么,但基于視覺經驗,都會判斷出什么是紀錄片。
進入21世紀10年代,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為紀錄片注入新的表達因素。以5D2相機為標志的攝影器材的變化,以電腦為載體的數字非線性編輯的普及應用,為個人紀錄片的前后期創作建構了完善的拍攝與編輯系統。現成的藝術表現媒介,人們用時代提供的形式和理念隨手便可以將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件記錄下來。包括當下人們用手機攝制的紀錄短片,較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普通民眾使用小型DV攝像機進行拍攝,從敘事到體驗,紀錄片的生產方式、表現形式和紀錄片作品多元化的傳播途徑,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在紀錄片領域的創作實踐。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高校大學生紀錄片創作悄然崛起。
時至今日,在紛繁的紀錄片創作格局中,大學生將視野投向社會生活,對現實的觀察與記錄,制作紀錄片的數量之多不勝枚舉,其中不乏具有獨創性、內涵深刻的作品。大學生紀錄片創作呈現出鮮明的特點
其一,與媒體紀錄片導演和社會獨立制作人不同。在校大學生以學業為主,主要利用寒暑假及課余時間拍攝紀錄片,因此,紀錄片創作帶有很強的實踐性質。雖然大學生缺少時間,普遍缺少經費支撐,但并不妨礙他們秉承獨立制作精神,勤于思考、注重表達,形成了以個人形式獨立制片的紀錄片創作面貌。
其二,在題材范圍和表現內容上,大學生拍紀錄片有其局限的 面,比如,與重大題材無緣,難見宏大敘事,很少涉足歷史題材、文獻類、人類學和自然科技類型的紀錄片創作。總體而言,大學生紀錄片以現實題材為主,創作風格具有鮮明的紀實特點,作品形態以紀錄短片創作為主。盡管還存在著創作上的不足,但整體的作品風格樸實無華、自然、清新。
其三,大學生制作的紀錄片極少在媒體電視臺播出,主要通過自媒體和視頻網站進行傳播,受眾相對較少。
其四,大學生紀錄片的選題與媒體紀錄片的取材范圍和題材價值取向上存在較大的差異。然而,正是對題材選擇標準和選題價值判斷上的不同,使大學生紀錄片的選題范圍既受到制約又得到拓展。在寬泛的選題范圍內,大學生往往從自己最熟悉的人物、事件入手,記述人物故事的選題占有很大比重。在普遍而自覺的意義上,這種題材取向實際上是對20世紀90年代“聚焦時代大變革,記錄人生小故事”、“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紀錄片審美創作和人文精神的種續接。
二。大學生紀錄片中的人文精神
有人就有故事。在紀錄片創作中,每一個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唯性。他們的人生經歷、生活境遇和生存狀態無不呈現出獨有的人生質感,為紀錄片選題敞開了自由選擇的創作空間。不過,基于題材價值判斷的標準一一思想性、歷史性、普遍性、可視性等衡量選題的幾大核心要素,以及收視率的考量,生活中的許多普通人物、事件很難進入媒體紀錄片的視野。但面對俯拾皆是的選題,大學生作者沒有這種疏離感。大學生貼近現實生活,捕捉現實題材選題的深入和覆蓋廣度遠遠超過了媒體紀錄片,把很多普通人的生活情境轉化為紀錄片中被講述的故事。
表面看來,大學生紀錄片記述的普通小人物微不足道,人物的生存狀態、日常瑣事和主題內容也許顯得平淡無奇。可是這些平常的人與事旦與社會現實聯系起來,恰恰可以從這些普通人的身上挖掘出蘊含時代精神的主題。僅以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臺《紀錄·視界》欄目近年來學生拍攝的紀錄片為例,可以看到人文性的表達。
l、紀錄短片《第支書人物札記》(主要拍攝設備佳能6D)
《第支書人物札記》中記述的王慶祝、龍曉穎、謝江、田峰、李立超、王耀宗、楊俊都是湘西吉首市普通的基層工作者,自201 5年初,他(她)們先后到7個貧窮的苗族村寨擔任第支書,平日吃住在村寨里。經過幾年扎實有效的工作,修路、建房、通過網絡推銷農產品,展開文化教育建設,帶領村寨鄉民逐步擺脫了貧困面貌。在精準扶貧的工作中,每 個人物故事既平實又生動。
全片采用白描的手法勾勒人物形象,除了用字幕詳細交代時間、地點、人物身份和村寨的信息,不加任何畫外解說。該片用樸實的鏡頭語言和畫面同期聲呈現人物的情感狀態、精神面貌、性格、動作,表現人物與事件的真實形態。
2、紀錄片《閱兵日》(主要拍攝設備佳能ECS5D2、尼康D750等)
2015年9月3日,北京隆重舉行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70周年閱兵典禮。這天,5個學生攝制組在北京5位抗戰老兵(趙振英、尤廣才、葉子良、石兆祥、沈少忱)的家中記錄了他們 天的生活。趙振英老人98歲,是國民革命軍新6軍14師10團l營營長,抗戰勝利后,他率領全營官兵參加了1945年9月9日在南京黃埔路陸軍總司令部受降典禮儀式的警衛工作。沈少忱老人在兩個多月前逝世,攝制組拍攝了他的兒女、孫女。這天上午,老人們守在電視前,觀看著中央電視臺現場直播的閱兵儀式,暢談自己的抗戰經歷。另一個攝制組在北京城區的幾個地方拍攝街頭觀看閱兵式的市民游客、街道氛圍。
新聞工作者有句至理名言“今天的記錄就是明天的歷史。”大學生從生動可感的人物切入個具有歷史意蘊的主題,人物與正在發生的歷史事件有種深入的現實聯系。如果說,中央電視臺全程直播的閱兵儀式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國家記憶,那么,這部紀錄片所記錄的幾位抗戰老兵的日常生活更具有 種共時性的鮮活的歷史史料價值。因為“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現實因為歷史而更加的厚重、真實。
3、紀錄片《非典余生·武震》(主要拍攝設備索尼HVR-27C小型高清攝像機)
2003年,年輕的實習醫生武震參加治療北京第例“非典”病人時不幸被傳染,經過全力救治才生存下來。2011年深秋,編導走進武震的病榻生活。當時,武震正處于重度抑郁癥階段,甚至想過自殺。她能否挺過非典后遺癥病痛的折磨,恢復戰勝病魔的信心, 切都是未知的。隨著時間的流逝,到2013年,逐步擺脫了重度抑郁癥的武震做了置換股骨頭的手術,離開輪椅,不僅能正常行走,她還學會了開車。兩年跟拍期間,編導又認識了些非典后遺癥患者,了解到這個群體艱難的生存狀態,深入采訪了方渤、邊曉春、李朝東鮑寶琴夫婦,走訪望京醫院的陳立衡醫生,探討治療非典后遺癥患者的問題。在姊妹篇《非典余生·方渤》中,展開一個也許本不該由大學生觸碰的話題面對個特殊的弱勢群體,該如何完善社會醫療保障和救助機制?
4、紀錄短片《我的初中同學》(主要拍攝設備佳能6D)
《我的初中同學》講述了同齡人的故事 位女同學初中尚未畢業便輟學,17歲就做了母親。由于早婚早育,她既沒和丈夫領取結婚證,也沒有為女兒上戶口。2014年,編導在家鄉的小鎮上偶然遇到她時,她的女兒已經3歲了。另 位女同學高中畢業后在鎮上的企業當會計,面對鏡頭,她第次坦言自己的身世由于是女孩,出生后便被生父拋棄,所以她和養父的感情極深。2015年寒假編導再次回到家鄉拍攝時,這位同學由于養父病故,離開了讓她傷感的小鎮。做了母親的同學對今后的日子充滿夢想好好掙錢,爭取買輛車,等生活改善了,就可以生小二啦!該片沒有對農村常見的早婚早育現象進行價值判斷,而是用最單純的紀實手法客觀記錄了人物真實的生活情狀。
大學生記錄同齡人的生活狀態,同感式的貼近觀察與記錄,很多選題都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再如《光影路上》《BBOY的藝考》《復讀生》《衡中晝與夜》《高中生活》《我的金帆樂團》等紀錄片,大學生錨定感同身受的“高考”、“藝考”的熱點題材,跟蹤人物故事,透視中國高考制度下眾多學子奮進求學的歷程,每部紀錄片中記述的真實故事都猶如“高考”命題下的切片,支撐起主題與話題的重量。
5、紀錄片《洞庭之殤》(主要拍攝設備尼康D750)
隨著洞庭湖水質污染嚴重,湖區面積縮小,湖中的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江豚僅存120余頭。為保護漁業資源,拯救瀕危的江豚數量,漁政部門逐年延長洞庭湖春季禁漁期。禁漁期間成為洞庭湖周邊漁民最難熬的日子。2013年5月,編導跟隨岳陽市江豚保護協會的徐亞平等志愿者夜巡湖上,現場抓拍到夜間違禁捕魚的漁民。7月,禁漁期結束,編導跟隨漁民何光紅出湖捕魚,漁業資源的銳減,通宵撒網,整個夜晚只捕到一條魚。一年后,何光紅賣掉漁船,到挖沙船上打工。創作者沒有回避洞庭湖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客觀展示了當地漁民的生存現狀、江豚的生存現狀,提出人與自然如何和諧發展的命題,立意深刻,具有普遍的人文價值。
三。拓展大學生的題材范圍和類型
隨著大學生紀錄片創作實踐的深入,題材范圍逐步拓展到歷史文化題材和人類學紀錄片領域。大學生觸及歷史、文化題材,選題取材著眼于事物,以小見大,從微觀的視角切入事件,提煉主題。如紀錄片《走進科舉匾額博物館》,透過塊塊科舉匾額,反映中國 千三百年科舉制度最終“成于制、毀于度”的歷史現象。紀錄片《萊尼·里芬斯塔爾》通過解讀《意志的勝利》、《奧林匹亞》等文本,表現里芬斯塔爾這位備受爭議的紀錄片導演,并在紐倫堡對話今日的德國民眾。紀錄片《凱綏·珂勒惠支》介紹了珂勒惠支生的藝術創作,講述魯迅與珂勒惠支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新木刻運動的巨大影響。在口述紀錄片《我的1977》(15集)和《知青歲月》(10集)中,大學生與受訪者面對面地對話,一個真實的并不遙遠的歷史帷幕被撩開。“文革”中些許的人與事發人深省地延續到眼下,學生由此感知段陌生的歷史,并在剪輯臺上開始解讀這段歷史。
較之歷史、文化題材,人類學紀錄片創作會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
少數民族地區的大學生帶來家鄉的選題,不僅豐富了題材內容,在實踐方面也自然延伸到人類學(民族志)紀錄片創作領域。特別是那些具有民族文化特質的生活事件,為大學生遵循人類學紀錄片的創作理念和拍攝方式提供了創作空間。不過,雖然這些選題可歸入人類學紀錄片創作,但從嚴格意義上的人類學紀錄片的概念和嚴謹的工作方法來衡量,作品創作還存在著不小的距離,其制約因素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在校大學生缺少基本的田野調查環節——深入某地區,對一個民族的人種、社會經濟、歷史、宗教、文化形態的構成進行不少于 個年度周期的長期觀察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并將觀察結果隨時用影像客觀地記錄下來。其次,參加拍攝的學生缺乏有關人類學基礎知識的學習和專業技術性訓練。再次,人類學工作者攝制紀錄片屬于種學術研究成果。他們在長期的觀察過程中對某個族群的社會組織、生活習俗、生產方式、宗教信仰和民俗儀式等日常生活進行系統觀察記錄,記錄下來的內容與細節可以充分詮釋學術理論研究。最后點,人類學工作者攝制的目的不是為了送電視臺播出(雖然也會制作播出或參加國際人類學紀錄片的展映),而是表述文本。
盡管大學生很難嚴格遵循影視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方法,進行年度以上周期的調查和跟蹤拍攝,但是,卻并不妨礙學生帶著人類學的基本觀點和視角關注民族文化,體察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選擇生活事件拍攝制作紀錄片。
比如,表現苗族巴代文化的紀錄片《巴代·壺》,通過完整地記錄家庭舉辦“還儺愿”儀式的全過程,展現湘西苗族村寨至今不衰的祭祀遺風。紀錄片《婚日》記述了貴州省從江縣小黃村侗寨沿襲600多年的傳統一一侗寨所有成婚男女都在每年農歷臘月二十六這天舉辦婚禮的古,婚禮持續3天。紀錄片《出壩》記述了黎平縣勝利村侗寨年度的出壩儀式,勝利村侗寨出壩儀式,其獨特性在整個黔東南地區的侗族聚居地都是絕無僅有的祭祀活動。大學生置身事件現場,遵循觀察式的拍攝方法客觀地記錄人物、事件,拍攝中多采用信息量豐富的長鏡頭。如《婚日》中巫覡為新娘祭祀作法儀式的過程,其中的 個機位采用長時值的拍攝方式,對巫覡進行的各項祭祀環節、吟誦過程、動作、細節進行全過程地記錄。在敘事結構上,按照事件發生、發展的自然時間過程和情節走向來架構紀錄片。
人類學紀錄片創作有狹義和廣義之分。中央民族大學莊孔韶教授認為,按照嚴謹的人類學的理論方法攝制的影視人類學紀錄片,作者的首要目的是為了自己研究地方文化、民族文化,而不是送電視臺播放;寬泛地講,人類學紀錄片可以以所有的人為拍攝對象。
拍攝人類學紀錄片,對大學生而言最重要的是 種創作理念和價值觀念的調整。大學生自覺遵循影視人類學的理念走進事件現場,帶著文化人類學的視角體察人物、事件所蘊含的民族文化信息、文化細節,從表面的觀察與記錄走向探尋生活本質的體驗觀察和思考,進 步探究事物之間的內部聯系,學會如何進行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從觀察與思考中提煉觀點。有助于養成種文化審美的創作觀念。
紀錄片是一個蘊涵深厚人文精神的片種。大學生深入社會現實生活,在創作實踐不斷地認識他人,認識自我,用鏡頭記錄還原真切的現實世界,追求一種獨立言說的可能,不斷塑造著紀錄片的品質。其實,所謂紀錄片獨具魅力的品質,恰恰出自紀錄片作者的品質,是創作者思維品格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