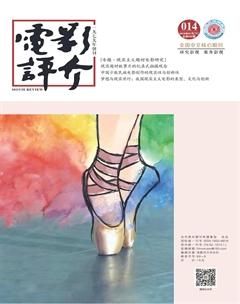國產青春電影的敘事新模式
薛宇杉
2011年由柯震東和陳妍希主演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在內地大受追捧,繼而青春主題類電影如《致青春》《梔子花開》《匆匆那年》等紛紛上映,國產青春電影迅速成為繼國產喜劇電影、愛情電影、恐怖電影之后的第四大類型的電影,雖然這類型的電影非常多,但就影片的質量而言,其水準較為欠佳。觀眾在觀影之后發現此類電影情節大同小異,充滿著各種斗爭、懷孕、流產等,無法引起觀眾的共鳴,久而久之對這類型的電影再也沒有觀賞興趣。《七月與安生》上映期初,也受到了這種氛圍的影響,并不被觀眾看好,即便有著名監制陳可辛加持,也無法引起人們的期待。
《七月與安生》2016年9月11日首映以來,口碑不斷攀升,票房高達1.67億元人民幣,同時電影的導演以及演員馬思純、周冬雨均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成績十分喜人。《七月與安生》之所以獲得如此好成績,不僅僅只在于對原著小說的成功改寫,且創制者調整了整個電影的敘事策略,使得觀眾更易接受。影片一方面成功地沿襲了人物塑造的優點;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一反傳統的屈于男權的局限,主張女性自由、獨立的人生態度。
一、 電影故事結構及影片節奏
作為一種敘事形式,電影必須能夠告訴觀眾整個故事中發生了什么從而引起觀眾的思考;因而,電影是超越空間的現實性和時間的單一性的。在電影的拍攝過程中,通過各種鏡頭的合理運用來處理人與時間空間的關系,不同的電影表達會有不同的敘事方式。
電影以同名小說《七月與安生》為藍本,利用小說的形式將整部電影分為幾個不同的部分,采用敘事者七月的講述構造了一個十分新穎的敘事結構。首先導演通過倒敘的方式將過去的時間和任務連接在一起,電影的敘述存在兩條時間線,其中一條是過去的時間線也就是以七月與安生小時候的生活為主;另一條是現在的時間線也就是安生與家明生活的時間線。這兩條時間線在電影中穿插著進行,使得影片的節奏十分緊湊,七月與安生的成長過程與長大狀態之間的過渡也十分自然,尤其是在二人相互寫明信片的過程中,利用明信片的內容將故事情節慢慢引出,而在電影節奏加快的時候故事的進行發展也十分明確,情節的推動相當自然。電影故事情節非常簡單,講述了一對性格迥異的女孩從小一起長大,之后愛上了同一個男生,所發生的一系列故事。從小聽話安穩成績優秀的七月與叛逆不羈渴望關懷的安生,二人因差異成為好友,卻又因差異出現隔閡。電影的大部分時間都放在了回憶的部分,但這種回憶并不是將過去的經歷事無巨細地進行回憶,而是有選擇性的。人們只是記住他們想要記住或者在意的,印象深刻的事情,由于這樣的敘事方式使得回憶模糊不清,有時又會加上當事者七月與安生的主觀印象,因而也就為影片的表達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
影片中的回憶并不是通過口述的形式進行的,而是借助小說來進行;充滿虛構性的小說可以增加敘事者的想象力,將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遺憾人為彌補,因而電影的結局也不是單一的。例如七月在現實生活中的結局是難產而死,而在小說中的結局卻是過上了其向往自由的生活,前者是不可不接受的現實,后者卻是敘事者想實現的愿望,亦表現出安生對于摯友七月的希望。[1]電影在敘事的同時也要引起觀眾的共鳴,喚起觀眾的情緒,因而觀眾在七月過上了自由的生活這一結局中情感可以得到一定舒緩。這樣的結局使得電影的主題得以升華,兩個主角——七月與安生都過上了對方想要的生活,這兩種生活在結局中交融,兩個摯友,兩種性格,這兩種對立的性格在影片和小說的最后獲得和解的過程也是自我認知的過程,影片中展現出來的個人的生活方式的變化也會引發觀眾對自身的思考。
二、 人生互換展現多重性格
《七月與安生》與其他的國產青春類電影的主要不同在于人物的設計中增加了互換人生的情節。通過人生的互換,兩個性格迥異的女主角七月與安生展現出自己性格的另一面,使得人物形象更加豐滿,性格更加多面化。影片塑造了兩個性格截然不同的女主角,表面上七月是一個乖乖女,實則叛逆囂張;而安生表面上特立獨行,實則向往安定。在對人物性格的渲染中,電影突出了安生命運的悲劇色彩,揭示了在愛情、友情和自由面前,女性沖破世俗束縛的心理狀態。影片在傳承小說中雙女主性格迥異的人物設置的基礎之上,為了適應當代女性對自我價值的肯定,打破原小說的局限,適當調整了部分情節,因而人物性格也更加立體多彩,且多重的敘事策略如插敘、倒敘等使得電影更具觀賞性,同時進一步強調了女性在生活中要尊重自己內心的想法、情感獨立、自由選擇的態度,使得觀眾在觀影之后對自我認知進行更深層次的探索。
影片的前半部分,七月與安生的性格截然不同,涇渭分明;七月乖巧、聽話,安生叛逆,不羈;而從兩人的生活互換之后,她們的性格開始交融,七月成了不羈的安生,而安生則成了安穩的七月。小說主要是以七月的視角作為敘事角度,因而讀者在閱讀小說的時候對安生的心理了解較少,而在電影的敘述過程之中,七月與安生的視角不斷切換,使得觀眾更能把握二人的內心世界,特別是在影片的推進過程中加入的大量旁白進一步展現了七月、安生兩人的內心。[2]同時導演采用鏡像的處理手段不斷地暗示出兩人的關系不僅僅是閨蜜情,而當影片最后二人又合為一體,暗指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乖巧的七月與一個叛逆的安生,因此有時候人們會向往安定的生活,按部就班,而有時則又會向往自由的生活,但這種自由的生活與當前社會的主流節奏不同,想要得到這種自由可能需要極大的代價,就像追求自由的七月最后的結局一樣,夢寐以求的自由生活依舊會被安穩的生活取代。
三、 結局的反轉與細節的處理
影片出現了三個重要的反轉,據導演陳可辛說,最初他是十分反對這樣設置的,因為他覺得在兩個小時這么短的時間內,觀眾無法接受多次的反轉,這會削弱觀眾的觀影興趣,降低觀影體驗。但在試映中,200位觀眾都表示非常喜歡這樣的敘事方式,于是這三個反轉都保留了下來,而當電影上映之后證明了這樣的方式是成功的,而觀眾之所以覺得反轉很合理,要歸功于影片前半段的細節和線索處理。
首先,影片第一個結局的設定中,一向叛逆不羈追求自由的安生最后卻與一個平凡的男人結婚生子,過上了平淡的生活,而一向安穩乖巧的七月卻由于未婚夫家明的逃婚而過上了流浪的生活,兩人生活發生了互換,這樣的結局看似無奈,但又好像是必然的結局,這樣的結果或許并不是她們本心的選擇,而更多是為了實現自我和對方的救贖。
其次,在另一個結局中,安穩乖巧的七月變得更加勇敢,為了自己的逃婚能更合理,她鼓勵未婚夫家明逃婚,在這個結局中安生承擔起所有的責任,幫七月撫養了她和家明的孩子,過上了平凡無趣卻十分安穩的生活。在這個結局中,七月與安生的生活好似發生了互換,性格也發生了互換,不同于第一個結局,這個結局完全是主人公自由選擇的結果。看似安穩乖巧的七月內心卻并不安分,內衣是影片中的重要線索,當安生問七月為什么穿那么老氣的內衣時,七月只是回答,是媽媽讓她穿的,七月只能無奈接受媽媽的安排;并且在倆人的第一次見面時,其實是七月砸的消防栓,因而她表面上的乖巧聽話只是為了哄大人們開心而已。而安生,由于自小父母離異缺乏家庭的關懷,亦是利用表面的不羈和叛逆掩飾自己內心的虛弱,在影片中家明送給她的玉墜自始至終都沒有摘下來過,即使是后來又換了一個鏈子,依舊帶著這個玉墜,說明她的內心向往的是非常安定的生活,安穩的家。
而另一個結局也就是故事的真相中,結束生命的是七月,第二個結局只不過是安生騙家明的,雖然這看似是一個殘忍的結局。[3]但七月和安生兩人之間的關系也從死亡中得到了升華,影片的結尾兩人照鏡子的鏡頭可能是暗示出叛逆的安生已經變成了安定聽話的七月,安生也會代替七月活下去。或許是覺得這樣的結局對觀眾來說太殘酷,因而影片的最后導演又增加了一個結局也就是第一個結局,通過安生寫的小說中可以看出,七月自由地無拘無束的生活著。
這樣的三重反轉對觀眾來說是非常好的體驗,更難得的是影片的每一個結局都非常的理性且不會顯得突兀。不同于原創小說,導演通過向觀眾展現出三個結局,使得影片的敘事內涵得到了深化。從影片的敘事內涵角度來看,其肯定了韌性中的善良,否定了由欲望驅使心靈充滿的攻擊狀態。[4]與此同時,電影也肯定了女性尋找自我價值,闡述了女性除了愛情、親情,還當擁有對自我及對世界的體驗等生命意義,這樣獨特的敘事策略獲得了觀眾的認可。
四、 旁白調控優化敘事節奏
影片開篇就為觀眾埋下許多懸念,如安生為何不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七月與安生之間的關系徹底崩盤了嗎?三個主角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隨著電影的放映,懸念隨著旁白也給出了答案,并且每次旁白的出現都配合著鏡頭以及內外層敘事的轉換。
旁白的設置一方面可以調控影片的敘事節奏,另一方面可以調動觀眾的興趣,優化觀影體驗。首先,無論是在影片的敘事內還是敘事外,旁白都有規律或無規律的在影片中充當著節拍器的作用,準確地把握著故事情節推動的節奏,由于時間跨度過長(影片中主人公的故事從13歲到33歲,跨越20年的時間),為了避免觀眾感覺突兀,旁白的加入不僅使得人物所在的時間點進一步明確,減少觀眾的困惑,同時還加快了影片的敘事速度,準確把握影片節奏。例如在第二次旁白之中直接描述了兩個主角從13歲到15歲,從少年過度到了成年。[5]在第四次的旁白出現之后,影片的敘事速度也進一步加快,通過明信片的方式展現出四年來二人的生活和心態變化。
影片利用旁白講述出《七月與安生》這部小說的作者是七月,但是在影片的外層敘事活動之中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七月這個角色,在此處添加旁白可以將一種不可靠的聲音設置為可靠的聲音:第一,不確定的敘述在影片開篇就帶給觀眾許多疑問,不僅留下諸多懸念,又悄無聲息地將這種假可靠敘述引導為一種可靠的聲音,充分調動觀眾的觀影興趣。第二,結局的反轉以及第二種結局由于有了假可靠敘述的鋪墊給予觀眾暗示,使觀眾猛然醒悟,小說作者原來不是七月,竟然是安生。最后,在影片結束時,舒緩的音樂,美麗的七月自由自在地生活著,這個結局又填補了觀眾由于真相中七月死亡而造成的心理落差,進一步優化了觀影體驗。
結語
《七月與安生》以兩閨蜜間的關系作為電影的出發點,進而探討人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而拓寬了電影的廣度。影片運用多條時間線的敘事手法增加了劇情的可看性,作為一個描述年輕人生活的類型片,從電影的深度來說,它確實是一個不一樣的青春類電影。
參考文獻:
[1]賈嘉.女性故事是如何被講述的——《七月與安生》:從小說到電影[J].藝術評論,2016(11):73-77.
[2]蔡郁婉.性別視角下的電影《七月與安生》[J].藝術評論,2016(11):66.
[3]龔自強.姐妹情誼與男權世界的辯證——簡論電影《七月與安生》[J].藝術評論,2016(11):67-72.
[4]陳文遠.《七月與安生》:女性成長的新境界[J].當代電影,2016(11):35-37.
[5]安妮寶貝,林詠琛,李媛,許伊萌,吳楠,包軒鳴,余靜萍.七月與安生[J].當代電影,2016(1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