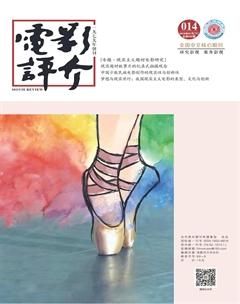光影、人物、情節
馬亞敏
盡管國內觀眾對導演阿基·考里斯馬基比較陌生,但是這位芬蘭國寶級大導演已經在國際上獲獎無數。考里斯馬基的電影風格比較個性化,對人文主義題材的電影十分偏愛。這次他的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一舉奪得第6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最佳導演獎,在他的獲獎名單上又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希望的另一面》延續了考里斯馬基的復古風格和人文主義題材,這位有著清醒的平民立場的導演這次將目光聚焦在難民問題上。通過畫面、人物和內容的對照設置,即雙重性設置,將考里斯馬基冷峻、疏離的情感風格展露無疑,同時帶來對底層人物難民問題的思考。考里斯馬基將雙重性這一審美原則應用到實踐中,便有了《希望的另一面》這一影片。本文將分析在《希望的另一面》中考里斯馬基雙重性的審美原則。
一、 光影的雙重性
電影的開始,在各種現代化工業設備的光影變化中,導演便傳遞給我們一種“雙重性”觀念。明與暗,光與影,每一幀仿佛都在強調“希望的另一面”,而明暗與光影是古希臘哲學對形體強調所產生的的結果。考里斯馬基對電影畫面光影的強調也加深了人們對事物“雙重性”的觀念,“希望”是明,是光,那“希望的另一面呢”?影片的開始導演似乎就在暗示幻影與晦暗的結尾。
由于古希臘哲學對形體強調所帶來的光影變化,在人類視覺里便產生了黑白兩種顏色。同時,古希臘色彩理論幾乎都認為黑白兩種顏色是萬物色彩的本源[1],雖然我們經歷了各種文藝思潮后對色彩有了各種各樣明晰的分類和標準,但是在古希臘時期,色彩卻僅作為充分了解世界本原的一個方面來進行研究,并且是在幾何學形體和數的比例尺度中來進行分析。[2]亞里士多德繼承了先前學者對色彩闡發的理論后,在他的《論感官和可感事物》中宣稱:“中性色(原色)來自于光與暗的混合。”并列舉了五種中性色:猩紅、紫、韭蔥-綠、深藍和灰(黃)。[3]因此,古希臘時期的哲學家認為,光與暗是色彩的本原,顏色是光與暗在客觀世界的體現。
考里斯馬基繼承了這種古希臘傳統,影片中光影的變化無處不在,時刻提醒著我們光影的雙重性。哈立德在移民中心向審查官解釋他為了尋找妹妹米麗亞姆,因此一直偷渡沒有申請政治庇護。審查官留下了哈立德妹妹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提出發布搜查請求幫助尋找米麗亞姆時,哈立德望向光亮的窗外發呆了幾秒,身子一半處在光影下,一半留在黑暗中。光影的停留表現出哈立德對尋找妹妹的渴望,和他即將面對的難民毫無話語權的黑暗生活處境。
除了對光影的強調外,考里斯馬基還在電影中大量使用了亞里士多德認為的由光和暗混合成的中性色。[4]電影里,港口在深藍色的天空背景下忙完了一天的吞吐業務,男主角哈立德·阿里紫色襯衫與綠夾克的配色、維克斯特倫收購的飯店的藍色墻壁與紅色地毯、維克斯特倫家中的黃色餐桌布等等,都體現出了導演對古希臘色彩原則的追尋。古希臘人認為這種中性色體現出厚重、樸實的色彩感[5],考里斯馬基將中性色運用在電影畫面中也體現了他對古希臘光影二重性理念的向往與他的雙重性審美原則在電影中的實際運用。
二、 人物的二重性
在考里斯馬基的一系列電影中,主要人物幾乎都生活在社會底層,大部分是工人和社會流浪者,為了使這些底層人物更具有標簽性,考里斯馬基會相對應地設置一些“上層人物”將他們進行有意識地“區隔”。《希望的另一面》中的底層人物是一位敘利亞難民哈立德,而與之相對應的一位“上層人物”是襯衫推銷商維克斯特倫。
在巴赫金的狂歡詩學理念下,雙重性既是對同一事物相反兩極屬性的對照共生,又是具有不同屬性的事物之間的正反對照共存,它與德國古典哲學中對立統一思想的區別在于:對立統一觀是一種預設的抽象理念形態,雙重性思想則是對西方實存的鮮活文化形態的具體體驗和把握。[6]考里斯馬基借鑒了這種雙重性原則并運用在人物角色的設置上,如果不是敘利亞國內戰亂,國內人民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懼下,擁有著一位未婚妻和眾多兄妹的大家庭以及可以預見的幸福生活的工程師哈立德,也不會流落到芬蘭尋求政治庇護。芬蘭的政府一方面說著歡迎難民,一方面又以各種理由拒絕難民在本國尋求政治庇護和個人的生存發展,哈立德像過街老鼠一樣不受歡迎,人人喊打。哈立德作為一個“雙重邊緣人物”,在本國戰亂的環境中已經沒有棲身之地,作為一個偷渡到芬蘭的難民,不能申請到政治庇護就只能躲避警察偽造身份當一個“黑戶”。難民的失語反證了自身的缺席和處于世界與意識的“邊緣”[7],而哈立德在本國與他國都沒有話語權,都處在失聲的地位,反映其“雙重邊緣”的人物特性,這是考里斯馬基將巴赫金對同一事物相反兩極屬性的對照共生理念運用到具體人物設置中的具體實踐。
巴赫金狂歡詩學中的雙重性理念的另一層含義,是具有不同屬性事物之間的正反對照共存[8],考里斯馬基將其也運用到對人物角色的設置上。除了對單個人物的雙重性設置,考里斯馬基往往將某個“上層人物”作為對另一個“底層人物”的對照,形成兩個人物的故事線同時發展的雙重性局面。電影采用了現實主義的手法來表現底層難民哈立德和相對上層的人物襯衫推銷商維克斯特倫的生活,二人的生活在電影的開始并沒有什么交集,彼此平行發展,作為對彼此生活的對照存在。哈立德在芬蘭國內生活的無助、困苦和渺無希望與維克斯特倫與妻子的中年危機、生意暗淡和轉行投資飯店相對照。個體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在無休止的戰爭和經濟蕭條的社會大環境面前,是軟弱無力、無法改變社會局面的。考里斯馬基的上層與底層人物的雙重性設置,是為了諷刺資本主義國家的人道主義精神,作為上帝耶和華的選民明明應該眾生平等,具有博愛、互相幫助的高尚品格,但卻被眼前的現實利益所擊敗。敘利亞內戰不斷,偽善的芬蘭國家拒絕接受難民。“底層人物”與“上層人物”的雙重設置,一方面在對照中突出了雙方的特色,另一方面彰顯了自身存在的意義,而且這種雙重性思想的兩極沒有主要和次要之分[9],“底層人物”哈立德與“上層人物”維克斯特倫是作為平行人物相對照而發展的,對故事情節的推動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
雙重性也指不同事物的相反意義和不同屬性事物之間的正反對照。[10]盡管是作為“底層人物”哈立德的對照,上層人物維克斯特倫卻秉承著正義與愛的善良本性。面對流浪的哈立德,維克斯特倫先是在自己的飯店招待他吃飯,接著問他需不需要一份工作并為他提供住處,甚至哈立德與妹妹米麗亞姆的重逢,也是維克斯特倫利用自己的人脈將米麗亞姆安全地偷渡到芬蘭。在蕭條的社會環境下,維克斯特倫也保持著自己正義與善良的品質,盡管國家無情,但是個體卻是黑暗社會中的閃光點,給人以希望和溫暖。當然,作為存在于世界中的雙重品質的善與惡,有善良溫暖的維克斯特倫也理所當然地有陰險惡毒流氓混混。哈立德完成移民審查官的審查后,獨自一人等公交車時遭到了三個芬蘭人的挑釁,三人對哈立德充滿惡意,對他進行嘲諷甚至推搡準備毆打他。在經濟蕭條、失業人數眾多的社會環境下,接收難民意味著國內更少的工作機會與報酬,意味著本國公民就業權利受到損害。部分芬蘭人對難民的惡意與維克斯特倫的善良形成對照,考里斯馬基電影中的善與惡的雙重性由此表現出來。
三、 情節的雙重性
面對《希望的另一面》的喜劇標簽與發人深思的電影主題,真的很難斷定考里斯馬基究竟拍的是喜劇還是悲劇。作為電影的敘事者,考里斯馬基經常隱匿在鏡頭背后做一個不在場的敘述者,將帶有幽默色彩的故事情節增添到嚴肅的電影敘事中。正如他自己所言:“電影的主要目的在于讓觀眾笑或者哭。”[11]考里斯馬基這種審美的雙重性,體現在故事情節里就是幽默的情節與嚴肅的故事整體的穿插。哈立德與維克斯特倫的第二次相遇可以用“不打不相識”來形容,飯店老板維克斯特倫想要擺放垃圾,哈立德想要睡覺,因此為爭奪一塊地方展開打斗,但當切到一下個鏡頭時,卻是鼻子里塞了紙團的維克斯特倫與另外三個服務員皺著眉頭看著哈立德狼吞虎咽地吃東西。畫面的銜接給觀眾帶來直觀的幽默感,在嚴肅的敘事中穿插了一絲幽默。
考里斯馬基的幽默是不刻意的、未經雕琢的,是一種自然產生的幽默。在得到觀眾會心一笑的同時又對他所表達的主題進行著反諷,造成哈立德的困頓處境的根源是芬蘭假意歡迎難民卻不能給予難民保障的虛偽與敘利亞國內戰亂不能提供給人民安全舒適的發展環境。在看似幽默的內容背后往往潛藏著更深刻的社會問題。反諷同時也加深了喜劇效果,讓故事情節更流暢地展開。
在幽默的背后,是考里斯馬基對荒誕感的追求。[12]人生有時候確實像“等待戈多”一樣迷茫、荒誕,哈立德的偷渡經歷、維克斯特倫的賭場贏錢以及二人“不打不相識”的相遇,都使得人生充滿了荒誕感。愛斯特拉岡與弗拉基米爾的人生是一場無盡無望的對戈多的等待,哈立德與維克斯特倫的人生是解決由外在的社會環境引起的個體人生危機,究其根源都是由于戰爭泯滅了宗教信仰和人性的正義,哈立德為妹妹而活,維克斯特倫也受到感觸,意識到在荒誕的人生面前還能珍惜身邊的親人是件幸事。比起哈立德的無家可歸與親人失散,維克斯特倫的芬蘭國籍可以為他提供一個暫時安全的環境,雖然國家處于經濟蕭條的狀態,但仍是和平穩定的狀態。
幽默的情節與嚴肅的敘事主題體現了電影內容的雙重性,喜劇情節的穿插也使嚴肅的敘事主題不會顯得枯燥、沉悶,相反,這種輕松的節奏卻更能體現出主題的嚴肅性。正如巴赫金的人類學世界觀,關聯于以理解世界的、自然的、科學的方法為范例的合理古典形式,建立在以20世紀人文意識研究的基礎之上,他關注的點是人類生活的事件及人的生存狀況。[13]考里斯馬基在他的電影世界中也將人的問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有的情節、人物的雙重性設置都是為了突顯“人的問題”這一主題。西方現代哲學家尼采已經喊出“上帝死了”的口號,沒有了傳統宗教的信仰支撐,沒有對西方傳統善良與正義的苦苦追求,人類將往何處去便成為整個西方世界所思考的問題。考里斯馬基在電影中不斷探尋著人的主題,寄希望于古希臘傳統精神正義與善的回歸。當信仰不能支撐起人生前進的方向,不如重新回歸到西方傳統理性,用宇宙最高的善來指導人生。
盡管國內觀眾對導演阿基·考里斯馬基比較陌生,但是這位芬蘭國寶級大導演已經在國際上獲獎無數。考里斯馬基的電影風格比較個性化,對人文主義題材的電影十分偏愛。這次他的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一舉奪得第6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最佳導演獎,在他的獲獎名單上又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希望的另一面》延續了考里斯馬基的復古風格和人文主義題材,這位有著清醒的平民立場的導演這次將目光聚焦在難民問題上。通過畫面、人物和內容的對照設置,即雙重性設置,將考里斯馬基冷峻、疏離的情感風格展露無疑,同時帶來對底層人物難民問題的思考。考里斯馬基將雙重性這一審美原則應用到實踐中,便有了《希望的另一面》這一影片。本文將分析在《希望的另一面》中考里斯馬基雙重性的審美原則。
一、 光影的雙重性
電影的開始,在各種現代化工業設備的光影變化中,導演便傳遞給我們一種“雙重性”觀念。明與暗,光與影,每一幀仿佛都在強調“希望的另一面”,而明暗與光影是古希臘哲學對形體強調所產生的的結果。考里斯馬基對電影畫面光影的強調也加深了人們對事物“雙重性”的觀念,“希望”是明,是光,那“希望的另一面呢”?影片的開始導演似乎就在暗示幻影與晦暗的結尾。
由于古希臘哲學對形體強調所帶來的光影變化,在人類視覺里便產生了黑白兩種顏色。同時,古希臘色彩理論幾乎都認為黑白兩種顏色是萬物色彩的本源[1],雖然我們經歷了各種文藝思潮后對色彩有了各種各樣明晰的分類和標準,但是在古希臘時期,色彩卻僅作為充分了解世界本原的一個方面來進行研究,并且是在幾何學形體和數的比例尺度中來進行分析。[2]亞里士多德繼承了先前學者對色彩闡發的理論后,在他的《論感官和可感事物》中宣稱:“中性色(原色)來自于光與暗的混合。”并列舉了五種中性色:猩紅、紫、韭蔥-綠、深藍和灰(黃)。[3]因此,古希臘時期的哲學家認為,光與暗是色彩的本原,顏色是光與暗在客觀世界的體現。
考里斯馬基繼承了這種古希臘傳統,影片中光影的變化無處不在,時刻提醒著我們光影的雙重性。哈立德在移民中心向審查官解釋他為了尋找妹妹米麗亞姆,因此一直偷渡沒有申請政治庇護。審查官留下了哈立德妹妹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提出發布搜查請求幫助尋找米麗亞姆時,哈立德望向光亮的窗外發呆了幾秒,身子一半處在光影下,一半留在黑暗中。光影的停留表現出哈立德對尋找妹妹的渴望,和他即將面對的難民毫無話語權的黑暗生活處境。
除了對光影的強調外,考里斯馬基還在電影中大量使用了亞里士多德認為的由光和暗混合成的中性色。[4]電影里,港口在深藍色的天空背景下忙完了一天的吞吐業務,男主角哈立德·阿里紫色襯衫與綠夾克的配色、維克斯特倫收購的飯店的藍色墻壁與紅色地毯、維克斯特倫家中的黃色餐桌布等等,都體現出了導演對古希臘色彩原則的追尋。古希臘人認為這種中性色體現出厚重、樸實的色彩感[5],考里斯馬基將中性色運用在電影畫面中也體現了他對古希臘光影二重性理念的向往與他的雙重性審美原則在電影中的實際運用。
二、 人物的二重性
在考里斯馬基的一系列電影中,主要人物幾乎都生活在社會底層,大部分是工人和社會流浪者,為了使這些底層人物更具有標簽性,考里斯馬基會相對應地設置一些“上層人物”將他們進行有意識地“區隔”。《希望的另一面》中的底層人物是一位敘利亞難民哈立德,而與之相對應的一位“上層人物”是襯衫推銷商維克斯特倫。
在巴赫金的狂歡詩學理念下,雙重性既是對同一事物相反兩極屬性的對照共生,又是具有不同屬性的事物之間的正反對照共存,它與德國古典哲學中對立統一思想的區別在于:對立統一觀是一種預設的抽象理念形態,雙重性思想則是對西方實存的鮮活文化形態的具體體驗和把握。[6]考里斯馬基借鑒了這種雙重性原則并運用在人物角色的設置上,如果不是敘利亞國內戰亂,國內人民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懼下,擁有著一位未婚妻和眾多兄妹的大家庭以及可以預見的幸福生活的工程師哈立德,也不會流落到芬蘭尋求政治庇護。芬蘭的政府一方面說著歡迎難民,一方面又以各種理由拒絕難民在本國尋求政治庇護和個人的生存發展,哈立德像過街老鼠一樣不受歡迎,人人喊打。哈立德作為一個“雙重邊緣人物”,在本國戰亂的環境中已經沒有棲身之地,作為一個偷渡到芬蘭的難民,不能申請到政治庇護就只能躲避警察偽造身份當一個“黑戶”。難民的失語反證了自身的缺席和處于世界與意識的“邊緣”[7],而哈立德在本國與他國都沒有話語權,都處在失聲的地位,反映其“雙重邊緣”的人物特性,這是考里斯馬基將巴赫金對同一事物相反兩極屬性的對照共生理念運用到具體人物設置中的具體實踐。
巴赫金狂歡詩學中的雙重性理念的另一層含義,是具有不同屬性事物之間的正反對照共存[8],考里斯馬基將其也運用到對人物角色的設置上。除了對單個人物的雙重性設置,考里斯馬基往往將某個“上層人物”作為對另一個“底層人物”的對照,形成兩個人物的故事線同時發展的雙重性局面。電影采用了現實主義的手法來表現底層難民哈立德和相對上層的人物襯衫推銷商維克斯特倫的生活,二人的生活在電影的開始并沒有什么交集,彼此平行發展,作為對彼此生活的對照存在。哈立德在芬蘭國內生活的無助、困苦和渺無希望與維克斯特倫與妻子的中年危機、生意暗淡和轉行投資飯店相對照。個體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在無休止的戰爭和經濟蕭條的社會大環境面前,是軟弱無力、無法改變社會局面的。考里斯馬基的上層與底層人物的雙重性設置,是為了諷刺資本主義國家的人道主義精神,作為上帝耶和華的選民明明應該眾生平等,具有博愛、互相幫助的高尚品格,但卻被眼前的現實利益所擊敗。敘利亞內戰不斷,偽善的芬蘭國家拒絕接受難民。“底層人物”與“上層人物”的雙重設置,一方面在對照中突出了雙方的特色,另一方面彰顯了自身存在的意義,而且這種雙重性思想的兩極沒有主要和次要之分[9],“底層人物”哈立德與“上層人物”維克斯特倫是作為平行人物相對照而發展的,對故事情節的推動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
雙重性也指不同事物的相反意義和不同屬性事物之間的正反對照。[10]盡管是作為“底層人物”哈立德的對照,上層人物維克斯特倫卻秉承著正義與愛的善良本性。面對流浪的哈立德,維克斯特倫先是在自己的飯店招待他吃飯,接著問他需不需要一份工作并為他提供住處,甚至哈立德與妹妹米麗亞姆的重逢,也是維克斯特倫利用自己的人脈將米麗亞姆安全地偷渡到芬蘭。在蕭條的社會環境下,維克斯特倫也保持著自己正義與善良的品質,盡管國家無情,但是個體卻是黑暗社會中的閃光點,給人以希望和溫暖。當然,作為存在于世界中的雙重品質的善與惡,有善良溫暖的維克斯特倫也理所當然地有陰險惡毒流氓混混。哈立德完成移民審查官的審查后,獨自一人等公交車時遭到了三個芬蘭人的挑釁,三人對哈立德充滿惡意,對他進行嘲諷甚至推搡準備毆打他。在經濟蕭條、失業人數眾多的社會環境下,接收難民意味著國內更少的工作機會與報酬,意味著本國公民就業權利受到損害。部分芬蘭人對難民的惡意與維克斯特倫的善良形成對照,考里斯馬基電影中的善與惡的雙重性由此表現出來。
三、 情節的雙重性
面對《希望的另一面》的喜劇標簽與發人深思的電影主題,真的很難斷定考里斯馬基究竟拍的是喜劇還是悲劇。作為電影的敘事者,考里斯馬基經常隱匿在鏡頭背后做一個不在場的敘述者,將帶有幽默色彩的故事情節增添到嚴肅的電影敘事中。正如他自己所言:“電影的主要目的在于讓觀眾笑或者哭。”[11]考里斯馬基這種審美的雙重性,體現在故事情節里就是幽默的情節與嚴肅的故事整體的穿插。哈立德與維克斯特倫的第二次相遇可以用“不打不相識”來形容,飯店老板維克斯特倫想要擺放垃圾,哈立德想要睡覺,因此為爭奪一塊地方展開打斗,但當切到一下個鏡頭時,卻是鼻子里塞了紙團的維克斯特倫與另外三個服務員皺著眉頭看著哈立德狼吞虎咽地吃東西。畫面的銜接給觀眾帶來直觀的幽默感,在嚴肅的敘事中穿插了一絲幽默。
考里斯馬基的幽默是不刻意的、未經雕琢的,是一種自然產生的幽默。在得到觀眾會心一笑的同時又對他所表達的主題進行著反諷,造成哈立德的困頓處境的根源是芬蘭假意歡迎難民卻不能給予難民保障的虛偽與敘利亞國內戰亂不能提供給人民安全舒適的發展環境。在看似幽默的內容背后往往潛藏著更深刻的社會問題。反諷同時也加深了喜劇效果,讓故事情節更流暢地展開。
在幽默的背后,是考里斯馬基對荒誕感的追求。[12]人生有時候確實像“等待戈多”一樣迷茫、荒誕,哈立德的偷渡經歷、維克斯特倫的賭場贏錢以及二人“不打不相識”的相遇,都使得人生充滿了荒誕感。愛斯特拉岡與弗拉基米爾的人生是一場無盡無望的對戈多的等待,哈立德與維克斯特倫的人生是解決由外在的社會環境引起的個體人生危機,究其根源都是由于戰爭泯滅了宗教信仰和人性的正義,哈立德為妹妹而活,維克斯特倫也受到感觸,意識到在荒誕的人生面前還能珍惜身邊的親人是件幸事。比起哈立德的無家可歸與親人失散,維克斯特倫的芬蘭國籍可以為他提供一個暫時安全的環境,雖然國家處于經濟蕭條的狀態,但仍是和平穩定的狀態。
幽默的情節與嚴肅的敘事主題體現了電影內容的雙重性,喜劇情節的穿插也使嚴肅的敘事主題不會顯得枯燥、沉悶,相反,這種輕松的節奏卻更能體現出主題的嚴肅性。正如巴赫金的人類學世界觀,關聯于以理解世界的、自然的、科學的方法為范例的合理古典形式,建立在以20世紀人文意識研究的基礎之上,他關注的點是人類生活的事件及人的生存狀況。[13]考里斯馬基在他的電影世界中也將人的問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有的情節、人物的雙重性設置都是為了突顯“人的問題”這一主題。西方現代哲學家尼采已經喊出“上帝死了”的口號,沒有了傳統宗教的信仰支撐,沒有對西方傳統善良與正義的苦苦追求,人類將往何處去便成為整個西方世界所思考的問題。考里斯馬基在電影中不斷探尋著人的主題,寄希望于古希臘傳統精神正義與善的回歸。當信仰不能支撐起人生前進的方向,不如重新回歸到西方傳統理性,用宇宙最高的善來指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