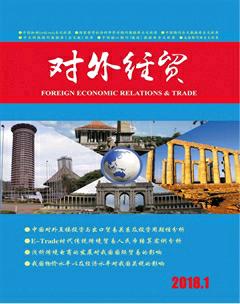西部地區城鎮化與信息化協調關系研究
黃文炎+唐順標
[摘要]通過構建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線性加權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實證分析了2012—2016年西部地區12個省(市、區)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協調度。研究結果表明,西部地區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發展水平整體偏低,且城鎮化水平明顯滯后于信息化水平。西部地區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協調度總體不高,整體呈現穩態發展的時序變化趨勢,并表現出明顯的“西北地區高,西南地區低”的空間分布特征,形成了重度失調類、中度失調類和瀕臨失調類和輕度失調類4種耦合協調類型。
[關鍵詞]城鎮化;信息化;協調關系;西部地區
[中圖分類號]F06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8)01-0080-04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the linear weighted method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were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in 12 provinces (cities and distric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from 2012 to 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generally low, a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lags behind that of informatization.
Keywords: Urbanization;Informatization;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Western Area
[作者簡介]黃文炎(1965-),男,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
[通訊作者]唐順標(1976-),男,本科,館員,研究方向:信息資源建設與服務。
[基金項目]廣西中青年教師基礎能力提升項目(項目編號:KY2016YB443)。
一、引言
我國現已將“四化”發展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城鎮化和信息化均是該戰略的組成部分,二者的協調發展將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學界對于城鎮化與信息化關系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者的發展與演變過程、兩者間內在關系、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實現路徑、以及二者綜合發展水平的評價與分析等方面。姜愛林[1-2]認為信息化是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城鎮化則是信息化的空間形式,并構建了城鎮化與信息化互動關系的理論模型。馮獻等[3]基于“四化”同步的時代背景,分析了城鎮化與信息化的歷史關聯及作用機理。徐君[4]通過建立“四化”耦合關系模型,探討了“四化”各子系統之間的耦合互動機制。鄭子龍[5]運用面板門限回歸模型,實證研究了我國31個省區信息化發展對城鎮化進程的影響。其研究結果表明,信息化能夠對城鎮化進程起到促進作用,但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趙施迪等[6]通過構建新型城鎮化與農村信息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復合模糊物元法分析了我國31個省區新型城鎮化與農村信息化的關系。劉躍等[7]運用靜態面板數據門限回歸模型,并結合2007—2013年我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信息化與新型城鎮之間的互動關系。其結果顯示,信息化與新型城鎮化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且二者之間的關系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馬德君等[8]綜合運用熵值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對2003—2013年西北民族地區18個城市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協調度進行了評價分析。該研究發現,西北民族地區城鎮化與信息化發展均表現為緩慢上升趨勢,但城鎮化發展水平更高。但從整體來看,城鎮化與信息化的協調程度屬于失調狀態。嚴昕等[9]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實證分析了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新型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協調狀況,并得出江蘇省新型城鎮化與信息化融合發展,各個要素之間均存在密切的關系。但是,現有文獻中有關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與信息化關系問題的研究成果仍較為匱乏,特別是缺少針對西部地區各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協調關系方面的實證研究。因此,本文以我國西部地區的12個省(市、區)為研究樣本,構建了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線性加權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對2012—2016年西部地區各省份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協調度進行實證分析,以此得出研究結論。研究成果可為西部地區各級政府制定城鎮化與信息化協調發展政策,進而推動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依據。
二、研究設計
(一)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的研究范圍界定為西部地區的12個省(市、區),具體包括:西藏、新疆、青海、甘肅、陜西、寧夏、內蒙古、四川、重慶、云南、貴州和廣西。借鑒向麗等[10]的研究成果,并充分考慮西部地區城鎮化和信息化的實際情況,本文構建了西部地區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表1)。其中,城鎮化評價指標包括人口城鎮化率、土地城鎮化率以及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信息化評價指標包括郵電業務指數、互聯網普及率、電話普及率以及信息就業率。并且,所有指標均為正向指標。
(二)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的指標數據由2013—2017年的《中國統計年鑒》直接得出或通過計算求得。在數據標準化處理上,采用面板標準化方法,具體計算公式如式(1)所示。對于無量綱化的零值,借鑒周先波等[11]的做法,使用單項指標第二小的數值的十分之一進行處理。
X′ij=(Xij-minXij)/(maxXij-minXij)(1)
式(1)中,X′i表示經過處理后的標準化數據變量;Xi表示原始數據;maxXi、minXi分別代表同一年份內所有省份相關原始數據的最大值、最小值。
(三)研究方法
第一,采用線性加權法計算得到考察期內西部地區各省份的城鎮化評價值和信息化評價值,具體計算公式為:
UR=∑mj=1wijx′ij,IF=∑nj=1wijy′ij
wij=Vij/∑nj=1Vij,Vij=σijxij(j=1,2,…,n)(2)
式(2)中,UR代表城鎮化評價值;IF代表信息化評價值;x′ij、y′ij均表示標準化值;wij表示由變異系數法確定的各指標權重。σij、xij、Vij分別表示各指標的標準差、平均值和變異系數。
第二,構建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計算方法如式(3)所示,以此對西部地區城鎮化與信息化的協調發展水平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并運用均勻分布函數法來確定西部地區各省份歷年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協調類型(見表2)。
D=C×T,C=UR×IF/(UR+IF)21/2,T=aUR+bIF(3)
式(3)中,D代表耦合協調系數;C代表耦合系數;T表示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評價值;UR和IF的含義同式(2);a、b表示待定系數。本文只研究城鎮化與信息化兩個方面,且認為二者的重要性相同,故設定a=b=05。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首先,運用變異系數法計算得到西部地區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中各項指標的權重(見表1)。然后,采用線性加權法分別計算出2012—2016年西部地區12個省(市、區)的城鎮化評價值(UR)與信息化評價值(IF),并根據耦合協調度模型得到考察期內各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評價值(T),如圖1所示。再根據公式(3)計算得到西部地區各省份在2012—2016年間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系數(C)以及耦合協調系數(D)(見表3),進一步得到各省份在考察期內的城鎮化與信息化各評價值的均值,并根據表2判別出各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協調類型(見表4)。下面分別對西部地區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發展水平、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協調度進行實證分析。
(一)西部地區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發展水平分析
由各省份的城鎮化評價值的均值排名情況(表4)可知,排名前3位的省份依次是陜西、內蒙古和新疆,重慶位列第4位。排名后3位的省份分別是青海、貴州和西藏,說明這3個省份的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從各省份的信息化評價值的均值排名情況來看,陜西排名第一位,其次是重慶,內蒙古排名第三,表明這3個省(市)的信息化程度相對較高。而貴州、云南和廣西均在后3位之列,且廣西排名末尾,說明這3個省份的信息化發展狀況均不容樂觀。另外,從各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評價值均值的對比情況來看,廣西、云南和甘肅3個省份均屬于信息化滯后型,其余9個省份均為城鎮化滯后型。根據各省份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評價值可以得出,西部地區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發展水平整體偏低,絕大部分省份在考察期內的變化趨勢較為平穩。陜西和內蒙古始終位居前兩位,新疆在2012—2014年間均排名第3位,但重慶在2015年超越了新疆,由第4位上升為第3位。云南、貴州和廣西的則一直排名后3位,且云南保持在倒數第三位。廣西在2012—2015年間均排名最后,但在2016年超過了貴州,說明該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發展水平提升較快。
(二)西部地區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協調度分析
由表4西部地區各省份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協調度的均值可得,2012—2016年西部地區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協調度總體偏低,其耦合協調系數的均值介于01907~04351之間。而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系數的均值介于03511~04970之間,明顯高于二者的耦合協調系數的均值水平,這是因為西部地區各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評價值偏低,由此導致這些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協調系數也不高。從時序變化特征上看,西部地區各省份在考察期內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表現為穩態發展特征。由表3可知,2012—2014年,廣西、西藏和青海3個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系數均排名在后3位。其中,廣西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度最低,但該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度一直呈現快速上升趨勢,并在2016年超過了重慶、云南、甘肅和寧夏。云南在2012—2015年間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度始終保持平穩發展態勢,但該省份在2016年的耦合度出現大幅度下降。2016年,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協調度位列前3位的省份包括:陜西、內蒙古和重慶;排名在后3位的省份分別為貴州、云南和廣西,且這3個省份均位于西南民族地區。從西部地區各省份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協調類型來看,廣西為重度失調類,貴州為中度失調類,陜西和內蒙古為瀕臨失調類,其余8個省份均屬于輕度失調類。可見,位于西南民族地區的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協調度明顯低于位于西北民族地區的省份,而位于西部地區內非民族地區的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協調狀況整體較好。
四、結論
第一,西部地區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發展水平整體偏低,且城鎮化水平明顯滯后于信息化水平。2012—2016年,陜西的城鎮化水平相對較高,其次是內蒙古,新疆排名第3位;信息化水平位列前3位的分別是陜西、重慶和內蒙古。廣西、云南和甘肅均屬于信息化滯后型,其余9個省份均為城鎮化滯后型。在考察期內,絕大部分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發展水平變化趨勢較為平穩,廣西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綜合發展水平提升較快。
第二,西部地區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協調度總體不高,考察期內各省份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協調系數的均值介于01907~04351之間,明顯低于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系數的均值水平。西部地區在2012—2016年間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整體表現為穩態發展的時序變化特征,但廣西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度呈現快速上升趨勢,云南的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度則出現大幅下降。各省份在考察期內的城鎮化與信息化的耦合協調度表現出明顯的“西北地區高,西南地區低”的空間分布特征,并形成了重度失調類、中度失調類和瀕臨失調類和輕度失調類4種耦合協調類型。其中,廣西屬于重度失調類,貴州屬于中度失調類,陜西和內蒙古屬于瀕臨失調類,其余8個省份均為輕度失調類。
[參考文獻]
[1]姜愛林21世紀初用信息化推動城鎮化的戰略選擇[J]經濟學動態,2001(9):46-48
[2]姜愛林城鎮化與信息化互動關系研究[J]經濟學動態,2004(8):67-69
[3]馮獻,崔凱中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內涵與同步發展的現實選擇和作用機理[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3(3):269-273
[4]徐君,高厚賓,王育紅新型工業化、信息化、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互動耦合機理研究[J]現代管理科學,2013(9):85-88
[5]鄭子龍我國信息化對城鎮化的非線性動態影響機制研究——基于面板數據門限回歸模型的經驗分析[J]財政研究,2013(8):48-51
[6]趙施迪,楊德才,施漢忠新型城鎮化和農村信息化發展相互影響機理研究——基于復合模糊物元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62-70,190
[7]劉躍,袁雪嬌,葉宇梅信息化與新型城鎮化的互動效應與路徑[J]城市問題,2016(6):24-32
[8]馬德君,宗雯,楊青,等西北民族地區城鎮化與信息化[J]財經科學,2016(7):99-110
[9]嚴昕,鄭建明新型城鎮化與信息化耦合度分析[J]圖書館論壇,2017(5):10-17
[10]向麗,藍文婷長江經濟帶“四化”協調發展的綜合評價[J]江蘇農業科學,2017(10):278-283
[11]周先波,盛華梅信息化產出彈性的非參數估計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10):130-141
(責任編輯:顧曉濱馬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