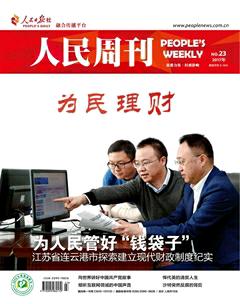監察法征求意見 五大話題引熱議
王燦
編者按:11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以下簡稱《監察法草案》)在中國人大網首次公布,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草案作為監察體制改革成果的法律固化,明確了國家監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甫一面世就受到了社會的高度矚目,被輿論普遍認為“是我國反腐敗理念和思路的全面提升,代表著我國在反腐檢查與決定權力的全面制度化”。不過,作為一項重大政治體制改革的法律載體,《監察法(草案)》中的部分條款和規定也引發輿論熱議。
輿論普遍認為,《監察法》作為國家權力架構頂層設計的法治成果,將為我國形成“一府一委兩院”的新國家機構體系提供法律支撐,有助于進一步實現反腐敗制度化、法治化,有助于推進實現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對此,國內輿論反映較為積極,多數公眾對該法的出臺寄予厚望。
自《監察法(草案)》發布以來,媒體報道、媒體評論和專家解讀是傳播的三方主要力量。主流輿論除了盤點法律條款看點、披露立法經歷,還從政治體制改革重大探索、科學立法的樣板工程、反腐敗的法制保障等不同視角對草案進行解讀,并提供了許多建設性意見。其中,“留置取代‘雙規”“反腐全覆蓋”“監察官制度”等話題受到了輿論較多關注。
不過,《監察法(草案)》作為一部全新的制度設計性法案,也伴隨著部分爭議。下文通過梳理熱度較高的話題,總結出了爭議聲音較為集中的五大話題,根據關注程度由高到低排列,輿論爭議焦點依次為立法依據問題、接受監督問題、律師介入問題、留置條件問題及工作銜接問題。
話題一:立法依據問題
《監察法(草案)》的立法依據最受輿論關注,多數專家學者均提到了立法需要修改憲法的問題。
如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陳光中認為,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監察立法也必須寫明根據憲法制定。因此,必須先修改《憲法》,再根據《憲法》制定《監察法》,如此才能根本解決合憲性問題。北京大學法學教授沈巋也認為,《監察法(草案)》關于監察機關設置的條款,具有重大的憲法意義,應該在現行憲法中加以明確規定。部分輿論聲音甚至直接指責草案合憲性基礎存在問題,如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陳瑞華、云南恩龍律所主任許思龍認為,未修改憲法就改變政體有違憲之嫌。自媒體平臺對此話題關注度極高,如微博大V“@陶公春秋”發文呼吁稱“制定監察法必須嚴格根據憲法”,受到網民點贊和轉評近500次。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教授馬嶺進一步建議,除了在《憲法》“總綱”作出相應修正外,還應增加“監察委員會”的專門章節,對其性質、地位、組成、任期、體制等問題作出規定。在章節排序上,監察委應在法院和檢察院之后,“因為司法權是比監察權更重要的國家權力”。
話題二:接受監督問題
監察委員會設立后如何接受監督,該議題也備受輿論關注。
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韓大元指出,“人大機關”的公職人員也在監察機關的監察范圍之內,使得監察機關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有可能凌駕于人大之上,可能成為不受人大監督的特殊機關。陳瑞華教授也質疑稱,“監察委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產生,接受其監督,卻不向人大報告工作;監察委對人大及其常委會進行監察,違背人民主權原則”。
對此,《中國紀檢監察報》11月13日刊文解釋稱,“制定監察法,就是要通過法律明確監察范圍,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監察的是‘公職人員而非公職人員所在的‘機關”。
此外,不少專家學者也提出建議,如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秦前紅表示,監察委需要對同級人大及常委會負責,并接受監督,到底如何負責,怎樣監督,都需要法律予以界定。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郭華提出,一方面可以在監察委員會內部實行決策、執行、監督分開,通過人大監督來約束;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檢察機關在個案的查辦過程進行監督。
話題三:律師介入問題
《監察法(草案)》中未提及留置期間律師介入問題,因此引發了法學專家、律師等法律專業人士的多方探討。較多觀點認為律師介入有助于實現程序正義,建議增設律師介入制度。
如陳光中教授認為,留置是對于人身自由的嚴格限制,相當于監禁,律師介入可確保程序正義,提高辦案質量和防止冤假錯案。上海律師丁金坤也擔憂稱,留置期間不得會見律師,造成案件程序不透明,嫌疑人的基本權利將難以保障。有的觀點從保障人權的角度表達意見,如陳瑞華教授認為,不允許律師介入剝奪了被調查人的辯護權,違反了憲法和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還有聲音從境外立法經驗出發,建議允許律師介入,如香港律師張洪元以香港廉政公署規定為例,稱“被拘捕人士從被拘捕開始即可要求通知會見律師,并在律師出現前可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不過,也有觀點對此進行反駁。新華社日前發文稱,“監察委是政治機關,不是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監察委行使的不是司法權力,律師沒有權力介入監察委的調查過程”。
話題四:留置條件問題
由于《監察法(草案)》較籠統地規定了留置措施取代“兩規”,后續細化措施也引發較多討論。如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建議,在什么情況下可以采取留置措施、留置的對象是誰、留置的具體方式方法等,在立法中都需明確規定。
微信公號“監察委前沿”刊文中也提出了“留置條件過于籠統、可操作性有待提高”的問題,認為應區分“涉嫌嚴重職務違法”和“僅是違法”所采用留置的條件,對留置場所歸屬、性質等應進一步規定;留置如何執行,尤其是涉及行賄人等非公職人員時的措施等,也需進一步明確。《新京報》評論建議,可以把留痕制度運用于防止留置權任性方面,即把啟動留置權時所掌握的犯罪事實與證據進行固定、留痕,以防止有監察委人員濫用職權。
話題五:工作銜接問題
還有觀點認為,監察權有刑事偵查之實,如何區分和銜接二者工作?
對此部分專家學者提出意見。如陳瑞華教授質疑道,監察委可以采取剝奪人身自由和財產權的強制處分措施,有從事刑事偵查之實,卻不受《刑事訴訟法》的約束。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姜明安認為,監察機關可以行使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行使的某些刑事強制措施權和刑事偵查權,對于國家監察機關與司法機關二者的聯系與區別,國家監察立法必須對之明晰化。此外,秦前紅教授表示,監察體制改革面臨的首要現實問題就是工作銜接,全國檢察院的職務犯罪等職責如何在轉隸過程中保持工作連續,相關職能怎么安排、對接,這些問題在監察體制改革全面鋪開之時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