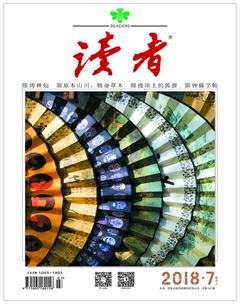鐘繇字帖
王澍
我練字有一個過程。最早練字沒有字帖。小學4年級時,老師讓我們描紅(楷書),我在家里翻出一本關于隸書的書,就照著寫。本以為沒按老師要求寫楷書會挨罵,沒想到老師說寫得好。因為被老師表揚,我就整天狂寫。一本書里的字不夠用,我就自己搜集,比如看到一本書的書名,在街上看到哪兒有隸書,我都記住,拼出一本自己的“隸書字帖”。而且我寫得非常熟練。
到中學,我們班上的黑板報都是我包辦的。那時,我們家對門住著我父親所在劇團的一位話劇導演,他見我一小孩兒整天寫字,問:“你有字帖嗎?”“沒。”“那我送你一本。”那是我得到的第一本真正的字帖,是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非常好的宋拓本。第一次拿到一本字帖,有種肅然起敬的感覺。因為那些字明顯跟我以前練的不一樣。我以前就是野路子。但它呢,有一種氣質,那是一種君子之氣、學堂之氣。因為歐陽詢的字是非常標準的,后世考科舉時學子答卷所用字體基本是從歐體演變出來的。以后我就練歐體。我大概屬于容易癡迷的人,一旦練起來,就廢寢忘食。1976年,唐山大地震對西安也有很大影響,大家不敢回家,都住在大地震棚里。我們在地震棚里住了一年,鬧哄哄的忙亂場景中,總能看到一個小孩兒整天蹲在桌子邊練字……
亂練之后,你會形成一些毛病。重新臨帖,你就像重新跟一個老師,練新字(歐體)的過程就等于在改毛病。我一直寫,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有長進。但是知道自己寫了之后,眼睛開始“好”起來。那時候,我經常跑去西安碑林——如果不寫《九成宮醴泉銘》,我對唐碑不會有興趣。從我們家走到碑林,去3個小時,回來又3個小時——沒有錢坐車,都是步行。我整天在那兒看,沒有帶紙筆,是在用心讀。幾乎每個周末我都去,持續了整個中學階段。由此,我養成了一個習慣,除了看整體的氣象,還會一個字、一個字讀,會在心里頭寫……所以到現在為止,我都說:“字是在心里寫的。”
我練字真正有老師指導,是在上大學以后。當時,我參加了學校的書法社團,書法社請了南京藝術院的研究生黃惇(現在是著名的書法家)當老師。我跟他學篆書、漢隸,還學金文。我練了很長時間《張遷碑》。基本整個大學期間,我都在練上古時期的書法,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我還在寫篆書。體會當然不一樣。唐人很有法度,但有個問題,我們對這個世界最直觀的或者最原初的那種渾然一體的認識,唐人顯然是不具備的。因為到唐代的時候,社會已經開始高度分工,開始專業化;人們在面對一個事物時開始一件一件地拆開理解,拆開之后才有道理,拆開之后才有法度的產生,一切事物都變得有規矩、清楚、明朗。最原初的那種渾然一體的帶有一點點神性的東西,在唐人那兒是沒有的。唐人有廟堂氣,但沒有自然的神性。這就是我通過練習上古書法得到的感受。
大學畢業之后,事情太多,我練字沒有那么連貫頻繁了。重新撿起來是我到同濟大學讀博士的時候。那時候我練的字,主要是散氏盤銘文,比篆書還要早。青銅器上每個只有小拇指蓋那么大的字,我卻都寫得像拳頭那樣大,用大張的紙,寫好掛在墻上,朋友來了可摘兩張走。
而說到鐘繇字帖,我是從2000年回到杭州做象山項目時開始臨習的。自此,我開始對精微的東西感興趣。那幾年,我一直把字寫得像拳頭那樣大,突然靈機一動,又把字寫得像指甲蓋兒那么小。這是一個人心境的變化。我對規矩的有和無之間的事感興趣。鐘繇,我們都說他是楷書之祖。之前,他把隸書寫出來,有點兒像楷書,但是按唐人的標準,這又太像隸書,它就是那么一種字,也有人把他的字叫真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性情。因為這是魏晉時代的字,《世說新語》時代的字,所以他的氣質不一樣。他知道有規矩,同時他也敢放浪形骸。我對那個時代有一種向往。鐘繇是帖學這一路,我以前臨的是碑,碑上的字是在石頭上用刀刻出來的,你再怎么練,都會有一種“碑氣”,或者說是一種“刀刻氣”。寫很大的字,用很大的力氣,力透紙背,恨不得把紙寫爛了,這就是典型的碑學。康有為就特別推崇碑學,貶低帖學。帖學的字從來不大,是要寫在紙上的,人們學的也是寫在紙上的帖,能看到筆鋒落在紙上的那種微妙之處。從這時起,我相當于改宗了,自己給自己換了一個老師,轉到帖學上去。從此,整個人的氣息都變得溫潤、柔軟起來。
中國的藝術特別好玩兒,既要想又不能想。你在寫的時候,不能多想,可是你又必須同時很清醒地意識到你在寫。就像一個人分裂成兩個,你在寫的時候,另外一個你就站在旁邊看著。像傳統戲曲,除了唱之外還要關照動作,所以分神;如果按現實主義完全入戲的話,就不可能做出動作。所以這種藝術是介入主客觀之間的、很特別的一種文化傳統。既不能說純主觀,也不能說它不客觀。我寫,我知道我在寫,我又不能太知道我在寫。我不能停滯。
鐘繇的字我很佩服,你把他的小字放到一拳大,一點兒問題都沒有。這里說的小不是絕對的,包括園林也是一樣。園林的核心就是8個字:小中見大,大中見小。其實這對書法一樣適用。它對我的影響也是很直觀的。比如我練鐘繇之前,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對我的影響其實是很深的,所以之前我的建筑都做得比較高峻,重心也高,看上去俊秀挺拔,好像一個清俊高大的書法字站在那里,很帥。但是鐘繇不一樣,他(的字)樸厚、重心低。到我做象山項目時,建筑就有一種蹲伏的感覺,基本的氣質就改變了,既舒展,又溫潤。要說舒展嘛,魏晉是個比較有舞蹈氣質的時代,寬袍大袖。比如畫一根線,唐朝可能畫這么長,魏晉要畫這——么長!做象山項目,尤其二期做完之后,有一位教藝術史的老太太說:“這個時代還能做出這么長的線,這個線比沈周的線還長!”因為沈周的線比文徵明的長,他是能連接前面時代的特殊的人。
我記得項目里面那幢臨水塘的樓(14號),一條線一開始做48米,做做做,反復地改,我又把它改成了60米,最后出圖紙之前,我又改了一遍,改成72米。這不是簡單的物理長度,它是指你待在一個院子里,你感受到的那個寬面兒、那個空間的長度;就是當我站在院子里往外看的時候,就像我呼吸一樣,看這口氣到底有多長。比如做48米,似乎沒有問題,但感覺和遠山的關系,還沒完全建立起來就結束了。所以再加長。加長的時候所有元素都要隨之變動,要重新整理一遍。后來想來想去,做到72米。此時,人的眼睛看的時候,已經不能把握它,開始有一點兒恍惚,這個時候正好。這種體會是和練字有關的。
(圓 田摘自上海譯文出版社《珍物》一書)